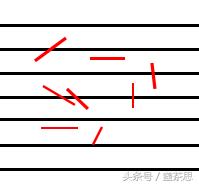【英】托比·利西蒂希/文 石晰颋/译

The Archipelago of Another Life: A Novel, Andreï Makine, translated by Geoffrey Strachan, Arcad, October 2021,240pp
三十多年前,安德依·马金尼(Andreï Makine)将自己的国籍从俄国换成法国,将日常语言从俄语改成法语——母国却依旧挥之不去。这种本能般的引力并不仅是怀旧,而是时刻存在,并且满怀伤痛。对马金尼来说,俄罗斯与其是一个国家或地方,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提醒——凭借其可观的历史和惊惧之美——提醒人类的无能、渺小和傲慢。
与遭遇伤痛后的情况一样,对此的凝视往往集中在过去。马金尼曾经提到俄罗斯“就像一个旧情人”,他需要保持其完整的形象,以获得审美与智性的灵感。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1987年他前往法国寻求庇护后,就不再愿意重访母国。相反,在《俄罗斯仲夏夜》(1997年)或《露水情缘永难忘》(2013年)等小说中,他倾向于重新想象这个国家动荡的二十世纪,并对其近年来堕入寡头资本当道的现状投以冷眼。
《另一种生活的群岛》是一部典型的马金尼作品,讲述了一个关于痛苦、抵抗和超越的迷人故事。它既像神话,又富有精细的现实感,既质朴又几近神启,在叙事上虽然简略,冒险和追踪的线索又是令人愉悦地直截了当。故事发生在作者的出生地西伯利亚,这不是一场徒劳搜索,而是一番狂野的针叶林追逐。

安德依·马金尼
与马金尼之前的小说类似,书中的故事宛如俄罗斯套娃般层层嵌套。一位老人回忆他年轻时与另一个当时已经年迈的人的相遇,并以此回望他自己的青春。这样的设定使我们能够纵览大量的历史背景信息:为我们讲述的“外在”的叙述者身处当下,回顾他孤独的童年,以及在1980年代作为“土地测量员”被派往俄罗斯远东的青年时期。这个年轻人在探索北方的森林时,发现了一个神秘人物,于是条件反射式地开始追查。结果他被比他更聪明的人骗了,像兔子一样陷入了圈套。猎捕他的是一个两鬓斑白的逃犯,名叫帕维尔·加采夫,可以说是一位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孤星血泪》中的马格维奇,属于他的发掘与探索的复杂故事由此展开。
加采夫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是小说的主体。当时这位二十七岁的预备役军人、学生,正在写一篇关于革命暴力的论文,加采夫在军事训练中与被临时提拔的上司卢斯卡斯发生了争执。他由此遭遇到的第一个惩罚是在一个地狱般的地下“掩体”过夜——一个他几乎无法出入的“棺材”;第二个惩罚是加入一支搜寻逃犯的队伍,如果没抓到,他就会成为替罪羊。
这支五人小队出发了,在针叶林里四处乱撞。加采夫本能地想要理解并在“残酷无常的历史游戏”中存活下来。曾是阶下囚的瓦辛,如今是这支小队的道德支柱,他早就放弃了这种妄想。他负责管教追踪犬阿尔马兹,他对这头野兽的付出,以及对其无意义的杀戮的反应(他对一个上司大打出手,然后温柔地跪下,“试图阻止鲜血从阿尔马兹的胸口流出”)表明他认可自然法则超过人类法则。队伍中还包括了施虐成性但又懦弱的卢斯卡斯上尉、他的下属——坚守规矩的拉廷斯基、以及有人情味但酗酒的布托夫少校。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有一种狄更斯式的奔放,对人类的愚蠢和虚伪则有一种奥斯丁式的玩味。还会令人想起契诃夫和康拉德。马金尼习惯于勾起这种高远的比较。
追捕本身一直保持着惊心动魄的气氛,对森林的描写华丽又异质,求生历程的诸多细节直指人心。人无法在针叶林里“行走”,而必须 “以游泳者的柔韧性穿过它”。人们必须避开溪流的“乳白色”部分,“河底是粘土,因此很滑”。把一件带帽的斗篷挂在树上,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诱饵。森林变化无穷,但苏联科学及其“测角仪、转速计和经纬仪”则似乎是其可笑的概述。杰弗里·斯特拉坎(Geoffrey Strachan)的翻译在许多抒情文字带来的挑战中得到了升华,但也包括了令人愉悦的口语化和粗俗感(“有点像穿裙子的教官”;“我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被追捕的对象一次又一次地胜过了他们,搜索队的成员也逐个受伤或病倒,不得不乘上临时扎起的木筏离队顺流而下(这些失败逐步累积,产生了一种刻意的荒谬感)。每失去一个成员后,这个小组的生态就会发生变化。逃犯是这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因素——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一直在移形换影,他展现出的与针叶林的关系,以及摆脱困境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几乎堪称超自然。逃犯既是一个电影术语里的麦高芬,又是反派,还是导航星,他是整部小说精神上的中心。而我们逐渐地了解到,引导这个神秘人物的是一种为了彻底弃绝这个世界的生存意志。
在追捕之旅中,伴随着同情心,加采夫逐渐摆脱了心理负担,包括与军队和社会之间的束缚,保持理智的努力,以及与人类本身的羁绊。他利用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一个破布娃娃,他童年时在一个可怕的悲剧现场发现了它。“看到这团碎布,我就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极端脆弱性”。这个布娃娃是他的“守护天使”,是一个具备“谨慎、妥协……服从”等特质的胆怯的辅佐者。也有代表欲望和征服的一面:简而言之,象征着凡人的肆意妄为和道德的冷漠怯弱。
只有超越这个“娃娃”,只有放弃他“生活的欲望”,加采夫才能真正地生活。这是那个逃亡者教给他的东西,也是加采夫后来教给本书叙述者的东西,也是我们从中所知的东西。马金尼的神学在此处可谓极为佛性,必然是后基督教的。在亲身经历了多年的恐怖之后,加采夫对“原谅这一高贵诱惑”说不。
全书上下文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这点的陈词滥调,只是安德依·马金尼勇敢而清醒地尝试了几千年来作家、艺术家、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超越加采夫所谓的“人性的核心”、经验的迷雾和时间的幻象,进入事物本身,将生命回归本质。而当加采夫和他的精神向导开始“另一种生活”时,我们会跟随他们,逐步地,走上他们的路。
(本文原文发表于2021年9月23日《华尔街日报》,由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责任编辑:彭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