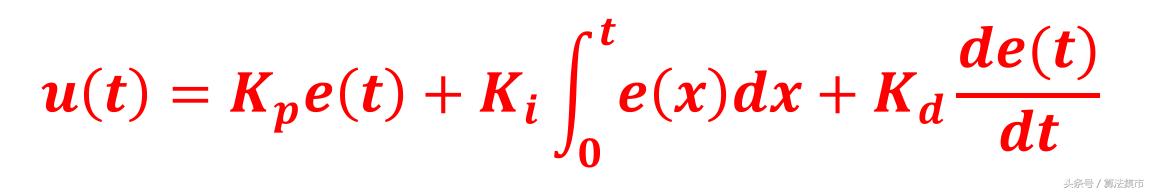端午节回家看母亲。到家的时候,将近上午十二点。
我是坐长途车回老家的。车到了镇子上,我买了一些茄子土豆等杂七杂八的蔬菜,给母亲买了几根麻花和几个糖糕,加上单位发的一盒宗旨,算是给母亲凑了一堆端午节的礼品。
进了院子,没有听到母亲的声响,到了母亲的屋子,看到她老人家醒着躺在炕上,见到我母亲说,还以为是邻居来家里串门子来了。
午饭是母亲做的,母亲说她忘记了今天是五月搭五。母亲问我吃什么,我说把我拿的粽子放在锅里煮一下吃,母亲想了一下说,“老规程,还是油饼白水鸡蛋吧”。
母亲烙的油饼油很大,是用电饼铛烙的,油饼很薄,吃起来有一些干脆的口感。白水鸡蛋散黄了,母亲说鸡蛋一次买的多,放的有一些陈了,没有把蛋黄包住。
母亲十年前住院的时候,得的新病是心脏房颤,住了十天医院,急性房颤没有纠正过来,就成了慢性房颤。四年前住院的时候,母亲出院单上写的病有房颤、高血压(高危)、脑梗、脑萎缩、脑供血不足、高血糖等病。这些病基本是典型的老年病,她都得上了。住了一周医院后,母亲说大夫打的针都不为啥,药也吃到石头上去了,母亲的主治大夫说,“你这是老年病,天王老子都没办法”。大夫拿着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对我说,“你看这白色的轮廓变大,你的母亲脑萎缩严重,大概快要老年痴呆了”。
四年过去了,母亲的记忆力基本没有减弱,有时比我的记忆力还好,只是她因为脑供血不足,动不动就头晕。母亲从五月中旬回到家后,一个人在家里,这教我操不尽的心。母亲说,“不怕,都快八十了,一个人在家里自己做着吃喝没问题,我有事随时给你打电话,农村年龄大的老婆多了,人家能行我就能行”。我总是不放心,每天晚上一个电话查岗,母亲就说,“别花电话费了,我好着呢,不好就给你打电话”。
吃完母亲做的饭后,母亲就让我午休去了。“你跑了一上午,去睡嘎”。
下午,我和母亲裁白。母亲把接的白从柜子里拿出来摊在炕上。母亲把白整理一下,给我说,“孝衫是一丈二尺的布,孝褂是九尺布,只给侄儿侄女和外甥外甥女,给侄儿和外甥一人一件孝褂,侄女和外甥女一人一件孝衫外加一件孝褂从,还有头巾、孝冒、脚头孝”。我把母亲整理好的白布,用裁好的小纸条写上晚辈名字,用线绳绑起来。我们姊妹三个两男一女,所以接的白布孝衫少孝褂多,要散的白则是女多男少。母亲说着,我记着,大约还差七十米布。

下午四点,天很热。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舅家看弥留之际的大妗子。在大妗子的炕前,母亲拉着大妗子的手,按着大妗子的指甲,和大妗子说话。大妗子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说话气息急促而虚弱,似乎神志还清楚,但答话似有似无,声音微弱,教人听不真切。母亲没有表示悲伤,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你大妗子两眼无神,看来人快不行了”。“人活一辈子,终到了还没有一口箱子耐久,你爸婆的爸婆的箱子就传到了我的手里”,母亲说。
农历五月初六早上六点不到,我三舅给我打来电话,说大妗子临晨三点走了。
“阿弥陀佛,你大妗子终于不用受罪了”,母亲说。从检查出病到死亡七十多天,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晚期的癌症病人生不如死,时时刻刻承受着难挨的肉体痛苦。
上午十点过后,我和母亲去舅家给大妗子烧纸。在我烧纸后,母亲给小她五岁的大嫂跪下磕了一个头。
回老屋的路上,我们去了一趟镇子上的布店,挑了一卷密实的白棉布,我们扯了七十米。
到了下午,我继续陪着母亲裁白。母亲说人,我来算尺寸裁布。“女的孝衫一丈二尺,男的孝褂八尺,你没算错吧”?母亲说。我说,“女的一丈二尺,就是四米;男的是九尺,不是八尺,九尺就是三米;一个女的给七米布,一个男的给三米布”。我们这里的风俗,给女的布包括女婿的(一个孝衫一个孝褂),给男的只有一个孝褂,不知道什么讲究。哭丧的时候,女的是主力军,一般女的号啕大哭而不悲哀,哭声和眼泪同步,有很强的表演性质。在女人的哭声中,男人只是无声地流泪哀痛。
不到晚上六点,我们就基本把孝布裁好写上名字绑好并装进塑料袋子。我把分好两个袋子的孝布放进柜子的后,母亲说,“我一直想把白裁好分了,可我不识字,这两天干了一件正经事情,了了我的一件心事”。我反问母亲,“你怕你走了,我们不给人散白”?母亲说,“我活着也闲着,我走了就没有那么乱了”。大约还有几家距离比较远的堂弟和走动不多的外甥外甥女侄儿侄女,母亲说她走了以后就不给人家说了,白也不散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是否要给门子里我的一个从小长在大城市的堂弟孝褂时,母亲说,“要给,这是近门子,不给散白就失礼了”。
此时,院子里的杏子正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