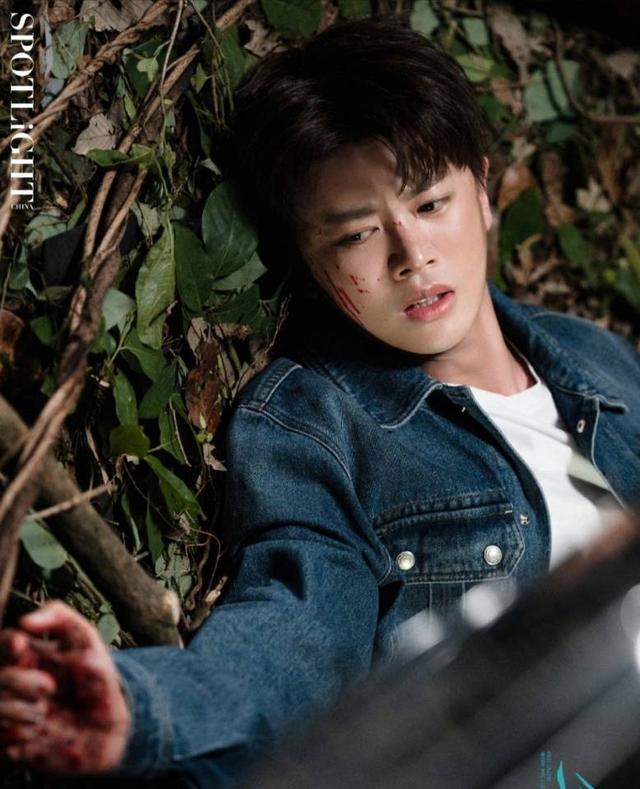作者: 罗东,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麦田信箱07。值班回信:罗东。法律读库转载本文已经取得授权。

来信人:恶女。
你好:
看到这个信箱,有点兴奋,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去和陌生人说一些不忍启齿的话。
其实,在我说我的故事之前,你的回复内容,有可能已经猜到,但是原谅我还想说,因为这些话已经在嗓子眼待了很久,感觉到了一股腥臭味。
你说:作为一个已婚的女人,和另外一个已婚的男人维持着暧昧的关系,是不是很可耻?是不是很令人作呕?
和自己的闺蜜说了,她说:站在我的立场尽可能的理解我,但是还是不希望我这样做,对不起爱自己的人,同时所谓令你上心的人不过是一个对家庭没有责任心的渣男,你何苦为了这样的男人去伤害爱你的人?
而我会不顾廉耻地说:我们见面,只是聊聊天,从没想过要渗透到彼此的家庭里,只是做一个朋友。可是,其实我心里知道,谁会翻来覆去的看一个朋友的聊天记录呢。
但是,你要说我是“小三”、“第三者”,我觉得我和他彼此都不是。他爱他的家庭,我爱我的家庭,我们从未想过介入彼此的生活,只是聊一聊工作,聊一聊电影,聊一聊自己。不过还是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对待爱我的人,感觉我不值得他全心全意的爱,我很可耻。
具体,我想说什么呢?有些混乱。这样双面人的生活还有两个月应该就会结束,爱我的人回来了,我就不会在有时间与精力去进行那段暧昧的关系,我希望是这样的,可我能保证吗?
自己采取过很多努力去遏制这样的关系,删好友,拉黑,可是最后自己都投了降,还是重蹈覆辙。慢慢,自己就觉得顺其自然吧,安慰自己只是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无关金钱,无关性,甚至一度认为我们之间是纯洁的,不是恶俗的“婚外情”戏码,我不是“小三”,他也不是“渣男”,只是两个互相欣赏的人保持了一段交心的关系。
也许,你已经发现了,我还在为我的无耻辩解,为自己找理由。我承认我爱着我的先生,每一次的视频,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幸福。但是,我也不想否认,对他,2017年的第一次见面,就让我心动了,只不过我以为这样的心动只是偶尔的波澜,没想到过了2年以后,他和我竟然有了开始。
恶女的自述,有可能你都不知道回什么,甚至不屑回复我。不过,还是感谢你看完。人性真的好复杂,好复杂。
回信人:罗东
谢谢你的故事。你最后一句是对的,“有可能你都不知道回什么”,我的确不知道如何去回复你。
婚后遇上一段暧昧关系,要如何去讲述、怎么去处理?你在脑子里可能已经纠结了几十遍。你是有答案的。你身边的同龄人也是有答案的。而我可能都没资格来说一两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和你一样的困惑,更缺乏生活上的阅历。
但是,在这一期邮件列表里,你来信的时间最早,内容也最长、思绪可能也最复杂。怎能略过?我看完你的故事,也回忆起过去的一些场景、听闻。倒有了几句话。即便是装成熟,也要回你的这封信。
那是四年前(还在学校没毕业),有一个晚上,我和一位同学在操场散步,无非闲扯、说这说那,印象里并没有什么目的。突然,他谈起微信的“漂流瓶”,还鼓励我去使用,并去感受另一个世界,然后回头再写一篇论文。
我笑他“不正经”。何为“漂流瓶”?我当年只把它理解为一种陌生人社交,在微信上就像“附近的人”“摇一摇”一样。运营商通过这些功能推动了微信早期的用户积累。
“不不不!”他打断我。他说,他用半年“漂流瓶”结识了一批奇奇怪怪的网络“野游者”。有男有女,有少年少女,有中年女性。夜深人静,他们都打开“漂流瓶”去放任。
他尤其提到三位。第一位是上海的企业高管,和他分享其与朋友、同事在身体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二位是南京的大学生,成绩好,性格大方,是同学们心里的“女神”,晚上也悄悄玩上“漂流瓶”。第三位是郑州的中学生,缺少朋友,在“漂流瓶”上对他产生好感,决定要到武汉来见面。他吓坏了,赶紧不再联系。他说,他只是迷上了这一种交流方式。
我今天去回忆他当年说的话,既不是评说、也不是为任何人辩护。他的这些故事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微信上那个不怎么起眼的“漂流瓶”选项里面竟然隐藏着一个波涛汹涌的网络世界,在那里,人性疯狂驰骋,欲望也一并泥沙俱下。
我所学的社会学一般认为,人类创造了一些制度、规范、舆论和习惯来建立社会秩序。要验证这些秩序是否建立,通常是要通过可查看、可感知的社会事实,而那些虚无缥缈、玄乎其玄、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即便反思,也经常是反思一种结构、一种背景。
然而,有那么一些领域,实际上是这些制度、规范、舆论和习惯无论如何都难以进入的。它们一直在逃离“驯服”。它们是“人”最后的“无政府”地带。而历史上的一些疯狂举措希望改造人性,统治关于“人”的全部领域,最终造成灾难,并不得不宣告失败。
我赞同你说的“人性真的好复杂”。你看见了一个矛盾的自己。没错啊,它就是复杂的。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是不可能像数理一样,一是一,二是二,也不可能像社会事实一样,有标准即有是非黑白。而反之,人性也不必像数理和社会事实那样非辨明不可。
那天晚上,因为那位同学的那番话,我回到宿舍好奇地打开了“漂流瓶”,要去瞧个究竟。很遗憾,扔出去两三个“漂流瓶”无回复,而收到的都是广告,也就此退出关掉,再也不见。只是,我依然知道那里躺着一片奇怪的、自由的、赤裸的领域。它表现着“人”不被驯服的倔强。
那么,是好,还是坏?既然人性是复杂的、捉摸不定的,那么,判断就非常简单:是否给他人造成不自由、麻烦或伤害。你要用其他标准来判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参考,反复纠结,持续怀疑自己。更何况,这里面还有的只是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评判。
到此啰嗦了这么多,我承认是因为阅历浅而不得不谈开去。但是,有些逻辑可能是相通的。你说的那部分人性,它是普遍的,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如果你能明确不会给他人造成不自由、麻烦或伤害,其实你完全不必像如今那么自责。何况,你的自我矛盾实际上说明你同意这个社会的舆论和风俗标准,且愿意让它们影响你的判断。我不觉得你错了。
但是,如果情况相反,你或许要尽快做出选择,确认是否爱上另一位。不是,快刀斩乱麻。是,向爱人坦诚这一切然后开始你的下半场。而这一句,你可能猜到我是从一些情感经验人那里学来的。他们被认为“三观正”。至于如何去确认、如何去选择,我就不赞同他们的做法了。没有谁能为谁指点,也没有谁能替谁选择。一个在旁观者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选择,在当事人那里也可能是复杂的、需要反复权衡的。旁观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你也无法讲述所有的来龙去脉。
但愿你的纠结压力会被这些东拉西扯稀释一些,哪怕只是一丁点。不要叫自己“恶女”。
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