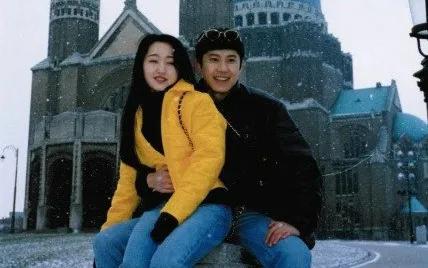狗也不是那条狗
严雨龙
难为情啊!有个声音总会在耳边响起:“呜——噜噜,呜——噜噜。”这是儿时村子里呼唤狗回家吃食的吆喝声。隔着岁月的长河,于今听来也仿佛是向我召唤:回来吧,回来吧! 乡民的语境里,狗一直卑贱屈辱地出没着。
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地独自扛起人类几乎所有贬损侮辱词汇的加身,狗东西,狗崽子,狗窝狗运狗命;丧家被人嘲讽,落水还遭痛打。乡俗狗肉都上不了正规宴席。
杀狗散场,古时习武堂,徒弟师满,各奔东西之际,最后的晚餐就是杀狗喝酒。问世间卑微何物?直教人长叹狗生之艰难!然大抵哀其不幸更重其易生耐苦,乡民往往把痛爱的懦弱孩子,取名黄狗黑狗的叫唤。即便达官贵人也称自家孩子犬子犬女的斯文。似乎显示了卑贱者最聪明,卑贱者最顽强。

难怪狗眼看人了,谁说对狗的诸多叫骂不是人类的自我作贱呢?!读高中时,堂堂全县唯一的重点中学,果真也有一个叫黄小狗的同学。个子小小,声音细细,还满口山里土话。同班不同班的同学,都喜欢逗他玩,他总也不生气。惹急了,他也是叽里呱啦一通那山里话。谁也听不懂他说的是啥。那时男女同学不说话的,但女同学看见黄小狗,常常偷偷地吃吃笑,甚至偶然也要逗弄一下他。这让一些男生好不羡慕。
有一次黄小狗母亲给他带菜送米来,一进校门不管是否正在上课,就直着嗓门喊:小狗——小狗。也是巧合,教学楼一墙之隔是破破烂烂居民区。这边小狗——小狗的叫喊,那边却应声呜——噜噜,呜——噜噜的呼唤。
此起彼伏,顿时引发整个校园哄堂大笑。据说后来老师是慎重其事劝过黄小狗改名,甚至新名字都想好了,叫黄小国,并说明无论用方言读还是地方普通话念,音调含糊差不多,不影响习惯。但是黄小狗母亲死活不同意,说孩子命贱,那么个大名是压不住的。
四十年过去了,偶然还想起黄小狗。隐隐约约听说他后来是当了干部的,不知当了干部之后是黄小狗还是黄小国。

从前的农村狗多。彼时人家屋檐下来只狗,主人是赶紧要将之驱逐的,生怕一不留神那狗就把孩子拉地上的屎吃了,那得留给自家狗的。往昔的村庄,常常寂静间一声吆喝响起——呜——噜噜,这一般是哪家小孩随地方便,而女主人懒得清扫,就唤狗来清除(其实以前的狗除了看家护院,清洁此类事物也是一项任务)。
呜——噜噜,如此一吆喝,四面八方的狗就循着声音赶去。任由哪条正在野外或撒欢或悠闲的狗,只要隐隐约约听见这声“呜——噜噜”,立刻秒停侧耳探寻,一确认方向,便唰地箭似腾空射出。
即便是高坎深沟,也是奋勇飞跃,无疑那是去奔赴一场盛宴。这情形极为明白诠释什么叫奋不顾身,什么是狗急跳墙。小时候,小伙伴日常的游戏玩累玩腻了,大家就“呜——噜噜”地“忽狗”玩。

一声吆喝,看着四处的狗急命赶来,在面前窜来跳去,却没有什么吃食,悻悻然复摇尾乞怜的样子,特别开心。有时不忍心狗的失望,就想方设法去找点吃的以安慰。可常常是一筹莫展——连丝毫便意都没有。
心里就很是过意不去。待到某个节日或家里雇老师傅什么的,好不容易有块肉骨头了,自己啃啃吮吮,舔了又舔之后,再发一声“呜——噜噜”,显然是底气倍增,十分的嘹亮了。
三十年前刚刚进城时,整个城市宛如一个大工地,一些进城务工的老乡,晚上也常要来串门闲聊。那时的老乡尽管离家不久也不远,但普遍挂念老家,所以他乡遇故乡,分外热络。不管干啥的,碰到就熟就亲,聊上一阵家乡话,仿佛也是莫大的慰藉。有一天一个务工的老乡说,他住的工棚里养的狗生下五六只小狗,弃之不忍,养着不能,问有没有人愿收养的。我说你自己都干得狗似的哪还有闲工夫养狗啊?
他说,有所不知,那天街上几个人追打着一条狗,那狗慌不择路,跑进了他的工棚,他赶紧操起棍棒要打,但那狗就是站住瞪着他看,摇尾乞怜。

在四目对望刹那间,猛然感觉这狗似曾相识,定睛一看他肯定这狗就是他村里的,他确定不了到底哪家的狗,咋跑城里来了。于是就收留了,白天狗照样乱闯,但每晚都准时回到工棚。
这不,还和城里狗恋爱生子了......
之后在城里走动,偶然角角落落遇到流浪狗,心中会一闪:那该是哪个村里的狗吧。如今乡村狗少多了,而城里的狗日益增多,是否有些狗原本就是追寻着主人进城务工的背影,而流落他乡。

由于风云际会,有的被好人家收养,摇身一变成了宝贝,有的则倔强又漫无目的地寻找老东家啊?不得而知。每每见此,很想“呜——噜噜”一下,张张嘴罢了。倘若真“呜——噜噜”了,我想那狗是能够听懂的,那是乡音啊。
前些年农村蹲点,许是触景生情勾起往昔的记忆,在村巷里也“呜噜噜呜噜噜”,却不见一只狗跑来。就近见了狗,呜噜噜,狗居然充耳不闻,无动于衷。
甚为奇怪。后见一女扶小孩解恭,路过的狗木然地望了一眼那堆金黄,便掉头跑开了。惊奇问村妇:这狗不吃屎?答曰所有狗,早就不吃屎了。

“狗改不了吃屎”这个哲理却是硬生生被颠覆了。早几年是看过一则资料性的文章,说狗看见人突然蹲下身子,必定迅速转身跑开。“蹲下”就是狗要“被攻击”的条件反射,哪怕一只未谙世事的小狗,也如此自然而然。
这是因为从狗的始祖、太祖、高祖等等,一路过来,几经无数次的因人类“蹲下”而惨遭攻击,甚至反应稍钝而丧命,如此反反复复的深刻教训,以至于深刻到狗的骨子里,成为狗的一种“基因”。
某种事(包括文化)一旦成为基因,那就几乎不可逆的。或许“呜噜噜”声远没有衍生为狗基因吧。至于吃屎之类的,仅仅是果腹充饥到口味品尝,应归于“记忆”或“习惯”罢了。
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总离不开“渴”“饥”的特定条件。记忆也好,习惯也罢,却是此一时彼一时,何况是禁不住岁月的冲刷。不过,狗还有个习性看似有点“转基因”了。即“狗吠生人”。

所谓“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前些年有人笑称,“狗不理”的基层干部是好干部,因为干部成天在村子里忙活着,那狗见了都熟悉得很了,也当作自家人了。
狗对之熟悉,说明他对村情的熟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乡村的狗见了生人确实很少有吠叫咆哮的了。近年时不时要去农家乐、民宿等等,每到一个陌生的村子里,突然遇见不声不响的狗,心里就紧张。深知“不叫的狗会咬人”。
可乡亲和同伴见了就哈哈笑,说现在无论城里乡下的狗,见了生人都不大吠人了,一般也不会攻击人的;再说大多数狗是有身份的狗——有“身份证”的。乡村常常人来人往,如果见了生人就吠,那还不累死。
果然如此。想来狗的世面见多了,哪管谁是生人谁是客;而且不但已有几代狗没有见过“蹲下”之举,反而常常感受到“儿子女儿”般宝贝宝贝的宠幸,于是狗眼看人都是客了吧?! 鸡鸣狗吠,总归曾经是乡村鲜明的烟火。

陶渊明有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勾画了一副乡村清和景明的清欢。唐人刘长卿的一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读之心底一种家的安暖油然而生。炊烟袅袅,鸡鸣狗吠,倒真是深深的乡愁了。
有首歌唱——“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蓦然想起,回到故乡不闻汪汪叫,连狗都对你爱理不理的木然,心中未免很有些落寞,狗也真的不是那条狗了。
漂泊半生,乡关何处,难为总关情,反倒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故乡的一条老狗了,踟蹰在岁月的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