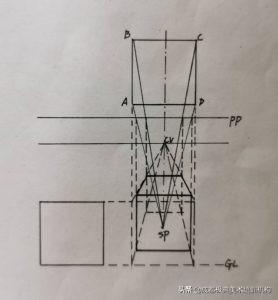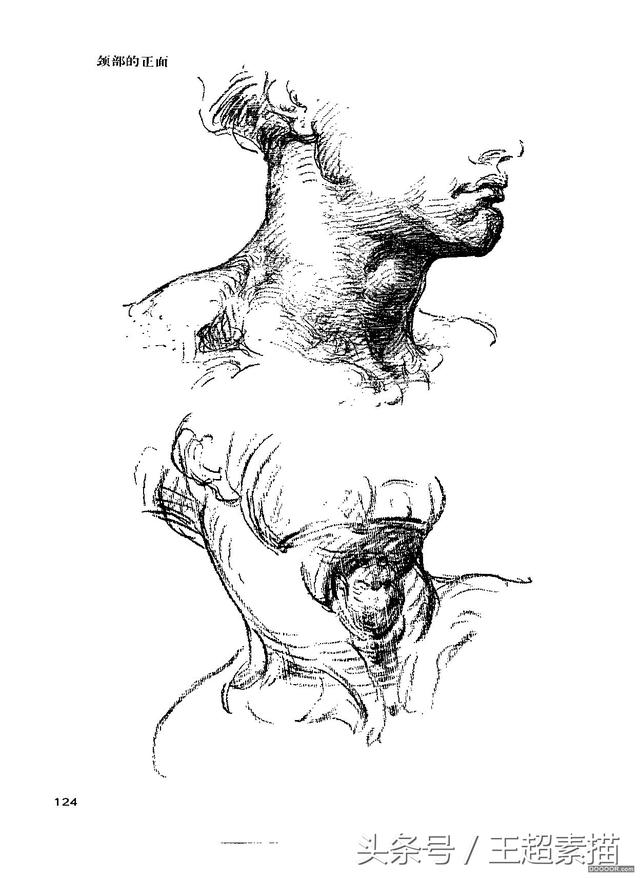第三次“抓特务事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已记不起来了,但肯定是在夏天,地点就在上海市宝山县顾村乡(今宝山区顾村镇)星星大队的农村,在我老家的东门口。
那年我已经工作,正好放暑假回家探亲,所以,家门口的这一次“抓特务事件”我自然就身临其境了。
我老家宝山县地处长江口,濒临东海,国民党派特务来大陆,很大一部分是从长江口偷偷上岸潜入我们宝山,再潜入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所以我们宝山的“特情”时有发生。
记得是我到家不久的一天傍晚,我们刘老宅第二生产队里响起了集合开会的钟声。
我家东门外面有一块比较宽阔的场地叫队场,是我们二队收晒粮食和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那里有一只大钟。听到钟声,我出东门看看,发现地里干活收工的人们陆续来到了队场。收工的队伍里有几十个从上海下来的中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他们是来我们队里劳动锻炼体验生活的。他们在队场上排着整齐的队列参加开会。我走过去,下意识地站到了他们的后面。
“开会了!开会了!勿要说话了!”(上海话“勿”,就是“不”,下同。)生产队刘队长宣布开会,向大家传达上级开会的精神。
队长说,请大家注意,上级开会告诉我们,最近,国民党反动派又派特务来了,很可能已经从长江口偷偷上岸,潜入到我们宝山了。大家要提高警惕,发现有陌生人到我们村里来,鬼头鬼脑东张西望的,要上前盘问;怀疑是特务的,要盯住他,想办法立即向队里报告。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夜里,那就更可疑了,你就大叫一声:“抓特务!”大家听到叫喊声,要立即爬起来抓。管他是不是特务,抓起来再说!
讲话的内容大概就是如此。
“听清了吗?”队长问。
“听清了!”大家回答,其中中学生回答得最为响亮。
随着队长的一声“散会”,大家忙不迭地回家烧锅做饭,吃饭,洗澡,乘凉,睡觉。农民一天中最后要做的事结束了,不久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特特务!抓特特务!”
凌晨3点多钟,队场旁边几家的人被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醒,第一个冲出大门的是带领学生到我们队里劳动锻炼的班主任老师。她见叫喊的人是住在斜对面的邻居,问清确实有特务并且特务已经钻进他家里时,就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钟跟前,拿起钟锤,“当当当当当当……”敲响了紧急集合的钟声。
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我立刻起床,找到一根米把长的木棍,冲到了队场上。我发现,队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来到了,有拿锄头的,有拿扁担的,有拿铁锹的,有拿镰刀的,有拿长柄铁勺的,还有妇女手里拿锅铲的……最先到达队场的是那些警惕性最高的中学生,他们几乎都是赤手空拳,有几个手里拿着手电筒。
几十个中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已经把潜入特务的那家人家团团围住,把前门和后窗堵了个水泄不通。
发出“抓特务”叫喊的人叫刘林宝,五十六七岁,天生口吃。例如,他把“特务”喊成“特特务”,把“抓特务”喊成“抓特特务”。原先他是个光棍,去年年初,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皮肤白嫩,个儿瘦高,挺漂亮的,却自愿与林宝住在一起,算是组成了一个家。因为这个女人会踩缝纫机做衣服,队里就安排她到大队办的服装厂干活。
现在这家男主人林宝说有特务钻到了他家里,人们就议论开了。
有人说,他老婆是外地人,来得不明不白,那女人是不是就是特务呀?
有人说,林宝可能在夜里发现他老婆在偷偷地向台湾发电报,就跑出来喊“抓特务”的。
还有人说,林宝可能起来到外面小便,发现外面来了个男特务钻到他家里,可能与他老婆接头了。
……
“冲!”大家正在纷纷议论之时,不知是谁一声令下,几个勇敢的男学生踹开林宝家的木门,照着手电筒冲了进去!
我急忙来到门口,手握木棍,警惕地向屋里观察。我虽然没有跟着学生一块儿冲锋陷阵,但勇敢地把守门口让特务插翅难飞,也算冲到了第一线。抓到特务到乡政府报功的时候,或许也有我一份呢!
“出来!出来!”屋里传出了学生们的喝令声。原来,他们发现特务藏在床底下,用手电筒照着喝令他爬出来。
“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屋里再次传出了学生们的喝令声。
“我没有枪。”特务一边从床底下爬出来,一边说。
“举起手!不准动!”还是学生们的喝令声。
一阵打斗似的杂乱声响过后,几个学生把特务押了出来。
我看清了,押特务的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生。他们一左一右,把特务治成了“喷气式”——就是男生各自用内侧的手抓住特务后背的衣领往下压,同时用外侧的手抓住特务的手往后提起,迫使特务弯腰伸头,两只手向后向外伸直翘起,好像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我见过,刑警押犯人上刑场时就是这种架势。
“让我看看,特务长个啥样子?”原来,刘队长来到了特务跟前。队长用手电筒一照,说:“噢,是侬呀!”(上海话“侬”就是第二人称“你”。下同。)然后对同学们说:“小朋友,把他放了,伊勿是特务。”(上海话“伊”就是第三人称“他”“她”。下同。)
“啊?他不是特务?”
“勿是。伊是我们大队服装厂的一个裁缝。”
“是裁缝?”
“是的。”
“那他到这家人家钻到床底下干什么呀?”
“迭个,你们小囡勿懂,就勿告诉你们了。”(上海话“迭个”就是“这”,“小囡”就是“小孩”。下同。)
“我们是中学生了,不是小孩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呀?”
“好,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刚才进去,看到女人了吗?”
“看到了,床上有个女人。”
“伊是来同屋里那个女人睡觉的!”
“啊?一男一女睡觉?那不是流氓吗?”
“是呀!”
“流流流氓!给给给我打!”队长与中学生们正在对话时,有人发出了“打”的命令。一听那说话口吃的声音,就知道喊“打”的就是那个喊大家起来“抓特务”的林宝。
一个“打”字,犹如战场上司令官下达的战斗令,同学们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到了流氓裁缝的头上和背上,三两下就把他打趴在地上了。
“踢踢踢死他!”肯定又是林宝在下令。
听到新的命令,同学们立刻用脚一个劲地踢,感到这样踢好痛快,好痛快!
“勿要踢了!再踢就要出人命了!”队长上前阻止。
同学们刚刚收住脚,挨打的裁缝立刻从地上爬起来,钻出人群就跑!
“哈哈哈哈!”见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大家发出了一阵大笑。
随着假特务落荒而逃,这次“抓特务事件”应该结束了。但是,人们好像没有回家睡觉的困意,纷纷围到林宝身边,想就这次“事件”的起因问个究竟。
我说明一下,上海话,尤其是我老家农民说的土话,是很难听懂的,例如上面队长说的话,而且在汉语里几乎找不到读音完全一样的字,所以,我继续在括号里翻译一下,以便不懂上海话的读者理解。
“林宝,迭个到底是难能一桩事体呀?”(林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是是是……”
“啥叫‘是是是’的,我问侬,伊,那个裁缝,是难能进侬屋子里的?”(什么‘是是是’的,我问你,他,那个裁缝,是怎么进你家里的?)
“伊伊伊……”
“夜里睡觉侬屋里没有插门吗?”
“勿勿插。”(没没有插门。)
“哎呀,夜里睡觉难能(怎么)不插门呀?是故意留门让伊进去的吧?”
“勿勿是!”(不不是!)
“那我问侬,你们夫妻俩睡在床上,伊一进去就往你老婆身上爬,把侬弄醒了,侬受勿了了,就出来喊抓特务的,是吧?”
“勿勿是……是是是……”
“啊呀,又是‘勿是’又是‘是’的,到底是难能(怎么)一桩事体呀?”
“是是是……”
“又是‘是是是’!好,我不逼侬了,侬自家(自己)慢慢讲吧!”
“好好好,我讲……”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凌晨3点多钟,林宝的女人叫他起来,给他3块钱,要他去杨行镇买只菜篮子,剩下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还需要说明一下,我南方老家的街道在天亮之前就开市,除了商店开门之外,做买卖的农民就在街道两边看着自己的摊位,买菜或买其他东西的农民以及街上人,在街道上货比三家,自由选购。天亮之后,上街的人们慢慢散去,纷纷回家,街道上就算罢市了。这跟北方的“夜猫子集”差不多。人们走两三里路上街买卖完毕,回家不耽误下地干早活,所以,凌晨4点左右上街买菜是正常现象。但3点多钟就上街,有点儿早了。
林宝说现在上街太早了,女人说不早了,去晚了买不着好篮子,催他赶快去,林宝就听从了。出门时,女人没有起来,他就把门虚掩上。
去杨行镇是向东走的。林宝一边走一边想,女人今天好像有点不正常,从来不给我钱,也从来不让我上街,今天突然对我这么好,是怎么回事呀?想着,想着,他要与女人反着做,“你叫我向东去杨行镇,我偏向西去顾村镇!反正都是买菜篮子。”这么一想,林宝就掉头向西走。
出了村,走到一条河边的时候,林宝发现对面来了一个男人,与他擦肩而过,向我们村的方向急急地走去。
“这是谁呀?好像在哪里见过。”林宝仔细一想,“噢,想起来了,他是大队服装厂的一个裁缝,与我的女人在一起干活。前几天大家都在传,说他骑自行车带着我的女人上街,到玉米地里铺一只麻袋,两人就在麻袋上……现在离开天亮还早着呢,他这么早就到我们村里去做啥呀?是不是去找我女人的?”林宝这么一想,掉头就去追!
追到村头,发现裁缝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低着头直往前走。一个走一个跟,来到我们二队队场,那个裁缝一头钻进了林宝家里。林宝想冲上去一把抓住那个裁缝,但他不敢,就只好在门外着急,可以说急得团团转,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进我家里去到底想干什么呀?不行!我得去听听。”林宝这么一想,就走到屋后面窗口边去听,家里的床就在窗口下。不听不要紧,一听吓一跳!他清晰地听到床上蚊帐里发出了一种他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噢,你这个女人,原来你们早就约好了,是故意叫我走开的。”林宝识破了他女人的调虎离山计,气不打一处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最恨的当然是那个裁缝喽!“你来睡我的女人,看我怎么报复你!”他“嗵嗵嗵”跑到前面队场上,忽然想到昨天傍晚生产队长开会时要大家提高警惕抓特务的话,立即拔直了喉咙大喊:“特特务!抓特特务!”于是出现了前面所讲的“抓特务”场面。
故事听完了,大家的好奇心也满足了,这回可以回家睡觉了吧?
不!大家忽然想起故事的另一个角色——林宝的女人。
“迭个女宁(这女人)还在屋里吗?”
“肯定在屋里呀!”
“想不到,迭个女宁好涅佳勿过(这个女人好日子不过),会去勾引野男宁(人)!”
“可能林宝满足不了她吧?”
“怎么会呢?”
“可能林宝下面的勿来赛(不行)呗!”
“哈哈哈哈……”
“勿对!”玩笑之余,有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伊在屋里一点响声都没有,会出事吧?”说着,一个年龄大一些的邻家妇女向身边的人借了一只手电筒,照着手电光走进了林宝家。
“勿得了啦!”那妇女一边叫着一边紧张地跑出来说,“伊曲牙得!”(“她喝药了!”)
“快点拖出来抢救!”队长一声令下,架人的架人,拿凳的拿凳,提水的提水,找肥皂的找肥皂,众人忙得不亦乐乎!瞬间,大半桶肥皂水制好了,两个女青年把林宝女人架出来按到了凳子上。
“灌!”不知是谁一声令下,抓胳膊的抓胳膊,抱头的抱头,扒嘴的扒嘴,拿杯子的拿杯子,一杯杯肥皂水直往林宝女人嘴巴里灌,把那女人灌得满身湿透,嗷嗷直吐。
“勿要灌了……我,只曲了一眼眼(只喝了一点点)……”林宝女人有气无力地哀求大家。
有人立即到屋里床边找出来那瓶开盖的“敌敌畏”。几个人都仔细看了,瓶里确实没有少多少,证明她确实喝得不多,就不再给她灌了。
天还没有亮,人们在队长的驱赶下回家睡觉,林宝也在邻居的催促下把他女人扶进了家里。
到这里,这个“抓特务”的故事真的结束了。但是,作为一个“故事”,它还有一点儿“尾声”。
从第二天起,林宝的女人除了倒马桶时低着头从家里走出来之外,一连几天都闷在家里,无脸见左邻右舍,更不好意思去大队服装厂上班。
四五天之后的一个上午,队里包括林宝在内的劳动力,以及由老师带领的中学生,都到村庄东边的地里干活去了。大概8点多钟吧,有留守在家看孩子的老妇人亲眼见到,林宝的女人肩上背着一个包,手臂上挎着一个包,低着头,向西出村,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