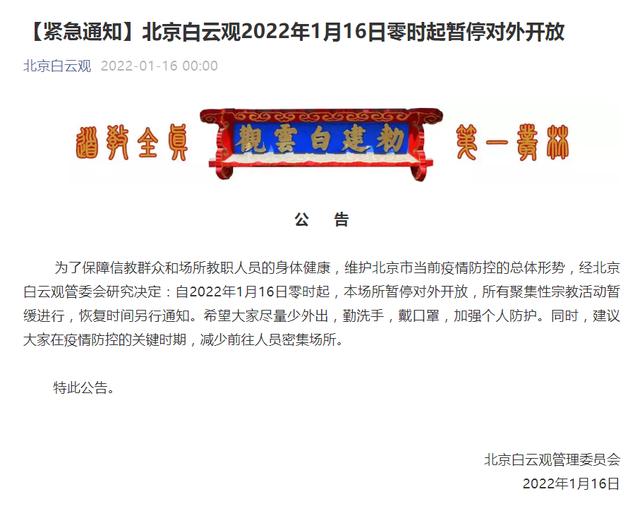【经文】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一〕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隍曰:入定。〔二〕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无对。〔三〕良久问曰:师嗣谁耶?策云:我师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四〕隍闻是说,径来谒师。师问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师愍其远来,遂垂开决,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五〕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

【述旨】
〔一〕长坐二十年,与守尸鬼有何异乎?总之性上大事,非坐不见,而坐法亦必随缘,不是死坐可得,要息下狂心,用"息"字功夫,不得不借资于法。至于定中起慧,慧中练定,使之圆融老熟,尤非随境练心不可,断非死坐可以守得出来。南岳对马祖之磨砖,用意可知。今二十年功夫,都用在守上,灵机既窒,大用即难起矣。彼开口即曰入定,直见其有能入之我,与所入之定矣。四相宛立,安名见性,使不遇善知识以开启之,其终身也已,可惧哉。又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自此方有入手处矣,盖必彻悟后,始入正修行路也。
〔二〕入定二字,通身都是毛病。智隍用功垂二十年,执取此法,牢不可破,一病也;有法即有取舍,出入是非相对,妄上加妄,二病也;既云正入定,复云不见有有无之心,自己尚在徘徊进退中,则其自己不能信入可知,安云大定,三病也;大定无相,然亦非无定相,乃无定无乱,本来无住圆妙湛寂之相耳,说有定者,已非定矣,以有所得心也,则能得者谁乎,曰智隍,此四病也。故眼中著不得一点屑,致满盘皆错。
〔三〕智隍闻玄策语,实已开悟,未敢自决耳,此即从前自谓已得正受之病也。惟因其言轻,尚不敢深信,观于"良久"二字,可知之矣,后得祖印可,曰:诚如所言,方始通体脱落,此刹那解脱,即名得道。
〔四〕出入定乱,因分别而有,尚属有心。在可思议之中,必入不可思议之境,乃真解脱,乃为大定。性本无住,莫以为住于禅定寂灭,即以为是,当远离此劣见,以此为颠倒法也,性本无生,莫以为有禅定可生而作此想,当远离此劣见,以此亦颠倒法也。当心如虚空,亦莫著虚空之见,乃自然本寂之大定。今死执有出入,有大定可得,便是有心,安得名定?若不如是,则又含糊笼统,或落断见,岂是佛之旨哉?
〔五〕空中有声报隍禅师得道,读者必叹为神异,往往于此等处著意,至前段紧要关头,往往略过,殊堪浩叹!不知此乃预植河北士庶将来入道因缘也。故智隍归后,得开化四众,乃护法神之慈悲也,又何疑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