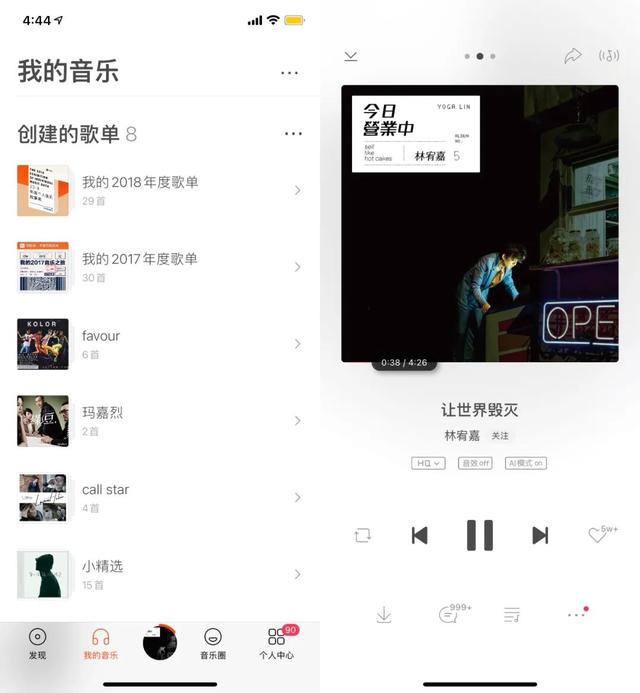唐代诗人李贺很有才情,韩愈对他十分赏识,劝他考取功名。正当李贺准备赴长安考进士时,却有人放出流言:李贺的父亲名字中有个“晋”字,与“进”同音,犯了当时“嫌名”的忌讳。正因这一缘故,李贺终身不举进士。
对此,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讳辩》:“父名晋,不举进士。若父名仁,子遂不得为人乎?”陈锡玄也说:“此讳而近愚者也。”
类似这样“讳而近愚”的现象,并非个例。范晔的父亲名“泰”,于是范晔不任“太子詹事”之职;吕希纯的父亲名“公著”,因而辞掉“著作郎”之任。这样的忌讳,现在看来迂腐可笑,但在当时,毕竟有社会风俗的外部压力。然而,对于为官从政之人,如果在工作中“讳而近愚”,那就另当别论了。
明代有一个郡守,与人交往时忌讳很多。他刚到任职之地,一个叫丁长孺的人来向他谒贺,因为“丁”字有“遭遇”之意,不吉利,郡守怒而不见。他的下属明白其中缘故,把名帖上的“丁”改为“千”,郡守才欣然出来相见。试想,如果为官者都像这样,把“吉利”与否奉为标准,识人用人还能有什么准头?但实际上,看八字、看面相、看风水等现象,时至今日仍未绝迹。
官位,是一些人忌讳最深、最多之处。一天,有客人登门拜访秦桧,大门的守卫说秦桧不在。因为“不在”有“死”的意思,客人怒道:“你怎能诅咒你们大人‘不在’,说‘出外去’就可以了啊!”守卫面露难色,答道:“我家大人宁死,也不肯说‘出外去’三个字的。”眼里只有官位,宁死不愿外调,秦桧的官欲可见一斑。
忌讳,有时也是谋取私利的工具。北宋时,宰相蔡京权势极大,对于自己的名讳十分在意。因此,各级官员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改称畿左、畿右。时任太尉的薛昂,很善于对蔡京逢迎拍马,与宾客会饮时,谁说了“京”字,就举杯罚酒;平日里,家人不小心说了“京”字,他也怒目相视;如果他自己一时口误说了“京”字,就自己抽自己嘴巴,以示警戒。
上级有所忌讳,下级知所趋避,难免会降低工作效率、搅乱官场风气、腐蚀政治体制,危害不可谓不大。上文中的薛昂,尽管因“善于讳”而一时显贵,但时过境迁,他终究还是和蔡京一起落得遗臭万年之名。
还有一类“忌讳”,是给违法违纪的行为安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头,以求掩人耳目。后唐明宗时期,僧家把酒称为“般若汤”,把鱼称为“水梭花”,把鸡称为“钻篱菜”,如此一来,破戒开荤就有了借口。这样的“巧言文过”今日也未绝迹,如“普通烟盒装中华”“矿泉水瓶灌茅台”之类。一旦事情败露,终究逃不过法纪的制裁,而且更加惹人痛恨嫌恶。
在封建时代,敢向风行于世的忌讳说“不”,需要非凡的勇气。北宋名臣杜衍,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之士。杜衍认为:所讳在我而已,他人凭何干预?正因此,他在并州做官时,下官请教“家讳”,他说:“下官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
“忌讳”的能量是正还是负,取决于目的和动机。坚持理智和道义的“忌讳”,与源于迷信和私利的“忌讳”,性质天壤迥异,影响大不相同。“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这何尝不是为人处世、调和鼎鼐的良策?在是与非、义与利、名与实的问题上摆正态度,勇做公而忘私、刚正不阿、敢于任事之人,方能处理好“有讳与无讳”的关系,成就一番无愧于天地人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