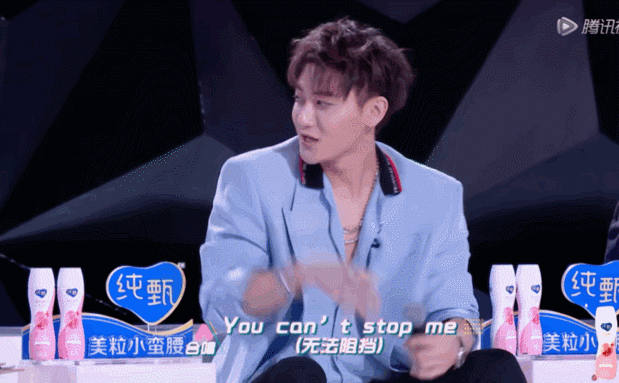“獄yu”,金文的写法,形如两犬相遇而嘶鸣争斗;中间是一个“言”字,在此表示两狗相啮争斗时的叫声。小篆和隶书可谓一脉相承,楷书中的简体仅将双犬之中的“言”字做了简化。
“狱”的发音,大概从相遇的“遇”而来。“狱”的本义为双犬撕咬狂叫。由狗的厮咬引申,可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吵骂。又因为那些争斗者在法庭上颇似二犬相斗,因而引申指争讼、诉讼。如《诗·召南·行露》:“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这里的“速我狱”,即让我吃官司,与人争讼的意思。以二犬比喻诉讼之人,表示古人对诉讼争斗者的一种憎恶之情。汉代以后,人们把监牢也称.“狱”。这是由吃官司必有人败诉坐牢引申而来。《释名·释官室》“狱,又谓之牢,言所在坚牢也,又谓之囹圄。”
从字形上讲,“狱”字用两犬守护,也算误打误撞十分形象地揭示了牢狱这一概念。不仅监狱要用犬来看守,旧时,无论大户人家,还是寻常百姓家,都用狗来看家护院,就连木刻的灶王爷画像上,在灶王爷的神案前,也站着一只金鸡和一只玉犬——据说鸡司展,狗守夜,鸡犬辅佐灶王爷,保佑全家安康。

《诗·小雅·巧言》中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的描述。由此可知,很早以前,狗已经是人们打猎的帮手,为人们“效犬马之劳”了。
兽shou”是“獸”的简体字。甲骨文的“兽”字,右半旁是一只犬,左半部是一个“单”(即猎杈)的形象。“单”字上部的小圆圈表示“猎杈“的尖锐之端,下部的大圆圈表示人手持“猎杈”(干)时的四处挥舞。上古先民在打猎时,先是让狗迅速赶到滞留野兽,直到手持“单”和猎网的猎人赶来。“獸”字正是古代狩猎活动的真实写照。小篆的“獸”字中间增添了一横,表示手的持拿;下部的“口”则表示驱赶猎物时特意挖掘的陷阱,完整地再现了古代狩猎必备的三要素:单、陷阱、犬。
“兽”的本义,既表示狩猎这种行为,也表示狩猎追逐的对象,即野兽。因而,早期的“獸”字,在语句中既可做名词,表示狩猎的对象,即野兽;也可做动词,表示特猎这项活动。这种一字多义的现象,在古文字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很多的。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獸”字的打猎义,则被后起的形声字“狩”所代替。“獸”字的动物义简省后写作“兽”,引申泛指所有野生动物,与人类驯养的家畜相对,即“野兽、禽兽”等。

“猎lie四声”是“獵”字借来的简化字。金文的“猎”字,左边为犬的象形,右边下部是一个老鼠的象形图绘:鼠形的上边增添了四道竖线,表示鼠的逃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此错释为:象发在囟上及毛发鬣鬣之形)。古代社会,狗除了被当作看家护院的帮手,另一用途,便是帮助猎人搜寻、捕捉兔、鼠、獾之类的小动物。“猎”恰是对这一用途的写实描述。小篆的“猎”字承接金文,形体上更为圆润美观。楷书改犬形为反犬旁,缘此写作“獵”
“猎”(读为xi一声),原本指古代传说中一种像熊的野兽,汉字简化时,借“猎”为“獵”的简体字。“獵”,《说文解字》释为:“猎,放猎逐禽也。”即狩猎时的搜寻驱赶。如《诗·魏风·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狟(huan二声)兮。”由此又引申指一般意义上的搜取、追寻,如现代汉语中的“猎奇、猎艳”等。“涉猎”一词则表示粗略地阅读和研究。

” 犹you”是“猶”的简体字。在甲骨文中,“猶”字的构形源自狗喝醉酒后的滑稽丑态,这就是古文字中的“犹”字,不论甲骨文、金文或小篆,在“犬”旁总有一个酒(酉)坛的原因。上古时代的酒,如同今日的米酒或醪糟,连喝带吃(酒糟),甜而微酸,酒精度很低,但喝多了一样会醉。狩猎大获后,人们狂饮之余,也会让狗加入会餐之列。这样,在人们的眼前便出现了醉狗之态“犹”,正是对这一情形的真实描述。
醉狗会东晃西倒,不知应该到何处去,因此,“犹”的本义为摇晃,引申为犹豫不决。醉狗之态的根源,是喝得太多,因此,犹在作为副词时有“已”、“太”的意思,也可表示某种状况的持续不变,相当于“仍然”。如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中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以及成语中的“虽死犹生”、“过犹不及”等。这里的“犹”均表示”同、和....一样”的意思。
狗喝醉后,不听人的吆喝和使唤,这是一种真实的变态。当人们以酒盖脸,假装喝醉时,乃是一种预谋的行为。因此,“犹”字在左右结构对换后,写作“猷”,表示欺诈、谋略。又引申为计划,如陈毅《示儿女》:“科学重实践,理论启新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