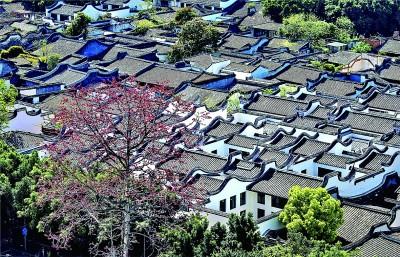文|李崇寒
开元十九年(731),杜甫20岁,在父亲“赞助”下从洛阳乘船顺运河南下,经广济渠、过淮水、邗沟,以江宁(今南京)作为吴越游首站。从小在北方长大的他突然闯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惊喜感大于冲击感。他自幼熟读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对南朝人文荟萃的金陵再熟悉不过。身处同一空间,书里的人名、地名、故事全对上了,只是时移世易,他感慨乌衣巷里“王谢风流远”,讶异秦淮河边瓦官寺(又名瓦棺寺)尚存。瓦官寺建于东晋兴宁二年(364),寺内有瓦官阁,高约60米,早在杜甫来瓦官寺之前,25岁的李白“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写下了他在江宁的第一首诗,阁楼之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杜甫关注的却是寺内那一墙顾恺之的成名作——维摩诘像。
相传众僧为筹钱建瓦官寺,遍求诸贤捐献,每笔捐款都没有超过10万钱的,轮到籍籍无名的顾恺之,他大手一挥,在本上注明百万。众僧傻眼,问如何兑现,顾恺之只说,在院内备好一面粉墙即可。一个多月后,墙上现维摩诘一身,只差画家点睛。顾恺之让僧人对外宣传,他要当众完成最后一笔,邀请大家前来观看,不过有个条件,第一天来看的,须捐10万钱,第二日施钱5万,第三天随意施舍。约定那天,前来观赏的人挤满寺院。点睛后的维摩诘像,光照一寺,瓦官寺立时众筹百万钱。谢安看后盛赞此画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它好在哪?有“清羸示病之容”,行“隐几忘言之状”。
在佛教中,维摩诘居士是金粟如来的化身,富而不吝,乐善好施。他是东晋士族名士尊崇的对象,谢灵运、昭明太子萧统、诗人王维等人受其影响颇深。顾恺之笔下的维摩诘略带病态地斜倚隐几,褒衣博带、论辩“忘言”,正是高蹈超世的清谈者形象,很对清谈领袖的胃口。谢安这么一夸,顾恺之名声登时传播开来。
三百多年后,杜甫寻迹而来,悔恨没和顾恺之身处同一时空,见证青年画家一笔成名。展现在他面前的虎头(顾恺之小字)金粟影,是如此神妙难忘。他如饥似渴地观摩每一处细节,沉浸在艺术的洗礼中,临走不忘从当地朋友许八那里求得顾恺之维摩诘图摹本,当作纪念品,时时观赏。

《龙门》,1959 年,秦仲文,浅绛山水
瓦官寺东北不远处,为顾恺之住处,他在宅内专辟画室,风雨寒暑不下笔,天气晴朗,才登楼作画,一上楼,把梯子撤了,免得旁人打扰,杜甫想必去拜访过。江宁那么多故人宅第、历史遗迹,因为时间原因,杜甫不一定全都去过,他在苏州待的时间更长,“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壮游》),远渡日本的计划没能实现,他只好在姑苏台、虎丘、剑池、长洲苑、泰伯庙中探寻吴王阖闾、泰伯的踪迹。
同样是漫游吴越,李白进入越地后,直夸“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在杜甫眼中,剡溪、镜湖、若耶溪、天姥山、越女确实美,过往历史更吸引他(“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他沿路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晚年作《壮游》时记忆犹新。杜甫死后多年,江左词人仍在传唱他留在江南的诗作,它们后来失传,应该是技法稚嫩、格调不高,一首也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