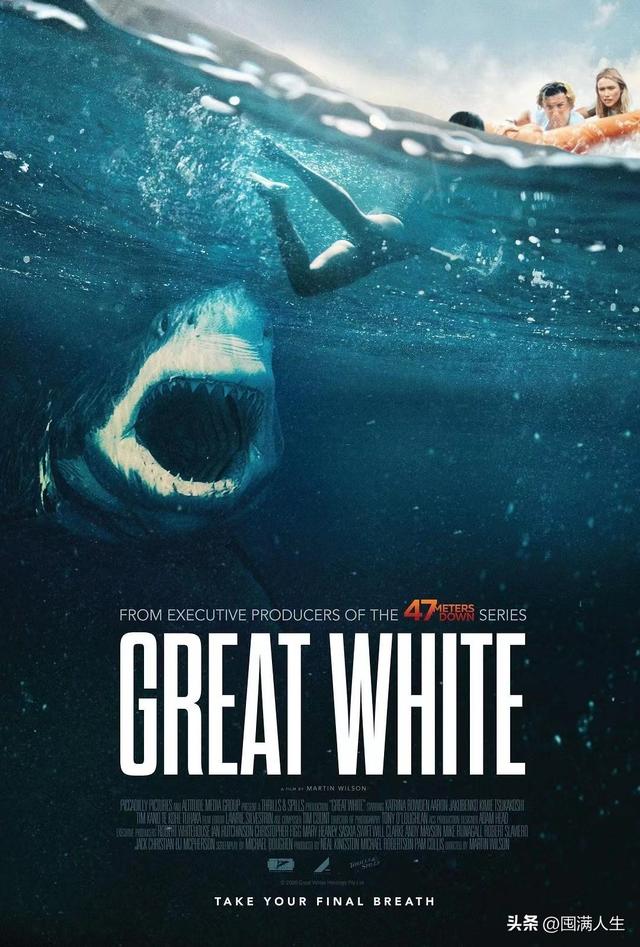苏江档《玉蜻蜓》第30回 “元宰借贷”
大娘娘看到元宰果真如王定所说,与大爷长得如同一个人。于是禁不住地想哭起来,嗓子里像是塞了东西一样。但又怕自己在孩子面前失态,就忍着不让眼泪水流出来,她把眼睛睁得“像汤团一样大”。苏先生说这是因为眼睛睁大了面积也大了,眼泪水就被分散了。我想这倒不是面积的问题,而是因为眼睛睁大,眼球就外凸了,使眼睑受到的压力增大,这样一来眼泪水就不容易流出来了。这个办法只有在刚刚开始想哭的时候才管用。
娘娘实在忍不住了,就回房间大哭了一场,芳兰也跟在娘娘后面进了房间。这时她又当起了“高级参谋”的角色。她对娘娘说,娘娘想要留下元宰,这倒也不难,只要叫他把娘娘认作养母便可。接着她又说作为交换条件,徐家借贷的事可以应允,还可以请徐家二老一起到金家来住,吃用开销全部金家承担——这叫“一妥百妥”。否则不但借贷事免谈,还要徐家将拖欠金家的房租立刻缴清。芳兰这一手真够厉害,难怪人说“最毒妇人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她对娘娘真是赤胆忠心。芳兰又说,留下了元宰,还可以顺藤摸瓜打听到大爷的消息。文宣已经告诉她,大爷确实到法华庵去过,芳兰仍怀疑智贞与大爷有染。听了这一席话,大家一定会感叹芳兰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所以编书的老先生不让她跟随文宣去金山湾,原来后半部书里,还是缺不了芳兰的策谋划策、牵线搭桥。
接着工于心计的芳兰又替娘娘想出了一个新花样,考察元宰将来是不是一个可造之才。她叫娘娘給元宰两份见面礼,一份是黄金狮纽印章,一份是读书人用的白玉戒尺,看元宰挑选哪一件。并说“长者赐,不能辞”,不怕元宰推辞不受。结果元宰说了非常得体的两个字:“权领”,而且就挑了那把白玉的戒尺,于是娘娘更加器重这个未来的养子了。
编书者通过对芳兰一而再,再而三的叙述,不但是情节本身的需要,更是为了突出芳兰非凡的聪明与才干。文艺作品都擅长用重复的修辞方法来烘托人物性格。《珍珠塔》里的小姐陈翠娥在九松亭“赠塔”一回书中,反反覆覆地对方卿说“干点心,千万要留神”,使得方卿差点儿将“干点心”(实质是价值连城的珍珠塔)退回去;在本书《文宣荣归》一回书中,芳兰因为不好意思问文宣是否已经结婚,几次欲问又止,便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了三遍“是娘娘与大爷做格媒”,体现了当事人这时矛盾的心理。在这回书里又成功地采用了这一修辞手法:如果徐上珍不同意让元宰认养母,娘娘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个“小金贵升”了。所以在元宰告辞后,娘娘连续三次重新叫他“回来”,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娘娘当时复杂的心理活动。
本回书的结尾也非常有趣,就在娘娘连续说了三次“回来”这一情节之后,元宰终于忍无可忍(因为他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竟发起少爷脾气来了。大娘娘一看,这个“小金贵升”发脾气来的样子,竟然也与大爷一般,于是想要领养元宰的心情也就更加迫切了——这时她已经深信元宰不是徐家的儿子,应该是大爷的骨肉。这回书结构非常紧凑,自始至终吊着听客的“胃口”,以至于让听客担心王定回徐府后,会不会真的被徐上真“吃耳光”。
还有一个地方让人回味:苏似荫先生对大娘娘见到元宰后的“失态”作了充分的渲染(眼睛像汤团、头颈像仙鹤),除了讲了如何制止眼泪水流出来的经验外,还讲了“变声”的问题,这倒不是噱头,而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生活体验。因为人在哭的时候,神经受到刺激,于是声带就变厚变宽,这样发出来的声音就变得沙哑起来,所以才有成语“泣不成声”的说法。他还说人在兴奋、紧张的时候也会出现“变声”现象,接着他又放了一个噱头:第一次上台作发言的人,因为紧张,会把“现在、现在”说成了“苋菜、苋菜”。让人觉得好笑的同时,又不得不佩服演员平时里对生活的观察力是何等的深刻,所以他们在台上才能給听客们带来如此“细”和“趣”的感染力。
本回书也只有一段唱篇,元宰向金大娘娘诉说借贷之事,由江老师用俞调演唱:“小侄登堂草不恭,家寒只得两手空。爹爹是,只为济荒把库银少,救饥民反揽自家穷。久闻尊府堆金玉,故而方才相请老封君。(插白)谅必婶母此情晓,你末慷慨情愿定乐从。若能骨肉回乡转,此德此恩常挂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