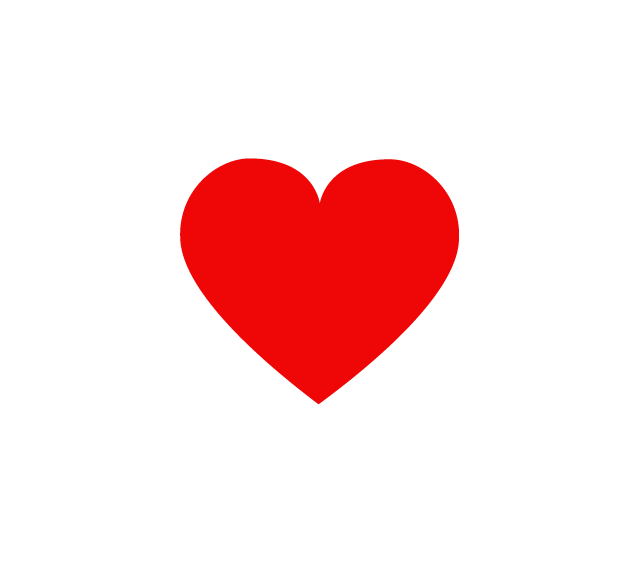在她无数个大同小异的梦境中,她总是可以看见那似曾相识的人与景。
背景是沉寂无声的黑与白,她与一群同龄人被分隔在鸟笼一般的铁栏杆后。周遭人声杂沓,喧闹不息。
只有她,睁大了仿佛能洞悉一切的水眸,缄默无声地伫立在栏杆前。
身边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被父母带走,喧嚣散尽,最后只剩下她一人。
她的下意识里反反复复地提醒她,再等等吧,再等等。直到那个白衫棉裙的女子在铁栏杆外对她伸出了一只手。
走,殳然,我们回家。
指间相触间,电石火光,石破天惊。
她浑身颤栗地从床上挣扎着醒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呢喃。妈妈,妈妈。
窗外群星黯然,天际泛着鱼鳞状的海棠白。她抽噎着,阖上了眼眸。

沽汀街是一条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巷,裸露出的灰色砖瓦的破败墙体,随处可见违章搭建的简易窝棚,潮湿的霉绿色路面上布满了泥泞污浊的鞋印。
这场雨季结束后,迎来的是绮丽恢弘的仲夏。伴随着夏天的到来,一场盛大的别离也在悄然而至。
那日他如往常一样回到了家,却看到空了半壁的房屋。母亲画着精致明丽的妆容,兴高采烈地楼搂住了他。
“言泽,你爸的官司终于打赢了。”
那刻,他感到心脏剧烈地跃动。这是他想要的,却也不是他想要的。
来接他离开的车辆无法开入狭小的巷子,他只能徒步走到外头的大街上。
途径殳然家的时候,言泽看见如他们第一次遇见那样,少女专心致志地低头阅读,青葱白玉般的指间抚过一页页。周边开着大朵白粉的花朵,她像一只卑微而羸弱的雀,再也飞不出这无望的铜墙铁壁。
而他,就要飞回到那片属于他的天穹。
她的名字是夜里海波上的光,不留痕迹地泯灭。
很多时候,命运的狰狞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浅显。
言泽转学离开的第三天,便看到曾经的班群里正如火如荼地讨论着佟殳然被学校开除的消息。
他如遭雷击,颤抖不已,半晌才打出了一行字问其缘故,但发出的消息很快就接二连三地被淹没。他急不可耐地想要继续追问时,一行简短的字如碎筋断骨的利刃,剖开了他的双眼。
“她怀孕了。”
是在沽汀街尽头的江边找到佟殳然。
她穿着印有素色藤萝纹案的棉布白裙,柔软如水藻的长发挽成了优雅的结。站在江边高高的堤坝上,仿佛一只随风而逝的羽蝶。
他的呼吸急促而紊乱,三步并作地冲上前去,大声咆哮。
“你被退学了?”
“是。”
“因为那个姓苏的……你们两人……”
“是。”
“……你到底想如何?!”对方淡然自若的神情更加激化了言泽的情绪,前所未有的怒意撕碎了他的理智。
他用力扼住了她细瘦的手臂,第一次,他用如此肮脏龌蹉的言语去骂她,嘲讽她,激怒她,就像是被逼入绝境的小兽。
殳然不气不恼,抚过一丝被江风吹得凌乱的发丝,静默地笑,“言泽,你不懂。”
他是不会懂的,永远不懂。
在那个狂风骤雨的夜,在苏老师家帮忙做家务的她被刚回到家的苏老师扑到了地上。
她闻到了铺天盖地而来的酒气,耳畔萦绕着一声声含糊不清的呢喃,“殳然,殳然……”
原来,这些年来,苏老师对母亲缄默无声的爱,早已潜移默化地转移到了同样聪颖美丽的女儿身上。
酩酊大醉的苏老师疯了一般地撕碎她的衣服,她挣扎时瞥到了从他口袋掉落的医院汇款单。
她咬着唇,闭上了眼。
可这一幕,落进了因不放心苏老师而紧随其后追来的同学眼里。
所有的气味,声响,轮廓与温度。
喧嚣磅礴的爱与恨,都被投入了深不可测的时光罅隙中。
那些无法言喻的情愫下落不明, 徒劳无功。
言泽回忆起那天大雨滂沱,她那坚韧而悲切的目光;想起她在花海中读一阙诗,安静而内敛的模样;想起她在遥远的主席台上演讲,周身那不可一世的光芒。
言泽阖上了眼,删掉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时光之力无所不能,他无力抗拒,终于无声妥协,向这骇人的命运低头臣服。
此后的两年,他逐渐像最寻常不过的豪奢子弟,浑浑噩噩地读完了高中,遵循父母的意思上了一所当地的财经类私立大学。
而言泽父亲的生意自东山再起后,愈做愈大,逐渐风生水起。虽再不及当年,但在同行同业中,也颇有口碑与影响力。
在大二的尾巴上,他遇到了一个人。
确切来说,是对方特意来寻他的。
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苏老师。
对方不知用何种方式寻到了言泽的学校,言泽见到他时,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文质彬彬的年轻男人已是憔悴萎靡的模样。
他局促不安地站在校门口,踌躇了半晌,终于表明了来意。
三个月前,殳然的母亲终于与世长辞。而殳然一声不响地带着母亲的骨灰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即便寻遍了整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就像从未存在过的星光,不留痕迹地消泯。
殳然没有什么朋友,曾经关系好的只有你了。我已经穷途末路,所以才从你曾经的同学那里,要到了你的联系方式。
请问……殳然最近和你有联系吗?
言泽猛地痉挛了一下,一股被他刻意抑制了多年的悸动,在灵魂深处复苏,化作了暖流,撕裂冰封多年的心河。
“你再说一遍,她母亲怎么了?”
苏老师似乎被言泽剧烈的反应惊到,怔了怔,“三个月前,去世了。”
“什么原因?”
“肺癌……很早就发现了。怎么,她没有和你说过吗?”
有什么在大脑间分崩析离,须臾间,他明白了一切。
言泽跳上了车子,疯了一般直冲沽汀街。
曾经破旧腐朽的沽汀街口已挂上了醒目的拆迁警示牌,言泽绕过了几辆横在巷口的挖掘车辆,刻不容缓地冲向那个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小院。
那个藏在芭蕉叶下晶莹剔透的玻璃罐早已泥泞不堪、空空如也,只剩一张破损得面目全非的小纸条静静躺在罐底,等待着岁月的使者将它忆起。
言泽捏着那一页纸,一瞬天昏地暗,血液逆流。
——你使我在花丛中绽开生命,又在美的形象摇篮里摇我入睡。
——你将藏匿于死,又在死里重获新生。
牢笼中苦苦挣扎的金丝雀终于获得了自由与新生,可他却再也找不回那片曾属于他们的苍宇与花海。
我们将有一天会明白,即使是死亡,都不能停歇我们灵魂的悸跳。
言泽毕业后来到父亲友人的一家金融证券公司实习,因绝美年轻的外表,可圈可点的成绩与坚如磐石的背景,追求他的女生接连不断。
他也陆陆续续地谈了几个女友,对方都是温婉可人的模样,可过不了多久总是不欢而散,屡次三番也逐渐没了打算。
他依然会想起她,在阳光充沛的夏日午后,在大雪飘飞的寒冬黄昏,在某个落雨伶仃的无人街角。
也曾回到沽汀街,那里已被夷为平地,新的大厦即将拔地而起,那些年少的痕迹灰飞烟灭,泯于无痕。
而殳然的父亲因无钱赌博而去抢劫,四处逃逸后在临省被抓捕归案,锒铛入狱。
他们并不算青梅竹马,在那些年里,她是属于所有人的,被成群的男生追求爱慕, 被所有的女生排斥诋毁,被街坊邻居评头论足。
而他,不属于其中任何一列,所以才与她保持独一无二的距离。
仲夏来临的时候,言泽结束了短暂的实习生涯。
那日,他在咖啡厅约见一个重要生意伙伴,对方比约定时间晚来了一个多小时,言泽正焦灼不安地等待时,手机嗡嗡地震动了起来。
“喂?”
“喂,我是佟殳然。”
他起身夺门而出,与刚赶到的客户擦肩而过。
他们在飞机场相见,她依旧是话不多的模样,静静地看着言泽笑。唇角轻抿微翘,如同一束皎洁无暇的白月光。
他们来到五年前最后一次相见却不欢而散的那条江边,充满着无数回忆的沽汀街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只有这条开满了海棠花的江滨路一路往昔,恪守回忆。
两人默默无言,沿着一望无际的江畔一直走。
仿佛这样便可以去往那无法企及的未来。
她说起了那年她回到老家,万念俱灰地埋葬了母亲后,偶遇了一位来自外国时装界的大亨,自此义无反顾地去了巴黎。
这些年来,她去过巴塞罗那,瑞士,芝加哥……一路上碰到形形色色的人,艺术家,摄影师,地产大亨。
一路坎坷,趔趄摔倒,再艰难爬起,最后鱼跃龙门。
她裸露在外的小腿上有一道细密狰狞的伤疤,那是一年前她在拍摄一组写真时,不慎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摔下。
说起这些跌宕起伏与惊涛骇浪时,她面带浅笑,漫不经心,仿佛这一切于她只是烟云过往,是别人的笑谈,而她本身只是一个红尘过客,一只途经天穹的飞鸟而已。
华灯依稀时,他们在露天的观光长凳上坐下,殳然侧头问他,“你觉得命运是什么呢?”
“命运无非取决人生的每一次脉动悸跳,这百转千回都在取决人怎么活。可人究竟如何去活,又怎么能说得清呢?”
殳然没有接话,只是在明灭的霓虹灯光下不留痕迹地叹了一口气。从他的言行谈吐中可以看出这些年他所经历的大风大浪,她没有再多问,她清楚他们不再处于同一平行线上。
那些年少仓促而缱绻的梦,在这始料未及、无法窥探的、无从抉择的殊途上,早已遗落亿万光年外,消泯得悄无声息,不留痕迹。
他于她,不同那些摄影师,导演,艺术家……她与他们彼此羁绊,彼此利用,彼此依附。
而他只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男孩,像是一棵扎根在她牢笼门前的一棵树,绿荫成碧,日夜交叠,四季轮回,缄默无言地陪伴在她身侧。
有太多的故事,她都未曾对他开口说过,并不是难以启齿,只是不知从何处说起。
比如那些不劳而获的财产最终没能救下她母亲的生命,在她离开时,那些不义之财被转赠给本市的福利院。
比如三年前那个公布拆迁的夜晚,她与苏老师在这条江滨路上漫步。而赌光了家当的父亲从天而降,扬言道,只要苏老师给钱,他愿意把亲生女儿卖掉。
那一瞬,她万念俱灰,闭上眼纵身跳入了波涛汹涌、浑浊不堪的江流。
他不知道,在那刹那,心如死灰的她,也想过死亡。
流年翻转,事过境迁,如今这些早已不再重要。
殳然在这个城市呆了一周,并邀请言泽一起去敦煌旅游。
他们踏过了漫漫黄沙与沧桑古城,在佛像下跪拜并虔诚地念诵佛经。当石壁上轻歌曼舞的女神的目光轻落在他们的灵魂上,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和释然。
他们走很长的路去看长河落日,当那寂寥的炊烟袅袅升起时,言泽用力地拥抱并亲吻她,仿佛从此便要将彼此的生命相交相融,再不分离。
在第七天的黎明,她再次不告而别,只留下一枚小巧玲珑的戒指给言泽。
他坐在古城墙上仰头,看见大群自鸣沙山东麓向三危山飞行的黑鸟,言泽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并将那枚戒指藏在了古墙下的石洞里。
这是他们相识的第八年,此后不再相见。
他只能用余生去回忆她。
此去经年,世事变迁。此后言泽在父亲的协助下创办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人们都说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却不知他也曾有过一段晦涩黑暗的过往。
在此后他再次遇见了一个同样喜欢泰戈尔的女孩,她笑靥如花,十分欣赏与理解他。
而后岁月仓皇,他终于也做了父亲。
可他仍旧会想起殳然,那个曾与他一并逆行在时光中,最后彼此走失的女孩。某个恍惚,他仿佛还可以看见那破落的旧院里,她轻轻读诗,隐忍,苍凉而挣扎,宛若一只即将振翅欲飞的金丝雀。
在他二十九岁生日那年,他收到了一本匿名寄来的书,在扉页上有这样的一段手写体。
当我带来,你在草地上
给静止灌注生命
然稍有风吹草动
你随时预备逃走
当我离开,你在春藤里
是你,黑鸟,我所爱
《格兰摩尔的黑鸟》节录
在那一瞬,他彻底释怀,也彻底明白了殳然。
他们曾一起被禁锢在命运的囚笼中,朝暮相伴,共同守望。可终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挣脱开命运的桎梏,彼此挥别,展翅高飞。
无论他们归途何处,终究都能在同一片碧蓝天宇下,自由而鲜艳地演绎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