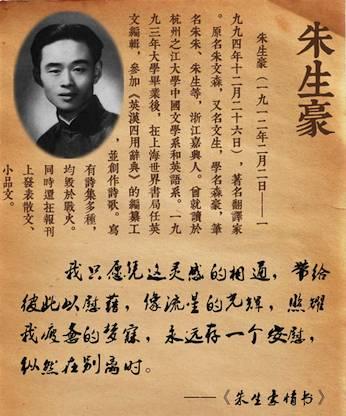今年适逢文学巨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近期以来,关于他们的话题绵延不断:
《玉茗堂四梦》主人携庙会戏台上的《牡丹亭》登场,应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推广汤显祖、重温莎士比亚的煦风中,两位穿越时空的“对话”、爱情观比较之类关涉“文学”的论题频繁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说到文学,老生常谈的话题自然少不了《红楼梦》,从曹雪芹诞辰300周年(2015年)延续下来情结,在际遇莎士比亚的日子再掀波澜,脱俗之人欣然招魂莎士比亚,让他“重写《红楼梦》……”
无论是业内,还是坊间,人们不经意地就营造出一个文学江湖:戏剧的汤显祖、小说的曹雪芹,相比莎翁如何?
《不列颠百科全书》表示莎士比亚“被广泛认为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没有哪个作家的声誉能真正同莎士比亚相比”。对此,用中文写字的人显然不太愿意接受。
精致的《红楼梦》与“粗陋”的莎剧
客观说,杰出的文学作品屹立于各自的高原之巅,无高下之分。不过作为好尚殊异的旁观者,将作者放在案头分配情怀也无可非议,何况还有无出其右之说。
何者更优?非学术判断通常从两方面来解读,一是故事的阐述方式,比如文辞语句的微叙事和运筹帷幄的宏大构架,另一则是思想深度和文化源流的持续影响。
就叙事而言,《红楼梦》的精巧无与伦比,机锋、典故无处不在,华语圈的各种文学体裁、各类人物魂游其中,“杜工部的沉郁”不过是史湘云闲暇的谈资。品味的雅致、文化的韵味更是弥漫整个大观园,连不识字的丫鬟,学问都可以比肩当下的知识分子。像贾母身边的鸳鸯,闻劝其为妾的“好话”,随口便说:“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在今天,不要说科学家,就是嗜古文人,不识鹰马出品工匠的大有人在。
总之,《红楼梦》被奉为圭臬并非浪得虚名,尤其是对那些致力于文学写作的人来说,其人物描绘的生动、场景刻画的传神,无不是教科书中的教科书。于是,圣典地位确立,颂赞辞藻堆砌。面对汗牛充栋的拥趸笔墨,想表达小说人物繁杂过多、铺陈迂腐虚饰的观感,必须在高声溢美之后委婉细语。
《红楼梦》在文人案牍从诞生之日起到今天,一直尊享极品地位。反观莎士比亚,虽然名利双收,但桂冠的获得就没有那么顺风顺水。
莎剧发迹于贩夫走卒之肆,在其同时代的文学巨匠眼里,比如本·琼森,“缺乏艺术”是中肯评语。其后的两个世纪,抨击莎氏作品“相当拙劣”的大有人在,幸得有慧眼大师推崇,如德意志的莱辛,莎翁才没有沦为被遗忘的小财主。当然,还有卡莱尔,他说莎士比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进入19世纪,关于莎剧,细节自相矛盾、冗长且低级趣味、人物形象荒诞可笑等标签依旧流行,连奋力为他抬轿子的歌德都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十分滑稽”,主人公“让人难以忍受”。
在书斋之外,人们也有机会听到《红楼梦》不好看,或者看不懂的流言,不过这种“外行”话流转到专家那里,却诡异地成了另类的赞美之词。
一个在批评中屹立不倒,一个在颂扬下呵护有加,两部作品的命运并不相同。
《牡丹亭》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
文学魔力和故事的情节有关,但本质影响力取决于故事蕴含的思想,就像人们在论述伟大的曹雪芹时,很难避开的表述: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溃散的历史命运。这种论调搞笑吧?但所指就是思想。不仅哲学家,经济学家对思想之力也有洞悉,凯恩斯和哈耶克就得意地布道:危险的,导致社会演化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显然,想证明文学作品的伟大,就必须暂弃情节迷恋,返身思想辨识。
落泪黛玉葬花的心智,从思想角度看,于世于己当无太多助益,而《红楼梦》的庞大繁复,难免沾染道统的旧文学淤泥,“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陈独秀)。所以呢,喜欢好说,思想却很不好说。
好在有《牡丹亭》,这部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时代(16世纪)、内容主题等方面有着相似性的戏剧说明,相较于“粗鄙”的莎先生,汤显祖只高不低。
其实拿不同文化体间的戏剧来PK不太合适,不过思想层面的拔高可以有。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就被称为是对自由的追求,显示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欲望导引下的叛逆爱情是个性解放和自由向往吗?
不错,莎剧的人物确实荒诞,但并不可笑。这正是文学超越文字范畴的另一面。哈姆雷特和普通人一样,优柔、焦虑,但不失坚毅的决然之心。荒诞(或者说完整)人性的发现是大师的杰作,回视当下的主流文化,为什么高大全的形象仍矗立在不容置疑的位置上?这是思想的影响力。
再聊自由。“罗密欧”剧实际上不是关于自由的叙事,它演绎的是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丧失独立个体意志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死亡不是为了获得爱情,而是向否定独立精神的旧世界(世仇)宣战。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被枷锁羁绊,没有欲望的自由,只有作为个体存在得到被尊重的自由,这是超越个别文化体系的。
回来看《牡丹亭》。我们不妨回到晚明,人们一直很困惑那个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光。“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大思想家黄梨洲的现代思想,为什么没有长出民主制度的树?自由、民主需要以个人权利作为基石,没有土壤,在一个完全忽视个体存在的环境里,所有关涉“君为客”的说辞不过是空想。
现实里,明清以来恋爱自由了吗?大观园里《牡丹亭》的粉丝选择的是自由吗?不是,徒增几分幻想而已。
西方与东方的视野
上世纪80年代初,大二的我正寻求阅读所有可以找到的莎士比亚著作,同屋的阿平则抱着汤显祖摇晃。待到我的莎士比亚收官,他还在研究《牡丹亭》。
“汤显祖比莎翁伟大。”阿平认为。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玉茗堂四梦》,也不知道有西方文化霸权,再加上明白诗词翻译会遗失语言音韵本身的味道,所以真的无从评价。但没认真读过莎翁作品的阿平知道。
现代以来,曾经的西方文化中心视野不断地被他们自己矫正,而我们则正走在他们的老路上意图重现雄霸之光,王国维将《红楼梦》提升到“宇宙的”境界还不足以满足痴迷者的欲望。
大约是认识到静安之语有些坐井观天的虚妄,或是觉得与废话太过相似,刘再复先生觉得《红楼梦》呈现了存在论哲学家焦虑的核心问题。这太深奥了,一帮子类型化的角色会怎么传神地表演荒诞的存在(生活、人性内在的冲突)呢?也许曹雪芹笔下生动的人物经过观者想象可以脱离类型化锁链。
在我们发力推高英雄的时候,晚近的莎士比亚却在去光环化。西方的学者,如戴维·卡斯顿,以及巴尔赞,告诉人们,今天看到的大师是18世纪之后才现世的,是被各色各样的人改写后的莎士比亚(他初始的剧本已经无迹可寻),而不是那个编写剧本的莎士比亚,但这无伤莎翁的伟大。他是首位打破了类别和阶层界限,将完整的人性,而不是类型化木偶搬上舞台的大师,国人类似的模仿迟至《雷雨》才出现在舞台上。
实际上我们识读的莎士比亚早已被重新构建、改写,不仅是文化符号,还是思想旅途上的重要驿站,曹雪芹或者汤显祖是吗?
曹雪芹、汤显祖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任何一位文学巨匠进行心灵对话,他们在肯定人的欲望、歌颂自然的人性方面有共同语言。但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路径被这些作品改变了多少呢?
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理解和参与是伟大思想确立的基石,珍藏在文人的斋室里会是什么呢?这大概就是曹雪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区别吧。
(插图 李法明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