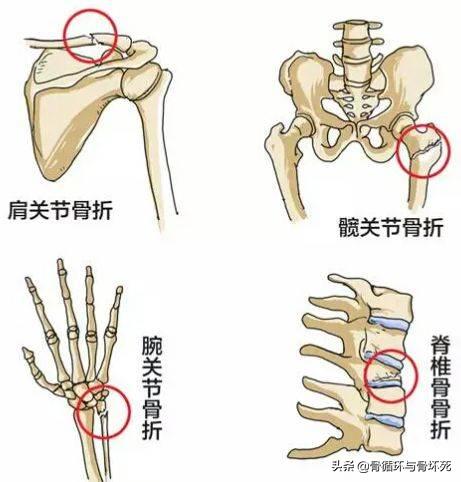图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文章内容不代表本人立场,杠精勿扰。
written by曲辰

《国宝》,吉田修一/着,刘姿君/译,新经典文化
《国宝》总处在一种「将要消逝」的时间状态之中,用张爱玲的话,就是「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而在这即将到来的败亡前,用自身的肉体升华为艺术并抵住毁灭,便成为这本小说角色的发光之所在。
如果自出云阿国起算,歌舞伎至今约莫有四百余年的历史,在这段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确立了无数的「型」供演员模拟与驱使,也就是有一套标准的身体程式来决定演员该怎么动、怎么走位、怎么扬首低头。而在这一套「型」之下,则藏着每个演员各自的「芯」,不断微调着既定的型,好符合自己,也符合这个时代。
吉田修一的《国宝》,毋宁是这种「型」与「芯」的结构缩影。
初读此书的读者,恐怕都会讶异于这本看似庞大(字数上)而沉重(物理上)的小说读来竟如此轻易,事实上,《国宝》原本是在《读卖新闻》上连载的小说,作者巧妙地将连载的字数限制以歌舞伎的形式包裹起来,透过大量的旁白与外声腔的介入,简要而干净地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但当遇到需要迫使读者睁大眼睛观看的部分,则如同歌舞伎时常会慢动作演示的杀阵,或干脆停格作为足以拍成明信片的「见得」一般,放慢语速、焦点缩得极小的细密的描绘给读者看到。
这种文字版的「子弹时间」所想讨论的——也就是这本小说的「芯」——固然是在书中反复提问的,「为了艺术,一个人到底可以承受多少,又做到多少」 ,书中的师徒三人,几乎都是以某种与舞台共存亡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艺术至上主义的精神。但更引起我注意的,则是这本小说刻意渗入的某种衰亡的时间感,以主角喜久雄为例,他的父亲就算没有死于帮派械斗,但黑道在日本如今已然凋敝,他的母亲则死于原爆后疏于照护的结核病,他自己则投身于一个只能以「无形文化遗产」封存的行业。这本小说总处在一种「将要消逝」的时间状态之中,用张爱玲的话,就是「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而在这即将到来的败亡前,用自身的肉体升华为艺术并抵住毁灭,便成为这本小说角色的发光之所在。
《国宝》之好看毋庸置疑,只是我还是不太确定,为什么吉田修一需要一厢情愿地让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退位为舞台上的黑衣,她们当然各自有各自的个性,但当面对了「艺术」的时候,成全似乎成了她们唯一的选择。面对曾写过《恶人》或是《再见溪谷》的这位作者,我不免有些遗憾。
⊕书籍资讯:
《国宝》,吉田修一/着,刘姿君/译,新经典文化
1964 年元旦,长崎料亭的初雪中,这个国家未来的国宝诞生了──「好精彩,长崎竟有如此出色的艺伎。」「不,那不是艺伎,那是立花组老大还在上国中的独生子。」
梨园与黑道,出身截然不同的两名少年,被命运带上同一条求艺之路。「你看,膝盖打开到这个角度,会让身体显得最大……很神奇吧。」「这张脸蛋真漂亮……只不过,总有一天你会被这张脸给害了。」历经血腥、冲突、丑闻、背叛、成名、离散……最后,谁能坐上人间国宝的王座?「你恨透歌舞伎了吧?可是,再恨也要跳……再恨我们演员每天还是要上台。」「没事的,我早有觉悟,因为我实在太爱歌舞伎了。」
艺道一门的情仇纠葛,为报杀父之仇的一生执念,掌声与眩光背后,是戏子风云变幻的一生。
⊕延伸阅读:
《火花》,又吉直树/着,刘子倩/译,三采文化
我们总是对「技艺」有所憧憬,会对那些为了追求梦想与打磨自身,牺牲近乎生命中一切的人由衷感佩,所以《国宝》、《蜜蜂与远雷》都格外撼动人心。可是,「搞笑」可以是个技艺吗?又吉直树的《火花》或许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搞笑艺人其实不需要磨练什么,但事实上从措辞的选择、搭话的节奏甚至是肢体抑或是看向观众的方式,都会决定一个艺人的「格」,而再往下深挖,甚至还会关乎于哲学、或什至存在的议题。想来颇有些不可思议,但别忘了,歌舞伎原本也只是在江户街头表演的野台戏之流而已。
新书资讯员|曲辰
一个试图召唤出小说潜藏的世界样貌的大众文学研究者。相信文学自有其力量,但如果有人能陪着走一段可能得以看到更清晰的宇宙。曾编选《文豪侦探》、《文豪怪谈》(独步出版),评论文章散见诸多出版品。现有Podcast「独角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