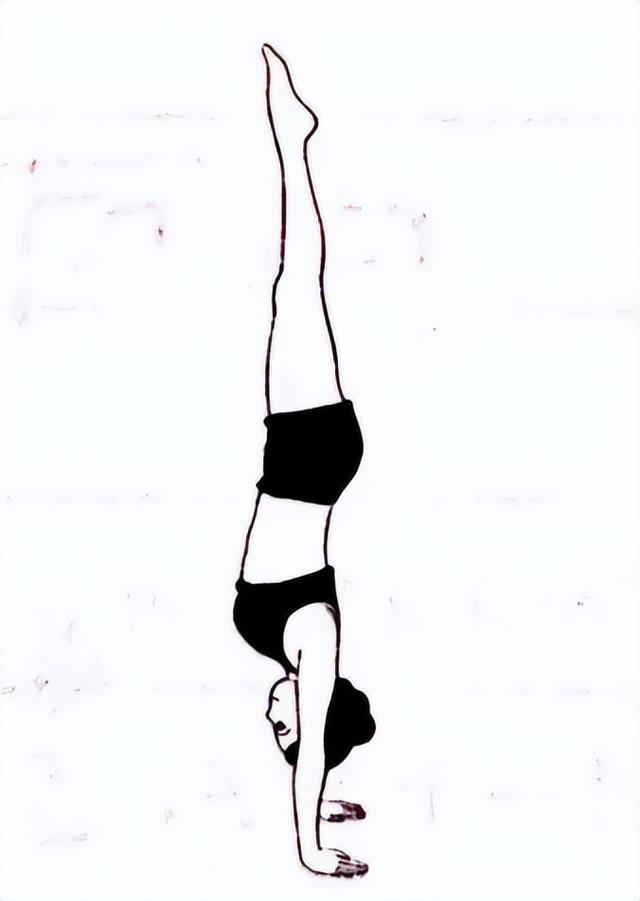2022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中国生态文学论坛”6月5日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表示,能在自己的写作中传达尊重自然、认知自然的观念,是个人写作上一个小小的骄傲,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阿来的写作技巧是什么呢?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阿来的写作技巧是什么呢
2022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中国生态文学论坛”6月5日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表示,能在自己的写作中传达尊重自然、认知自然的观念,是个人写作上一个小小的骄傲。
“此次临行前,有同行对我说,你这是跨界,从文学跨界到社会学,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感觉。”阿来说,人本身就是自然演进的结果,也是地球生物圈的基本成员。在他长达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大部分作品都致力于写出人类社会的丰富与复杂,同时也写出人类所依存的自然环境的真实状况。“写出一个时代人类社会从个体到机构到团体,几乎无限的增长冲动与物质消费欲望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他说。
阿来的作品《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并称为“自然三部曲”。其中,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蘑菇圈》写的就是富裕起来的人们对松茸近乎痴狂的消费如何造成边远地区生态的紧张。
他的关于汶川地震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花了大量的篇幅,着力于岷江干热河谷地带自然的修复与重建。他说,有一位对生态问题有严肃关注的批评家统计说,《云中记》中写出了有名有形的三十多种植物,并考证称那些鸢尾、丁香真的就生长在那些村庄所在的海拔高度上。“在中国文学还普遍缺乏科学健全的自然观时,能在自己的写作中向社会、向读者传达尊重自然、认知自然的观念,也许效应微弱,但也是我个人写作上一个小小的骄傲。”
如何把对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认知融入到文学作品,融入到创作实践中?他认为,要坚持知行合一的传统。“我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志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向科学家学习,向所有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成绩的人学习,与他们同行、共同提高。”他说,一个作家,首先是参与见证,其次才是书写记录。
-
对话
作家采风调研不是功利地找素材,首先要参与见证
新京报:作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你一直关注环保议题,目前你的哪些建议或者议案得到了推动?
阿来:我觉得是一个群体在推动,不能夸大自己,但是我确实参与了一些相关工作。因为我们经常到自然界中去,了解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建议可能更有针对性。
比如建立国家公园或者生态保护区时,一些原来生活在其中的老百姓需要迁移并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自觉维护生态,首先应该让他们从维护生态中得到利益。
新京报:保护环境跟经济发展要如何平衡?
阿来:目前,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不能生产,大部分居民要退出,对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所以需要国家财政对百姓进行转岗安置,让他们经过适当的培训后成为做生态维护工作的人,比如养护森林等。
以往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但经常是阶段性的,这样的工作需要有连续性。
新京报:你提到几天前在四川北部探访森林中巴蜀古道遗址,和当地探讨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当地的现状是怎样的?得出了相关建议吗?
阿来:这些地方对生态环境影响小,当地老百姓的出路就是所谓的文旅融合。我不觉得一个作家到哪里就是功利地去找自己的写作素材,首先是参与和见证,其次才是记录。
我们去探寻的古道被森林“淹没”了,未来是要修一条大马路进去,还是将十几公里发展成更适合旅行的徒步线路?我不建议修公路进去,一方面会对森林造成破坏,另外从文化意义上来,古人走这段路时也是在体验它。徒步用不了太长时间,只要三四个小时。其实景区也可以诱导现代人改变旅行方式。
新京报:你参与环保志愿活动和调研采风,有哪些收获?
阿来:我参与的环保志愿活动有科学家参与,我会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现在有的草原要求禁止放牧,我们有科学家小组在三江源地区调研,长期观察发现,有的草原尽管完全没有人放牧,还是会退化。
因为植物要开花、传粉,适度的动物和人的扰动,对传粉是有帮助的。现在野生动物跟昆虫都减少了,所以适量的人类和其饲养的牲畜,反而有助于植物传粉。这个研究项目还有待观察,但初步得出了这样的认知。这不是调研一两天找题材就能发现的,只有长时间和科学家在一起工作,才能了解接触前沿的知识。
新京报:你为了写自然题材,也曾经学习植物学和地理学知识?
阿来:书写自然的时候,对它一无所知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学有一个问题,只写人跟人,自然偶尔出现,也是作为背景和风景,树、花、鸟都处在“无名”状态。
新京报:生态文学在中国应该如何发展?
阿来:文学有两个圈,一个是人的社会圈,一个是生物圈。生物圈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但是大家只注意到人和人际关系的问题。虽然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亲近山水自然的传统,但只是出于古人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不是基于科学的系统。
专业人士有科学的认知,但也要让中国公众有科学的生态意识。
新京报:让大家通过文字关注自然,是中国作家的使命感吗?
阿来:我觉得要慢慢建立环境自觉,这是中国现实的需要,民间有各行各业的人投入环保志愿的行列,但目前没有变成大部分人共同的意识,比如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更加低碳,诸如此类。
中国作家和作品一定会在这方面起到作用,一个人这么做,恐怕作用有限,但当我们成为一个群体,很多知识和正确的理念、方式就会一点点扩大和互相影响。
作家本身会寻找新的写作领域,在关注社会发展问题时,会注意到生态问题是如此突出,这是我们吸一口空气、喝一口水的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影响我们。
新京报:你考察过很多地方,是否觉得中国环境呈现出变好的趋势?
阿来:那还是有,保护环境在慢慢形成社会共识。公众要从自上而下的服从规则,转变成自觉的行为。如果有一半的人自觉爱护环境,就会形成习惯,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就会对少数人形成某种压力和强制,变成道德约束。
新京报:去年,你担任了“四川环保大使”,是如何履职的?
阿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了四川、重庆两地作家环保行,以嘉陵江为主题。嘉陵江穿越的地区包括青藏高原东部森林草地、中间还有像九寨沟这样的风景名胜,下游又是农业和工业高度开发的城市,这样全流域的生态发展可以说是长江或者黄河的缩影。
我觉得要选一些确实能引起大家感触的点位,让不同的作家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入手。
新京报:你是2022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此前提到要考察黄河源,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阿来:当下,四川省正在筹划若尔盖草原建立黄河国家公园,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大概本月底开始,我会做一次黄河源的生态和文化考察,预计花两个月时间。我曾经多次和黄河源擦肩而过,现在我60多岁了,将来应该不会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今年去完成这个计划。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张磊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