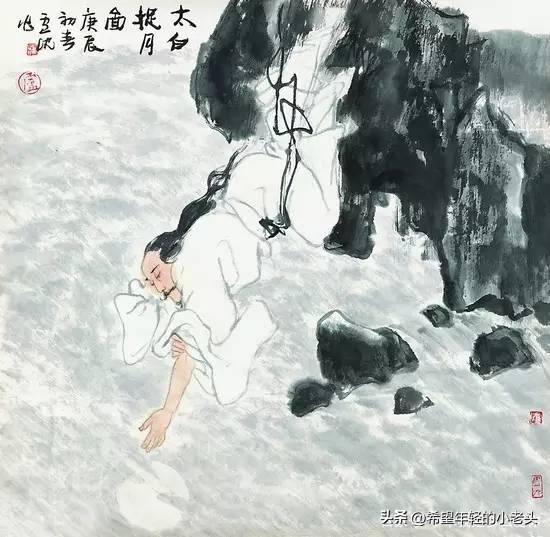“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千百年来,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为什么她非得要代父从军?
因为“昨夜见军贴,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因为“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不去不行吗?
文献证明,不去,还真不行。
木兰生活的朝代,大约是在北魏时期,那时候,朝廷实行的是府兵制,将一部分民户划为“府户”,不需要交纳人口税,但是,他们世世代代,必须服兵役,要上战场时,每户更是要出一名男丁应召出征。
从“卷卷有爷名”看来,木兰家,就是当时的“府户”,她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让老父亲上阵,要么自己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并且从军的所有费用、马匹都要自己解决,于是,木兰只能东西南北市地采购从军所需的物品。
这样的府兵制,一直延续到隋唐,中晚唐以后,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随之兴起的,就成了募兵制,当兵参军,已成了自愿,而非强制。
但是,这些招募来的士兵,国家是需要支付他们的薪水以及衣服鞋帽柴炭补贴的,没有充足的国库,根本无法支撑起来。
宋朝以后,这种需要充足国库支撑的募兵制,再也发展不起来,反而,又实行了北魏隋唐时期的府兵制。
这究竟是统治者,治国手段的进步,还是退步?
一位加拿大学者宋怡明,将用他所编著的一本书——《被统治的艺术》,引导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别看宋怡明教授是加拿大人,但是,他普通话流利,为写出这本书,他有近三十年田野调查经验,收集了大量家谱、地方志等第一手民间资料,很多中国人都不曾翻看的民间资料,他以学者治学的精神,一一查阅。
没有防伪身份证的从前,户籍制度就是管理工具
在古装影视剧里,我们以常能看到这样一些避世的桥段:某某从此找一处无人认识的乡镇,隐姓埋名,远离与那个曾经让他操心劳碌的世界。

于是,不少人就认为,古代反正没有网络,没有防伪身份证,去到哪里,重新生活,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人口流动并不大的古代,你以为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安家了?
恰恰相反的是,当一个从没见过的新面孔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也许就会被路过的乡亲向上级举报。如果来的人,恰好是犯了事的通缉犯,而当地村官没有及时举报,自己则可能背上窝藏罪犯的罪名。
因为在没有防伪身份证的从前,每一个地方的户籍册上,都清楚地记载着,所有人的生卒、家庭信息,什么时候张家添了丁,李家发了丧第几个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都会被记录在册。
这样的户口档案,在中国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
有关于户籍制度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唐文宗太和四年,属于国家下发的定税文书,交了税的每户人家,就颁发给一户户籍。
到了明朝,朱元璋在借鉴之前各朝代户籍管理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成熟的方法,既是对以往各朝代管理经验的继承,又结合了自身的实际进行了创新,称之为——黄册制度,使统治阶级,对国家人口状况、赋税核定等有了更强大的依据,从而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
明朝的户籍档案,与现代身份证的作用十分相似。册子里记录了每一户人家的人口、财产、籍贯等,且每十年定期更新造册一次,期间如果人口信息有变动,则由地方管理者及时更改。
任意地去想去的地方?没有入籍,就没有身份
现代的年轻人,身在外打工,租着房子居住,在A城市打拼,觉得不爽,退房去到B城市,住了一段时间,觉得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于是又到了C城市。
换一种职业换一种活法,这种生活方式,在如今很常见。
然而,这种人,在明代,称之为——“流民”。
出身平民的朱元璋,深知,历代大乱,许多都是由流民牵头而起的。这些流民,有的人,恰好有着,一般农户所没有胆量与能力,正是这样到处游走,鼓动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

于是,他规定,每个人,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社会上,不许存在无业流民,同时还要乡里乡亲都知道彼此的职业,所有人,都要入籍。
各地父母官、村官,对这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要告诫,要规劝,要他们立即找活干,然后把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就归什么户种,都写到黄册里,包括他几个老婆几个儿子,挣下了多少家产,家产怎么分,应该纳多少税……等等。
于是,各地父母官、村官不敢怠慢,纷纷给自己管辖地上的居民发户贴、造册,让他们入籍,其力度,不亚于今时的各类登记检查。

民户、佃户、茶户、马户、矿户、匠户、织户、船户、商户、营生户、铺户、盐户、军户,合计14种职业户,总有一种,符合其职业。
户口还分三等,民籍、军籍、匠籍。
民籍属于自己组织生产和经营,按时缴纳赋税的百姓;
军籍、匠籍,分别指军人和手艺人,国家支付一定的报酬。
入籍意味着什么,其实当时明朝的百姓都很清楚。
一是自己的名字与祖先的名字被记录在官府一类特殊档案中,明确了,由此会带来哪些权利和义务是自己要遵守的;
二是自己的身份阶层与其他类别人群间的社会关系,得到确认。
明朝统治者,正是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把人民紧紧控制在手中,防止人户随意流徙,动摇赋役根基。
户种对应福利,也关联着世袭的责任与义务
事实上,明代所有户籍类别,理论上,都是世袭的:
盐户必须 世代负责生产食盐;
匠户必须世代为官家的手工作坊干活;
民户必须世代服徭役并以实物或工钱纳税;
军户则必须为军队提供军士,守卫指定的驻地,但免除徭役。
以军户为例,明代一户人家被编为军户的方式有四种,
第一种是“从征”,即多年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直到他登基的士兵,有一部分直接享受世袭军官的待遇。
第二种是“归附”,即被朱元璋所打败的军队里的士兵。
第三种是“谪发”,即犯了罪的充军犯人。
第四种是“垛集”,即在所管辖当地,将壮丁强征入伍,连同他们的亲属一起被编为世袭军户。
前两种在开国之后,就没有军户再通过这两个渠道被征伍,第三种也仅是少数,完全不足以及时供给兵力,于是,第四种,就成了主要的征兵渠道。
一家被编为军户,不是说所有家人都是士兵或都需要服兵役,而是这个家族必须派出一名成年男丁参军。
这个参军的任务并没有期限,而是一项持久的责任。当这名参军的男丁去世、或因为年老、疾病、丧失行动能力,甚至当了逃兵时,军户就必须再派出一名壮年男丁补充进军队。
也许你会好奇,如果正好没有壮年男丁,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又会上演木兰的代父从军呢?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军户们当然会精心策划着补充男丁的事宜,并且还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于是他们想出了几种办法,与官府同时进行斡旋。
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把家族共同的义务集中由一人履行,这个人或代表自己,或代表自己的子孙,接受由整个家族的人,共同为这个人建立起一份固定家产,从此之后,承担起整个家族的服役任务。
又或者将家族共同义务在内部的不同家庭进行轮替,其他没轮替到的家庭按人头,定时固定出一笔钱给服役的家庭,用以维持缺少了男丁的家庭生计,直到下一轮的轮替。
这样一笔报酬须得相当可观,足够养活几十人。富裕的家族成员乐意用一大笔钱换取子孙免于服役,而家境贫寒的成员也乐意为这笔收入承担起当兵的义务,正好各取所需。
但是他们也发现了一个漏洞,承担义务的人,不一定非得是本户的成员,他们可以通过报酬的形式,让外人代替自己服役。
这样一来,如果应当去履行义务的男丁拒绝参军甚至当了逃兵,不见踪影,那么官府派来的官差同样会上门,而付出的钱财,便打了水漂。
从明代开始,正式确立起来的户籍制度,同样也在现实与制度规则中不断完善,无论是怎么样的政策,入的是什么样的户籍,当时的人们,都会费尽心思,在相对简单的制度规则里,将复杂的现实进行权衡比较。在“家族”的名义下行事,尽可能地优化自己的生存处境,于是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便衍生成了生存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