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希利·浦洛基

作者|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
哈佛大学俄罗斯及乌克兰史教授,东欧诸国史研究学者,专攻俄罗斯及乌克兰现代史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一道诏书,把首都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原名称是彼得大帝所取),让这个城市的名字从纪念一位圣徒改为纪念它的创建者。更重要的是,用俄文的“格勒”(grad)取代德文的“堡”(burg)标志着俄罗斯想要切断它和中欧的密切连结。一个逐渐疏远西方的过程于焉展开,它将会在一九二○年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时彼得格勒再次更名为列宁格勒,并在下一个十年期间达于高峰。
这个更名之举发生在俄国对德奥宣战的几天后,是受泉涌的爱国热情所驱使。沙皇没有和几个主要部长商量太多便做出决定,更多是为了回应群众而非内阁的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俄罗斯首次和一个西方强权发生军事冲突。类似的事情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屡见不鲜,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人想过要给首都重新命名。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在不久前重划的边界线两侧,民族主义情绪都大为高涨,而最能满足民族主义胃口的莫过于战争。俄国人相信这场战争必然是速战速决,以胜利收场,给首都更名之举并非临时起意,却也引起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热烈欢腾。当时一份报纸这样说:“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两百多年来被称为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首都因为一纸诏书而更名为彼得格勒。在这个对日耳曼主义斗争的伟大时代里,最美好的亲斯拉夫派梦想获得了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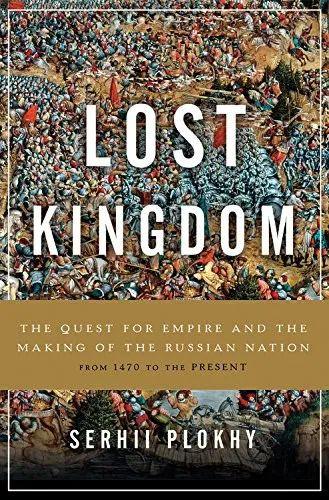
几星期前的八月二日,数以万计公民涌入冬宫前的广场。九年前的一九○五年革命就是在该广场点燃,但这一次,群众并不是前来抗议和要求什么,而是为了表现爱国热情和忠君心迹。世界知名的俄国歌剧演唱家夏里亚宾带领群众合唱〈天佑沙皇〉。当尼古拉二世出现在阳台时,群众跪了下来。他把前一天向奥地利宣战的诏书读了一遍,解释说政府此举是为了回应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攻击。宣战诏书上称:“忠于自己的历史使命,俄罗斯从不曾弃同一信仰与血脉的其他斯拉夫人的命运而不顾。”沙皇继而解释,随着德国对俄国宣战,事情攸关的已经不仅止于斯拉夫人的团结一致。“我们(WE)坚定不移地相信,”他说,“我们所有的(all OUR)忠诚子民都会和谐和无私地起而为保卫俄罗斯土地而战。让我们在这个接受考验的可怕时刻忘掉内部纷争。愿沙皇及其子民的团结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
他不是把战争说成欧洲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而是说成俄罗斯人和他们领导的斯拉夫世界对日耳曼民族的角力。冬宫殿前的群众高举着横幅和沙皇画像,位于最中央的两面横幅一面写着“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国度胜利”,另一面写着“解放喀尔巴阡罗斯”。虽然俄罗斯帝国打着泛斯拉夫的旗号对德奥宣战,但俄罗斯问题从一开始便深深被卷入其中。战争最直接的目标之一是要把基辅罗斯最后尚未收复的祖产纳入沙皇的长臂之下,也就是收复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在俄罗斯的官方术语里,它们被统称“喀尔巴阡罗斯”。收复这些土地将会完成“俄罗斯”全域重归统一。
八月十七日,俄军越过德俄边界,进入东普鲁士。官方宣传集中在强调俄国有必要粉碎野心勃勃的条顿武力。次日,俄罗斯指挥官亦率领军队,越过奥地利边境,号称此举是为了解放长期以来遭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俄罗斯人”。发生在战线南区的战争被说成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俄罗斯问题,让所有俄罗斯人重归沙皇怀抱。它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让当局可以粉碎崛起中的乌克兰和白罗斯民族运动,确保“俄罗斯民族”的完全统一。
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在战争头几个月空前高涨,让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对战争期望更殷。他们长久以来都力挺加利西亚的亲俄罗斯派,又不遗余力斗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给他们贴上俄罗斯民族叛徒的标签。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日子终于到来。
一九一四年八月入侵加利西亚前夕,俄军总司令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宣言中把这次行动说成是为解放长期受苦的一支俄罗斯人:“父老兄弟们,上帝的审判已经降临到我们!抱着基督徒的谦卑心态,俄罗斯人几个世纪以来默默在外国枷锁下承受折磨。但不管是甜言蜜语或迫害都没能折断他们对自由的盼望。就像一条等不及要与大海汇合而冲破沿途岩石的溪流,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俄罗斯人追求统一的决心。让世界上再没有『受宰制的罗斯』。”这个宣言还用了更传统和更历史的论据合理化俄罗斯的入侵:“愿圣弗拉基米尔的国度,愿雅罗斯拉夫·奥斯莫梅斯尔、丹尼尔亲王、罗曼亲王的土地,摆脱枷锁,高举伟大、单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的旗帜。”最后,宣言呼吁哈布斯堡王朝的乌克兰子民,为俄罗斯帝国的光明未来,起而反抗他们的政府。“长期受苦的罗斯兄弟们,起而欢迎俄罗斯军队吧。被解放的俄罗斯兄弟们,你们将会在母亲俄罗斯的胸脯上找到一个位置!”
“重新统一”是宣传机关在战争初期主打的口号,被用来凝聚帝国境内的民心和鼓动国外的“俄罗斯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如果说奥地利官员当初不确定俄罗斯会不会在将临的战争中打亲俄罗斯牌,那么现在他们再无疑议。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宣言让他们有充分理由可以围捕和拘留亲俄罗斯派分子。
在战争的头几星期,数以千计被指为亲俄罗斯派的人─包括知识分子、教士和村干部,被送往施蒂里亚的露天拘留营塔勒尔霍夫。在它的两万囚犯中,有大约三千人将会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许多被送入塔勒尔霍夫或另一个奥地利拘留营泰雷津的人事实上不是亲俄罗斯派,而是亲乌克兰派。这是因为,很多居心不良的人都利用战争引起的恐慌气氛向当局诬陷他们的敌人。乌克兰活动家相信他们是被波兰人诬陷。有些个案确实如此,但他们有时也会是被自己人诬陷,又或者因为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了不恰当的话。典型的情况是,他们被人听见他们说俄罗斯人的统治可让地区内的生活条件改善。大部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居民将很快知道此说是否属实。而他们许多人都失望了。
战争头几个月带给俄罗斯很高期望,但也带来了一些最初的失望。坏消息从前线的北部地区传来。俄军在东普鲁士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遭遇大败。另一支军队亦被迫撤退。但在加利西亚,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九月三日,俄军列队进入利沃夫,把它的名字从德文的 Lemberg 改为俄文的 Lvov。同一个月稍后,俄军逼近普热梅希尔,那是一个古老的罗斯中心,设有坚固碉堡,奥军在此顽强抵抗了快半年。一九一五年三月,疲惫的奥地利驻军弹药用尽,被迫投降。至此,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完全落入俄罗斯控制之下。俄方计划取道匈牙利平原,直取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让奥匈帝国无法再战。当时很少人会怀疑,普热梅希尔和加利西亚的其余部分将永远是属于俄国。下一个目标将会是匈牙利统治下的奥匈帝国的一个地区外喀尔巴阡,在俄罗斯的官方用语中是“外喀尔巴阡罗斯”。只要取得外喀尔巴阡,“收复”基辅罗斯全域的大业便会全部完成─根据俄罗斯史书记载,这大业是由第一位自称沙皇的俄罗斯统治者伊凡三世发端,时为十五世纪。
一九一四年秋天,新征服地区交由加利西亚总督博布林斯基伯爵管理。他是俄罗斯裔,把推行俄罗斯化看成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一上任便宣称:“我将让俄罗斯语言、法律和制度在这里扎根。”负责促进总督这目标的是他的秘密助手和侄子小博布林斯基。小博布林斯基是杜马的成员和“温和右派”的领袖之一,自一九○七年起是“加利西亚慈善协会”会长,一向不遗余力支持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两地的亲俄罗斯派,又游说俄罗斯政府做同样的事。他主张,政府只要在桑河─奥治乌克兰的重要水道,稳住亲俄罗斯派的阵脚,就可以在聂伯河稳住阵脚,否则,如果加利西亚的亲俄罗斯运动崩溃,小俄罗斯的亲乌克兰运动必然会声势大涨。现在,在他叔叔的力挺和杜马一票盟友包括霍尔姆大主教叶甫洛吉的联手下,小博布林斯基获得实现自己想法的难得契机。
除了利沃夫的名称被改为俄罗斯语,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城镇的街道和广场也比照办理,纷纷被冠以普希金和其他俄罗斯文化或政治名人的名字。俄罗斯语被引入教育系统,最终目标是取代乌克兰语。当局为“俄罗斯裔”教师开设专门课程,让他们更能掌握俄罗斯语。乌克兰语报纸遭查封,以“小俄罗斯方言”撰写的书籍被禁止出版。即使以乌克兰语写的书信一样会被取缔。亲乌克兰派的组织被关闭,数以十计的亲乌克兰派分子被捕。都主教舍普季茨茨基,是希腊天主教联合教会首脑,一九一四年九月遭拘留,接着流放至俄罗斯中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一间东正教修道院度过。
反之,亲俄罗斯派分子和组织却获得支持。小博布林斯基亲自到新占领土地每一座监狱释放被奥地利当局监禁的亲俄罗斯派分子。自此,亲俄罗斯派大力鼓吹支持“白沙皇”,号称他的保护业已延伸至长期受苦的“红罗斯”(加利西亚的中世纪名字)。早在战前便活跃于地区内的俄罗斯慈善团体此时更是迁入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打着“全俄罗斯人”的旗号为农民提供援助。
但战争环境限制了小博布林斯基的俄罗斯化大业。一票军方将领,特别是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他在军中的受欢迎程度尤胜于沙皇,相信应该把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立刻整合到帝国里面,但政府却希望等到和平条约签订再进行整合事宜。双方最后达成妥协,同意把全面整合推迟至战争结束,但在这之前,朝廷会把军方的需要放在优先位置。当局想要的是稳住占领区,避免进行会引起不满和抵抗的大刀阔斧改革。因此,东正教教会的活动受到限制,规定大主教叶甫洛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方能接收希腊天主教的教区:一是该教区乏人主持(很多希腊天主教教士不是已经逃走就是被奥地利当局逮捕),二是有大多数教民同意(至少要有百分之七十五同意)。尽管有这些严格要求,改教的人仍然很多。据报章报导,光是占领的头几个星期,就有三万名联合教会的信徒转而皈依东正教。
在加利西亚居民中间,因为占领政策而吃最多苦头的是犹太人。在德军手中吃过几轮败仗之后,俄罗斯军队和社会开始疑神疑鬼,把犹太人看成是最大的隐患,主张把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犹太人宣布为俄国子民,把他们移转到其他地区。但由于政府拒绝立刻把加利西亚并入帝国,军方便改而禁止犹太人在前线附近的地区从事任何活动。此举有效杜绝犹太人的商业活动,破坏了犹太社群在该地区的经济基础。补给欠佳的俄军后来还强征甚至抢夺犹太人的存粮,让他们成为受害者名单的最大苦主。在俄军来到前便逃走的犹太人被没收家财,这政策对奥地利人和波兰人一体适用。
俄罗斯为对付德、奥所打的民族牌充满矛盾。在加利西亚的情况,它有两套政策直接产生冲突:一是承诺实现波兰人的民族愿望,另一是把加利西亚视为俄罗斯的原有土地。当局向波兰裔承诺,战后将会把波兰裔的聚居地重新统一,让他们独立建国,新的国家还会包括属于奥地利的波兰人土地。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于入侵奥地利和东普鲁士前夕在宣言中这样告诉波兰人:“让那些把波兰人民切割得四分五裂的边界消灭吧。让它在俄国沙皇的权杖下重新统一自己。在那权杖之下,波兰将会获得重生,能够自由选择信仰、用自己的语言和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由于占领加利西亚的俄罗斯当局想要表现出说到做到的姿态,所以容许某些地方的法院系统继续使用波兰语。占领初期被关闭的波兰语学校也重新开放,容许波兰语与俄罗斯语一道被用作教学语言。
这让加利西亚的亲俄罗斯派有被出卖的感觉。他们不被允许在占领当局任职,而这些职位通常是由来自帝国和资格不够的官员滥竽充数。最重要的是,原来叛逆的波兰人被当局看成是盟友,而加利西亚的“俄罗斯人民”反而再次受到二等公民对待。
亲俄罗斯派的担忧被他们在俄罗斯民族主义阵营的盟友认真看待,后者也常常在杜马为亲俄罗斯派抱不平。这些议员反对任何和他们民族主义愿景不符的占领政策,认为俄罗斯是奋斗了好几百年才达到目前快要重新统一的状态,不应该对有敌意的西方─以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为代表─有所姑息。反观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自由派却欢迎政府以宽容态度对待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波兰人。但就像战前一样,立宪民主党人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也是分裂为两派。
司徒卢威认为,取缔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运动可以让帝国境内的乌克兰运动无疾而终。米留科夫不同意这位党同志的意见,暗示自己对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运动研究有素,主张这种现象不可能通过军事占领消灭。他对立宪民主党的中委会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求政府“结束在被占领地区进行俄罗斯化政策,重新开放封闭了的民族机构,并严格保护民众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但他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有些学者主张,米留科夫此举只是要安抚他在亲乌克兰派中间的支持者和盟友:如果是这样,他是白忙了。
不管怎样,帝国境内的乌克兰运动家对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加利西亚的侵略性行为都难有多少作为。他们自顾不暇:他们必须竭尽所能证明他们本身忠于帝国,因为他们在俄罗斯民族主义阵营的敌人质疑这一点,又把乌克兰运动说成是一个德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一起弄出来的阴谋。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定,加利西亚是乌克兰运动的中心。早在战争爆发好一段日子之前,基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便提出警告,说乌克兰有可能会脱离俄罗斯,加入奥匈帝国。战争爆发后,当局按照俄罗斯民族主义阵营的担忧和疑心病采取行动,查封乌克兰语出版品例如以基辅为基地的报纸《议会》,骚扰乌克兰人的组织和活动家。他们被政府贴上“马泽帕主义者”的标签,能够对大众表达意见的机会少之又少。
格鲁舍夫斯基是大战期间乌克兰运动在俄、奥两国命运的缩影。他是加利西亚亲乌克兰派的领袖之一,自然也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战争初期,奥地利当局怀疑他有亲俄情感(他从未放弃俄罗斯国籍),命令他离开前线地区,往西而去。他在维也纳待了一些日子,期间受到警察监视。他离开奥地利几天后,当局便对他发出逮捕令。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抵达基辅,却又被俄罗斯警察以亲奥的罪名逮捕。警察在他的行李中搜出“罪证”,其中包括一本题为《沙皇如何欺骗人民》的乌克兰语小册子。但这只是表面理由,因为逮捕格鲁舍夫斯基的命令早在俄国攻占利沃夫未几便下达。当时,当局在利沃夫找到格鲁舍夫斯基和一些乌克兰活动家的合照,而根据线报,照片中的乌克兰活动家是为奥地利政府工作,反对俄罗斯。
警方断定格鲁舍夫斯基是加利西亚马泽帕主义者的领袖,计划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因为一些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说情,这些知识分子背景分歧,既包括为科学院就乌克兰语撰写备忘录的沙赫马托夫,也包括立宪民主党的司徒卢威,因而当局改变主意,把流放地改为辛比尔斯克。后来流传一个笑话,说之所以会有这种改判,是因为格鲁舍夫斯基的支持者动了手脚,在判决书上改了几个字母,把 Siberia(西伯利亚)改成 Simbirsk(辛比尔斯克)。辛比尔斯克是伏尔加河河畔的一座小城,靠近莫斯科,但离乌克兰仍然很远。此举有效让格鲁舍夫斯基和整个乌克兰运动为之噤声。自此,政府和支持它的那些“不折不扣俄罗斯人”便可以放开手脚,在帝国边界的内外按自己的民族打造工程纲领行事。
一九一五年三月,当格鲁舍夫斯基在流放地辛比尔斯克安顿下来的同时,皇帝尼古拉二世计划访问新占领的加利西亚。三月九日,普热梅希尔的陷落给了他一个沐浴在军事荣耀中的机会。这不是他第一次造访前线区域,却是他第一次在战争期间走出帝国的边界之外,因此让他的近卫军相当恐慌。同样反对沙皇出巡的还有以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首的一票军方大老,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守不守得住新占领的地区。他们也担心,随着沙皇踏上被报章称为俄罗斯所固有的土地,他们在接下来势必艰辛的一九一五年夏季战役中,有可能会被迫把政治考量置于军事考量之上。
但尼古拉坚持出巡,他的近卫军和将领只好配合。这相当于一场媒体政变,因为他此举的一大目的是扭转自己在军中受欢迎程度远不及亲族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现象。俄罗斯民族主义报章对出巡计划欢呼喝彩,认为沙皇此行不仅标志着俄罗斯的军事胜利,还标志着其民族理念的胜利。沙皇的行程包括造访利沃夫、普热梅希尔和布罗迪。当时是四月,正值复活节期间。按照传统,沙皇为了表示亲民,每年复活节会跟朝廷直属的官员和士兵及水手交换复活节彩蛋(和亲吻)。他会用陶瓷彩蛋─当然不是法贝之家所制造的那种保留给皇室成员的复活节彩蛋,但以当时标准而言也是极其奢侈的彩蛋─换取士兵赠送的手绘水煮蛋。现在,这一套被带到加利西亚的部队,以象征帝国的神圣空间向西延伸。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
远游期间,尼古拉常常感觉自己就像还留在帝国境内。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走得愈远,这个国家的景色就愈美丽。路上看到的聚落和居民会让人强烈联想起小俄罗斯。”造访过利沃夫之后,他又写道:“好漂亮的一座城市,会让人微微想起华沙。好多花园和纪念碑,到处都是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百姓。”在利沃夫迎接他的除了加利西亚总督博布林斯基伯爵,还有地区内的最高宗教领袖大主教叶甫洛吉。
沙皇莅临前夕,叶甫洛吉接到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短柬,请求他不要在欢迎致词中涉及“政治”。他不知所措,问送来短柬的首席随军牧师︰“我是否不可以说『陛下您是以最高主宰身分踏入这片土地』之类的话?”得到的回答是︰“对,不可以。战争还没有结束,没有人知道沙皇以后还会不会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叶甫洛吉拒绝接受大公的忠告,在致词中说:“皇帝陛下,您是第一个踏入这片古老罗斯土地的沙皇。它是罗曼亲王和丹尼尔亲王传下来的祖产,之前从未有俄罗斯君主踏足过。许多年来,这片受宰制的罗斯土地长期受苦,唉声叹气了好多年,现在终于可以向您发出一个胜利的欢呼。”
尼古拉龙心大悦。当地亲俄罗斯派的热情接待也让他印象深刻。当晚,在总督府举行晚宴时,突然来了一群叶甫洛吉教区的东正教教民。他们举着圣像和教会的横幅,突破外围的安全戒护,出现在总督府的前广场,高声合唱〈人民之歌〉,即〈天佑沙皇〉歌。尼古拉走出阳台对人群讲话,情形让人回想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他在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的一幕。他感谢群众的热情接待,并用让叶甫洛吉和其他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大为受用的措词结束简短讲话:“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和不可分割的罗斯!”沙皇的妹妹奥尔加日后回忆往事时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受到,有一条神秘纽带把我们的家族和人民连结在一起。”
尼古拉在一九一五年复活节的加利西亚之行被一支俄罗斯摄影队摄入镜头,而他在当地庆祝复活节的场面后来也成了油画和明信片偏爱的主题。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梦想的象征性高点:长年以来,他们都梦想着把基辅罗斯曾经有过的土地收复回来,建立一个帝俄民族,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构成,让君主、宗教和民族为国家服务。任何曾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九日目睹过利沃夫总督府广场上那一幕的人都很难不去相信,俄罗斯帝国在经过长期转化后,终于成功蜕变为民族国家。因为它不但没有被兴起中的民族主义撕扯得四分五裂,反而成功地把疆土扩张到原有边界之外,把所有俄罗斯人纳入怀中。
俄罗斯“统一主义者”的热望和梦想是被俄军快速击败奥军所燃起,但它们破灭的速度比燃起的速度更快。一九一五年五月,即沙皇以胜利者之姿进入利沃夫后不到一个月,德国的师团便开抵奥地利前线,对加利西亚的俄罗斯守军发起攻击,一举夺回普热梅希尔并迫使俄军撤出利沃夫。九月底,俄军失去了大部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一大部分、所有的波兰、白罗斯西部和大部分波罗的海省分。
一九一五年八月,愤怒的尼古拉自任作战总指挥。此举固然有助于提高士气,但他也等于把战争胜败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战况持续走坏,耗尽俄罗斯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一九一五年夏天,在春季和夏季战役败北不久之后,杜马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联合米留科夫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十七日联盟”中的君主主义者组成一个“进步集团”,要求朝廷成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言下之意要让他们来组成政府。沙皇拒绝所请。在一九一五年的余下日子和一九一六年一整年,俄军在对德奥的阵地战中消耗日益加剧,但朝廷与杜马始终处于对立。
一九一七年二月,首都严重缺粮,面包店外面大排长龙,到处出现群众示威,军队也因为拒绝镇压示威而发生哗变。社会主义者创建的“苏维埃”(议会)成为彼得格勒的真正力量,让沙皇政府变得无足轻重。杜马的领导阶层也成立了一个自己的政府,但未能安抚人心和控制住局面。最终,他们决定,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是逼沙皇退位。他们得到军方支持,因为一票将领就像许多大臣和议员那样,相信沙皇已经与现实脱节,只是德裔妻子亚历山德拉的傀儡。盛传,皇后希望俄国撇下盟友英国和法国,单方面和德国签署和约。
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军方反对缔结独立和约,认为此举不仅违反俄罗斯对盟友的义务,也会导致帝国解体,因为它在战时落入德国的领土势必会继续被占领。他们还担心这样的和约会动摇军队士气,引起前线部队叛变。现在,看见彼得格勒的街头叛乱和士兵兵变,他们知道尼古拉非下台不可。杜马的领导阶层表示同意。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杜马派出两位代表,执行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告诉沙皇已经没有人欢迎他留在皇位上。被委以此重任的两人一个是知名议员舒利金,一个是新政府的海陆军部长古契科夫。
身在白罗斯莫吉廖夫陆军大本营的尼古拉得知彼得格勒发生革命之后,急着取道普斯科夫返回首都。他也知道了杜马派代表见他的事。他有些随从相信,舒利金的出面对沙皇和君主制的未来都是好兆头。
因为众所周知,舒利金不仅是知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理论家,也是忠诚的君主主义者,而这时候的君主制用得着它能找到的所有支持。舒利金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学院,父亲是全俄罗斯人派在乌克兰的喉舌报《基辅人》报的创办人维塔利.舒利金,但自幼丧父,由《基辅人》报下一位主编尤泽福维奇养大。舒利金后来接替主编职位,又在一九○六年秋天的杜马选举中初试啼声,当选议员。任职杜马期间,他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右翼主义者的领袖之一。他同时是一九一○年年初创建的群众组织“全俄罗斯民族主义联盟”的领导者。
一九一七年三月,舒利金自告奋勇,扛下谒见沙皇的使命。他认为,若能说服尼古拉逊位,将可保住君主制度。他的同行者古契科夫也是抱持一样观点。就像包括新任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在内的许多政府成员那样,古契科夫相信,沙皇主动逊位会有利于十二岁的儿子阿列克谢接班。此举可安抚人民的怒气,让杜马和临时政府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夺回主导权。以变成立宪君主制为代价,俄罗斯君主制可望安渡危机。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黄昏,舒利金和古契科夫抵达沙皇的驻跸地普斯科夫,下火车后先求见北方面军司令官鲁斯基。先前,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取得各个方面军司令官的同意,采取一项形同政变的行动。他对控制着普斯科夫的鲁斯基下达命令,要他利用一切劝说手段说服沙皇逊位。鲁斯基和杜马的领导阶层一直保持密切接触,并像其他高级将领一样希望看见沙皇下台。他以令人钦佩的效率完成使命。舒利金和古契科夫没有见到鲁斯基,而是直接被带到沙皇的火车厢。鲁斯基稍后出现,低声告诉舒利金,逊位的问题已经搞定。
尼古拉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告诉舒利金和古契科夫,他同意退位,但不打算让儿子阿列克谢继位:阿列克谢的严重健康问题让他必须留在父母身边。取而代之,尼古拉想要传位给弟弟米哈伊尔。犹豫了一下之后,两位客人同意了沙皇的建议。舒利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未成年的阿列克谢不能合法地宣誓效忠宪法─宪法在舒利金的俄罗斯君主制愿景中是一个重要元素,而米哈伊尔却是成年人,有资格这样做。舒利金请求沙皇在逊位诏书上补充一点,表明米哈伊尔将会对“全体人民”发誓,保证会密切配合代表他们的机构,意即杜马。尼古拉表示同意,但把“对全体人民发誓”改为“发出不可违反的誓言”。显然,他仍然努力想要让君主不为人民所缚。
但是,部分人民─至少是那些在彼得格勒街头起义的人民─更清楚知道他们对君主制是什么感想。舒利金和古契科夫回到首都之后才发现,那里的人既不想要尼古拉,也不想要君主制。由杜马领导阶层组成的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人民的意愿。“当然继承人”米哈伊尔也是如此,他在尼古拉退位第二天便签署一项声明,表示除非制宪会议向他要求,他才会接受皇位,制宪会议是预定要用来决定俄罗斯政府政体的组织,其代表由人民选出。米哈伊尔的声明起到了预期效果。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同意下,杜马政府组织了一个俄罗斯“临时政府”,负责筹备制宪会议的选举事宜。新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结束政治侵害,引入民主机制,并承诺取消“所有土地、宗教和民族上的限制”。这表示所有俄国人民在法律前面人人平等。至此,君主制空有其名。
舒利金、他的杜马同仁和一票将领都感到失望,但不得不接受现实。不过,让他们放下心头大石的是临时政府并未宣布打算和德国签署和约。很明显的,临时政府准备要把仗继续打下去,以恢复帝国领土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它获得了政治菁英和军事菁英的充分支持,因为他们都把俄罗斯的统一和不可分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对帝国统一性的威胁更多不是来自德、奥军队,而是来自帝国内部的革命力量。
君主制的垮台和彼得格勒的权力真空状态导致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和社会主义者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发生激烈竞争,这又让各民族运动的领导者有了可乘之机,民族主义运动在大战爆发后一度退潮。首先对这种革命新形势加以利用的是那些在十九世纪经历过某种形式自治的民族。其中之一是芬兰人,芬兰在一八○九至一八九九年之间曾享有自治权,他们立刻要求让他们原有的宪法恢复过来。临时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即尼古拉逊位不到三周─予以同意。九天后,波兰人得到承诺,他们将会获准独立建国,条件是建国后与俄罗斯缔结军事同盟。这一切会等到制宪会议召开后正式拍板定案。不过,在波兰的情况,临时政府的承认徒具形式。在那段日子里,彼得格勒的市民喜欢打趣说:“承认波兰独立就等于是允许月亮独立。”这是因为,波兰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便不再由俄国控制,目前是处于德国占领状态。
对帝国的西部省分来说,波兰问题从来不是存在于真空状态。每一次的波兰起义都会鼓励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从而把“单一俄罗斯民族”的想像体砍去一些。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并未要求独立,但急于争取文化和领土的自治,还有争取俄罗斯转型为联邦制国家。现在,根据临时政府的宣布,构成这个国家的不是帝国子民,而是俄罗斯公民。
但临时政府不愿意让帝俄民族两个较小分支圆梦。这不仅是因为它希望把一切有关政体和国家结构的问题拖到召开制宪会议再解决,也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力阻─在一九一七年春天,立宪民主党是政府内最有影响力的政党。像司徒卢威之辈的立宪民主党人仍然反对分裂帝俄民族,主张民族是由语言与文化界定,不是由血统界定,而像米留科夫之辈的立宪民主党人则只准备给予非俄罗斯人个人自主权,即只允许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化,不是允许他们拥有自治领土或政府。
但后者正是乌克兰领导人和一些白罗斯领导人向彼得格勒政府要求的。在接下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中,史称俄国革命,他们将会把声音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迈出他们原来不敢想像的大步。
—End—
本文选编自 Lost Kingdom: The Quest for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Russian Nation,译者梁永安,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