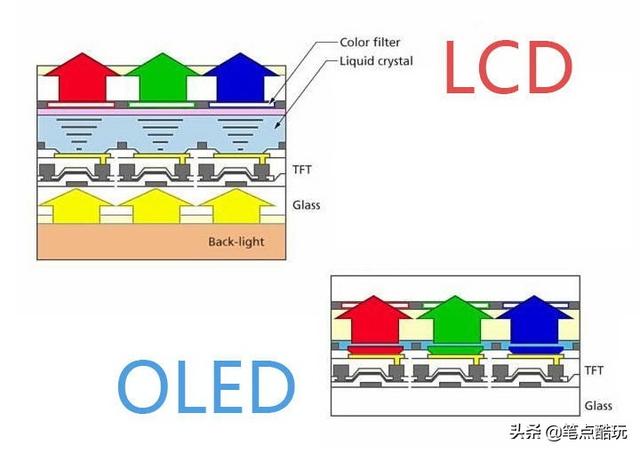我大吃一惊,今天,我们说的话,所谓中规中矩的发音,有没有浓浓的汁液,只有南北之分。
从前,听家乡某个老男人唱山歌,歌词里不断地闪出阿哥呀,阿妹哟,我不问歌手是谁,大约了解是谁又能怎么样呢?一笑了之。事过多年,突然问起自己,那首山歌是谁写的?我爷爷认得那个作者吗?因为那首歌肯定出自方圆几公里之内,倏忽就成了山歌。哪个鼻祖如此让人汗颜,不让我们把他记住。沉甸甸的历史,倏忽就劈头盖脸地俯冲下来,我面红耳赤,要么甩自己一巴掌,要么咽泣……把巴掌甩向别人。
我几乎天天听复制的A THOUSAND KISSES,因为没有了那个可爱的阿哥呀阿妹哟,我们现在都吃快餐了,吃流水线上的食品,音乐也一样,周 而复始地听,颓废着颓废着,口腔上了火,脑门干涸了,也定当随着歌声一起飘荡,掠过欧亚大陆。想起宫殿里的长老,还有齐地的长袍。直到有一天,别人告诉我,这是一次跨越,我直接跨越了千山万水, 插进了欧洲人的心脏。
我就是这样老实,吃了假药,喝了假奶,天天还穿着被污染的水,浸过的衣服,也不埋汰

,还决然幸福。只是我的耳朵竖着,我天天听复制的A THOUSAND KISSES。感谢我撞上某个人的博客,一次次,让我在这首歌前停止了苦涩。
我甚至大吃一惊,今天,我们的嘴都抹了蜜吗?为什么一张口,就是哈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