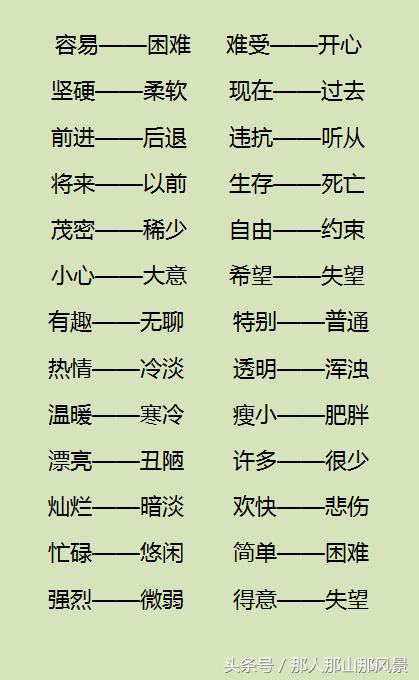大概很少有哪个词语像“美”一样,既让人愉悦和向往,又令人惶恐不安。
这是因为,美是我们通过感知得出的看法,一个人、一件器物、一处建筑由于符合了某种美学标准,而被认作为美,比例、线条等表象取代了东西本体的品质,比如是好还是坏,是恶还是善,是实用的还是无益的。然而,我们却有着一种冲动,赋予美“不单是美”的神秘力量,最近的例子是“颜值高的人更不容易感染新冠”。这个说法借用一些医学研究、“专家补充”得出结论,简而言之,长得好看的人其面部比例更健康,人更自信,故而有更强的免疫力。这一说法很快沦为段子,其实它最致命的问题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美是感知的、是人群定义的,而不是实在。犯这种逻辑错误的,还有《冰川冻土》刊登的论文《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期刊方已撤稿),作者对“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母的优美感”的论述,通过专业术语包装,煞有介事地把“无才便是德”当作实在,仿佛它能使师母成就导师的崇高。
“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母的优美感”原文刊于2013年,由于在2020年1月偶然走红网络,因此也被称为“2020年第一神论文”,“气哭了”康德(其实康德不是崇高和美最经典的阐释者)。当月,紧接着,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暴发,很少有人再关注了。如今,快三年过去,不知还有多少朋友记得此文?

电影《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1952)剧照。
崇高和美是一种矛盾关系,甚至最初彼此没有多少关系。美是一种协调比例,是柔和,抵抗的是畸形——当然畸形也未必是丑,尤其是在形状符合某种标准的情形下。而崇高是一种震撼,是人看到了无法把握的并且无限大的景观、数字或力量之时产生的某种惊惧。用个未必切确的说法是,如果说美是寻求安稳的,那么崇高就是激发变动的,因而在政治或社会哲学上,它也有暴力的冲动和倾向。在追求崇高的过程中,能否实现美,或者说,在完满中是否还能有一些崇高,让无数人为此纠结。
本文是《美学权力》作者巴尔迪纳·圣吉宏论述崇高和美二元对立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包括“丑”与美的对应、与崇高的区别。在她对埃德蒙·伯克等人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优雅包含了美的元素,并且能抵抗崇高可能存在的暴力风险,到这时,崇高和美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美学权力》一书,内容有删节,顺序有调整。标题由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美学权力》,[法]巴尔迪纳·圣吉宏 著,骆燕灵、郑乐吟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或者崇高,或者美
“这是美吗?或是崇高吗?”直到18世纪中叶,得益于埃德蒙·伯克,人们才追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斟酌过这个问题?

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1927)中的崇高视觉。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美和崇高这两个概念形成于不同的领域,且彼此间交流始终微乎其微。
“美”曾经主要是形而上哲学家处理的事情,而“崇高”特别涉及辩术师和文学批评家。自文艺复兴晚期起,我们就遗忘了这两个概念在源头上根本性的差异。原因在于美和崇高反向的演化制造了一种交错配列。一方面,“美”首先被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随后它征服了艺术领域本身;另一方面,“崇高”首先在它与话语的关系中被思考,因而通过伽利略哥伦布革命进入自然的领域。同样,在17世纪末,艺术和美被并置到新的意群“美术”里,其时还出现了一个全然一新的概念——自然的崇高(sublime naturel),后者指的是自然景象之崇高。

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是对“崇高”的一种表达。图为《涉足荒野》(Wild,2014)剧照。
直到1757年,埃德蒙·伯克,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性情如火,既迷恋弥尔顿和莎士比亚,也迷恋荷马和维吉尔,构造了崇高和美之间极端的对立。这个想法在他只有十九岁时就确立了。大约二十八岁时他撰写和出版了《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康德在1764年重拾这个概念,且于1790年重构改造这个概念。
如今,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要去研究伯克是否有理由在崇高和美之间引入一个极端的对立。如果我们严肃地面对美学,如果我们寻求理解它的哲学基础,我们就要明白忽略伯克所构建的这个断裂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伯克并没有使用美学这个术语,而且他指称他想要构建的科学时他所说的就是“哲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美学这个术语用在他的主题上。美学的关键词在美学专业出现之前就被发明了,而伯克在大西洋彼岸也通常被认为是美学的奠基者。
根据我们这里坚持的一个论题,崇高——或者其创始人所理论化的东西——不仅构建了一条主要的趋近美的道路,而且构建了唯一一条深邃严肃之道路:那触及美之力量的,不仅被认为是理念和情感,也是原则。“美的事物是艰难的”,这是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给出的疑难结论。斯宾诺莎更进了一步,《伦理学》以一个令人难忘的句子“Sed omnia praeclara tam difficilia quam rara sunt”结束,我们通常翻译成:“美的事物艰难而稀少。”
是什么构建了事物之美?为何美同时意味着幸福和痛苦,惊叹和恐惧?为什么它必须存在于可承受的极限内,否则即丧失内容,变得形式化,变得空虚而无聊?在《杜伊诺哀歌》的第一卷,里尔克追念美之痛苦,它被认为是可怖的萌芽,而非恐惧本身:
因为美只不过是
我们尚可承受的恐怖之开端。
如果我们仰慕它,也只是因为,在它的安息里,
它不屑摧毁我们。

电影《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第三部(2007)剧照。
有这样一种美学权力,越是可怕,越是让人仰慕,乃至令人生畏——根据拉丁语中“formidosus”(可怕的)的意义——它与我们保持距离,甚至嘲弄我们的存在或我们的不存在,它似乎没有忧虑它是否显现或不显现。这个力量处于摆脱或解脱的边界,同样属于卡斯蒂利奥内所说的漫不经心的优雅与“淡然”,这被认为是真正的艺术。然而这种漫不经心的优雅与淡然并不仅仅想要隐藏艺术,它甚至让我们相信作品自己“毫不费劲地、几乎想都不用想地到来”,或者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到来。像“淡然”一样,里尔克的美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傲慢无礼——它拒绝解释,拒绝投入:它自我关闭,距离遥远,在它庄严的自足里,对我们的在场毫无知觉,就像是对我们的致敬。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痛苦的不完整的存在,这个内在于美的寂静丝毫不意味着静止关系。这个美制造了一个矛盾的欲望:一方面被美的在场侵袭而战栗;另一方面企图去掌控、去处理它的显现。预感到美内在恐怖的威胁,我们更加急于找到美可以行使权力的准确切入点。如果美学对我们来说重要,不是因为它一次性解决了我们与一个价值的所有关系,或处理了我们与一个预定对象的所有关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审慎地给予了我们一个适当的工具去认识、创造和批评那些打动我们并让我们赞叹和震惊的东西。
更早的崇高与美问题
让我们简单回溯美与崇高在哲学和语文学领域的诞生。
正如黑格尔写道:“希腊意识正是美的时刻。”希腊人的特质,是在美的视角下来理解这个世界,并将其设想为艺术作品。宇宙(kosmos)指有秩序的世界,以及我们所看到的装饰者与被装饰者结合而产生的光彩:作为劳动疗法的辅助,我们曾提出美学疗法,用更好听、更准确的术语来说,也就是宇宙疗法。我们暴露于宇宙之中,让宇宙在我们身上产生回响,这是我们理解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们来源于此,我们属于此,我们也将消逝于此。
除了宇宙,另一个希腊哲学的关键词是艾多斯(eidos)。在表示形式或理念之前,它意即显现出来而被看到的,也就是指那持存于表象的多样性之中的东西。根据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它甚至给予表象以光辉,最后产生了爱欲。
作为艾多斯的美似乎特别地与视觉相关,与凝视冥想相关;但是遗忘它与听觉和话语的关系,这或许是一个错误。比如《大希庇阿斯篇》所指出的,又或者比如在《九章集》第一篇的开头,普罗提诺主张美不只与视觉相关,也与听觉相关,与所有音乐的形式相关。

纪录片《帕特农神庙的秘密》(Secrets Of The Parthenon,2009)画面。
如果将希腊的美仅仅和视觉放在一起是一种滥用,相反我们应该回想起古代的崇高首先是听到的(读到的,背诵到的,即兴的,歌唱到的),因为它诞生在修辞学和诗学的领域中。闻所未闻的震惊,恰恰指的是在听觉里却超越了听觉。这并没有阻碍视觉的涌现,反而促使了内在于词语的内在视觉的诞生。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主张演出或者表演在悲剧里是次要的。
如果说想象在朗吉努斯那里扮演的角色是首要的,这是因为它会产生词语,而这些词语,反过来,又产生新的富于想象的表象。在并不依靠论证这一方法的情况下,内在视觉与外在视觉相互竞争,通过产生心理上的图像、真实的影像或富于想象的连续性影像,来显示思想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词语都是有想象能力的,他们展现和创造的不只是孤立的表格,而是如电影般的连续性。
面对古代的崇高概念,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这个传统的二元性:希腊罗马严格意义上的修辞术传统和希腊的哲学传统。第一个传统广为传播,崇高(sublimis)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庄严、高雅、激烈或惊惧的近义词。第二个传统专注于高度和升华——直到17世纪晚期我们才把希腊语中的“hupsos”翻译为崇高(sublime)。

电影《现代鲁宾逊》(Lt. Robin Crusoe,1966)剧照。
升华的渴望需要肉身化为自然的和道德的冲动。朗吉努斯引用柏拉图,痛斥“正在饲养的动物,目光总是朝着下面,倾身向土地和筵席,饱餍食物和淫乐,为了更多的享乐,它们以角和铁屐彼此攻击,最后死于无法满足的欲望”。真正的人的特性是保持直立,感觉到为顶峰所吸引,总而言之,成为崇高。
但是朗吉努斯和柏拉图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和希腊哲学产生了分歧。他和存在论首先发生了断裂,他悬置了存在者和永恒存在的问题,他只关注崇高,启示优先通过逻各斯(logos)、话语、风格或言说作为中介,而不是通过知性或感性的视觉。逻各斯的本质是可渗透到崇高的,与其说是崇高构建了客体不如说崇高构建了主体。这意味着崇高话语的目的性,与其说是要言说崇高,不如说是让崇高言说。崇高不过是“经过”而已,我们可以给予崇高三重意义:短暂的瞬间显示,跨越障碍,最后是自我承认。创作者和见证者共同地向一个原则敞开,这个原则并不在语词里耗竭,而是赋予其活力,或多或少暂时性地让它发光,让它接下来继续它的旅程。
伯克的发明
18世纪末期关于“崇高”的思辨被人们遗忘了。仅剩康德的几个例子。没有任何人再引用朗吉努斯,人们也不再待见古代作家或现代作家。然而,吝于引用的康德,却引用了一些游记作者,比如马斯登(Marsden)和苏门答腊的胡椒地,萨瓦里(Savary)和埃及金字塔,奥拉斯贝内迪克特·德·索叙尔和他的冰川。在康德之前,有强大视觉想象力的伯克已经觉察到那个时代的情绪,并给予风景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显然,伯克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非常重要,他指出美学涵盖了崇高和美两种彼此不相容的经验。
崇高的经验与痛苦关系复杂,痛苦可以转化为愉悦;美的经验,基于爱,基于交际性,基于关系的自在。崇高概念触及自我的激情,也就是说防御性的激情,因为它涉及主体的完整性,伯克称之为“自我的保存”。美,唤醒了积极的激情,它促使我们靠近他者。积极的激情与性别社会乃至广义的社会相关。弗洛伊德最初将“冲动理论”构建在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对立之上。生命激情包含两方面,一是自我的保存,二是对他者的爱。伯克将激情的二元论改造成了享乐的二元论,他原创性地彻底区分了否定性愉快(或相对性愉快)和实在性愉快(或肯定性愉快)。前者源于对最初的恐惧的超越;后者是瞬间性的。他主张“源于痛苦的想法比源于愉快的想法要强烈多了”。事实上,愉快并不阻碍我们的意志,我们很乐意接受愉快;而痛苦伤害我们,施与我们暴力。
美让人拥有,它外在性地给予我们一个确定的幸福。崇高却剥夺了我的所有。我没有了专家的知识,我是被缴械的俘虏。

电影《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1942)剧照。
伯克提醒我们,知识主要的效用是“把优雅种植进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方式里,根除肮脏、卑劣和狭隘(illibéral,狭隘的、不自由的)”。自由地感知,让自己和他者逃离狭隘的心胸,是美让这些成为可能,崇高在最高处让这些实现。
关于“美”,伯克诚然保留了它的爱欲力量(puissance érotique),却去除了它的可怖之处。他用了三个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首先,他假设“爱”自然地来源于“美”:“美的在场唤起爱,这就像冰或火让我们觉得冷或热一样自然。”这个效应几乎是瞬时的,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接收者个人的意愿。
接着,伯克以煽动的方式将爱允诺给鄙视(mépris),说“爱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接近于鄙视,爱并不畏惧它的对象,而是怜悯它,爱是使用昵称去表达情感的”。伯克提到,女性完全知道她们拥有卓越的美,却注意要佯装“弱小”或“不完美”(她们脸红、口吃、左右摆动),这让她们更美了,仿佛美并不是难以亲近的。体验美的来临,就像相信孤零零的危险平安抵港。美也是人类关系的黏合剂,它惠泽与维持爱欲和社会激情。但是我们好像习惯了美的降临,也就再也意识不到它的恩惠,奇怪得仿佛我们对美屈尊了。
伯克极大地影响了康德。伯克的原创性在于他寻找对于美的准确的美学定义,并对美做社会心理学的辩护或生理心理学的辩护。美之物是微小的,曲折的,清澈的,精致微妙的。它们孕育出情感、信心和爱,慰籍疲倦,有助于我们从紧张中得到片刻的放松。
美的反义词是丑,
还是崇高?
问题在于,崇高与美之间的对立是否是逻辑的或者实在的。
康德在《试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L’Essai pour introduire en philosophie le concept de grandeur négative)中恢复了作为力量的否定性,这是非常有用的。康德像数学家一样假设了否定性的量,他指出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基于“矛盾律”的逻辑的对立(“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其中一个是真命题,那么另一个是假命题”),我们应该考虑基于存在原则的实在的对立,因为存在不仅仅是通过可能性来证实,而是通过其现实性来证实。

《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mmanuel Kant,1996)剧照。
那么,崇高是如何实现与美对立的?毫无疑问,不是通过逻辑的角度,通过逻辑的排他性来实现,而是通过实在的角度,通过那个甚至有可能使得崇高消逝的实在来实现。那么崇高不会和丑相互混淆吗?美的反义词是丑,还是崇高?
伯克回答道:丑和崇高是相容并存的。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丑因其丑而崇高。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当丑)“与能够激起强烈恐惧的质相结合时”,它才能成为崇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论题呢?丑并不是简单的畸形:美也可以是畸形的,当比例不再是必要的时候。但是丑也不仅仅意味着美的缺席,它是废除美的原因。与其说这是在场,不如说这是驱逐过程的再现,这是感性的表达能力的废除,突如其来,不仅无法吸引和诱惑,而且不能指示。
如何将丑和崇高区别开来?我们可以将丑定义为对崇高化的不服从,相反,崇高揭示我要超越自我的召唤,目的是抵消那些无法辩护的东西,或者消减它们。
丑构造了丑闻,它是思想的绊脚石;相反,崇高是飞跃的要素。对伯克来说,“可怖、恐惧、可怕”是丑可以成为崇高的条件,伯克的文字语言是非常模棱两可的,我们可以在马修·格雷戈里·路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安·拉德克利夫(Anne Radcliffe)或者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的黑色小说里看到他们阐释的恐惧可怖之物。在我看来,我们过多地强调了那个“甜美的可怖恐惧”,而忘记了崇高本质上召唤我们去“燃烧起那个已经在别处点燃的火焰”。对于伯克和朗吉努斯来说,崇高的主要使命是启发灵感,而不是单纯的取悦:它必须使我们摆脱旧的感知和思考方式,并向我们传递一个全新的热情,点燃我们的生命。
“丑”的震撼
康德从伯克那里继承了崇高和美的二元论:崇高与可怖相关,它产生一个否定性的快乐,并让灵魂升华;而美只是简单的愉悦。无限与有限相对,暗晦与澄明相对,动态与静止相对。
1764年,在《对美和崇高情感的观察》中,康德将这个二元论应用到自然、人类的德性、两性乃至国家等概念的分析中。然而,在1790年,康德对于美和崇高的区分是与伯克相关的。这个区分与享乐主义的(或者说,简单的关于“快乐”的问题)关系比较小,它主要与“情绪”的地位有关:崇高激发热情,而美不再给予任何情绪,甚至连温柔都不再给予。基于温克尔曼的启发,康德发表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情绪不再属于美。”在一个学究的角度下,美失去了它的动力,它自我客观化了,以至于我们得到一个关于“美自身”的定义,“世人啊,我很美,哦,死亡,像石头的梦一样”。同时,康德借助“先验说”(transzendental),即通过追问关于感性反思的可能性条件,修改了伯克所构造的美和崇高的对立。

《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1931)剧照。
总之,我们应支持以下论断。
如果崇高的传统成功地赋予它所有深刻的美学价值,如果美最终在崇高中实现了完满,那是因为我们不能将美归结为一个简单的观念或简单的感觉,被动和即刻被感受到的,被认为是一种处于主体之外并仅取决于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恩惠。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同时指定了主动原则、媒介和接受者,我们既不能理解崇高也不能理解美。原则,就是主动且不可或缺的第一因;媒介,就是其物质性很重要的能指;接受者,是为其运作做出贡献并见证它的人们。
从媒介的角度看,崇高对我们来说首先是与美最对立的,就像我们在伯克和前期康德那里看到的一样。但是崇高,它超越形式,展现出隐藏的背面,使痕迹变得模糊。巨大的错乱、过度的激荡、朦胧的眩晕是倾向于消除美的三个原因。
关于巨大的错乱,最经常引用的是埃及金字塔的例子:它们在建筑成就、竖起庞然大物,或体现一种几何理念方面是崇高的吗?我们也要想一下梅西安(Messian)的交响曲或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其中过分的巨大、浩长、困难首先都是令人沮丧的。

毕加索晚年自画像。
对于丑的震撼,我们可以联想到毕加索最后一张自画像、滚石乐队或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它们都使人感到惊讶。关于昏暗的眩晕,让我们追念威尼斯的圣洛克大会堂,那里丁托列托(Tintoret)的画作起初似乎很难看。或者莫扎特的《唐璜》(Dom Juan),它与那个阳光的莫扎特完全相反。
无论如何,如果崇高首先视美为对立面,这最终是为了促生反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让反转成为可能,让我们摆脱偏见并摧毁绝对模型的理念。
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美的景象使我与世界融洽,没有任何真正的主体冲突;同样地,崇高的景象从内部严厉地煽动我,并且不停地教唆我和指使我。但是有那么一个时刻,以某种方式,它放开我,重新成为简单的美,好像它已用尽了那种奇怪地在它与我身上都出现的能量。我们可以说,崇高是那种通过激励我,将我从沉思的选择自由中抽离,使我陷入未知来自我否定的美。
我们以安提戈涅为例。她打算埋葬兄长的计划违反了克瑞翁的禁忌。这件事始于忧虑,也没有引起任何同情;而她被罚永久地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这惩罚带给她光辉和牺牲;而她最终通过破坏克瑞翁的权力而成功实现了她的伦理。但是这个胜利,她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前作为保证。安提戈涅的崇高是出于一种欲望的启示。这种欲望在深度和强度上类似于一部法律,因为它甚至使自身成为法律而超越了另一部法律。恐怖本来盛行的地方,崇高却成功穿过。安提戈涅,这个极其固执的人,一开始无法取悦我们:但她最终启发了我们。
本文内容摘编自《美学权力》一书。
原文作者/[法]巴尔迪纳·圣吉宏;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张婷
导语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