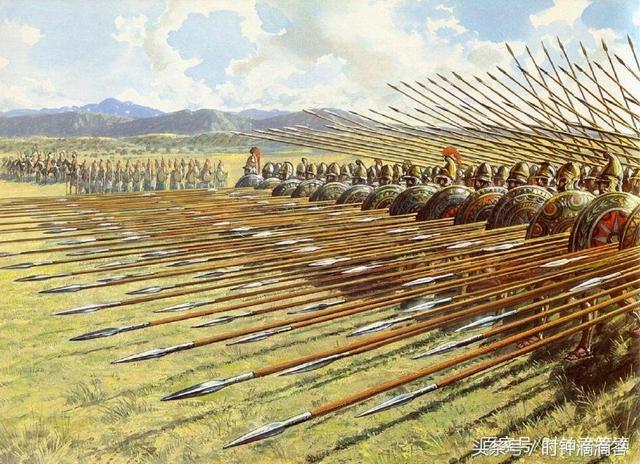本文乃希月独家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秦朝,从建立到灭亡,仅仅存在了短促的十五个春秋。以艺术的方式总结其历史教训的,有两篇名垂千古的文章。其一是贾谊的《过秦论》,另一篇就是杜牧的这篇《阿房宫赋》。

以“阿房”名宫,是说宫殿之四周皆有曲檐。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阿房村,为秦始皇所建。秦灭六国,图绘各国宫室,在咸阳北照样建筑,共有宫室一百四十五处。秦始皇还以为小,复征民工修建阿房宫前殿。殿之“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耗资巨大、空前宏伟崇丽的建筑,是秦统治者穷奢极侈、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一个历史见证。
历史上的阿房宫连同秦都咸阳城一起,后来悉数被项羽毁于一炬,今人已无法一睹其庐山真面。杜牧的《阿房宫赋》,却以瑰丽的艺术想象和多姿多彩的画笔,恢复了这一建筑史上的壮丽景观。开篇概写阿房宫的地理位置和建筑规模之大:
“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
北由骊山构阁道通阿房,折而西向直至咸阳,在长达三百余里的地面上,连绵覆盖着巨大的建筑群落,高楼峻字,遮天蔽日。连水流盛大的洞、樊二川,也不得不驯顺地穿越宫墙而过。以上写远景、外景,接着把笔墨收回,写近景、内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矗不知其几千万落”。连用几个确定和不确定的数字,以及一个“查”字,表现宫中楼阁高耸,鳞次栉比,不可胜数。“廊腰缓回,檐牙高啄;各抢地势,钩心斗角”几句,描写走廊、屋檐及建筑物之间严整对称的特点。又用“盘盘”、“困困”、“蜂房”、“水涡”等形象化比喻,形容建筑物的密集而又回旋曲折、相互勾连。
写毕楼阁廊檐,再拓开笔墨,把目光引向远眺和仰视,写桥梁道路:“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那横跨在滑水上的长桥,那一条条油漆彩绘、高架半空的复道,真让人如坠迷宫,误以为蛟龙卧波,彩虹高挂。作者充分运用赋的特长,层层铺排,竭力渲染阿房宫的堂皇富丽、巍峨壮观,客观上歌颂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举。但从全文看,主要还是为揭露秦统治者的罪恶、总结历史教训的创作题旨服务,为“可怜焦土”的叹惋和嘲讽作铺垫。
作品围绕阿房宫,从纵情享乐和劳民伤财两个方面,对秦统治者进行揭露和押击。秦始皇在结束春秋以来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过程中,是一个有巨大历史贡献的皇帝。但同时又是一个专横、暴虐和极端骄奢的皇帝。国家统一后,他一方面想要“后嗣循业”,子孙万世,传之无穷;另一面,就是纵情声色,荒淫无度。本篇对后者给予了有力地揭露。“辞楼下殿,葬来于秦。”秦始皇下令,将六国后宫美女选入阿房宫,成为秦国的宫人。作者用妆镜星耀,晓提如云,脂水涨流、兰香横雾、车惊雷霾等宫中生活剪影,不无夸饰地表现了宫内所藏美女的数额之巨。如许众多的美女,或急管繁弦、朝歌幕舞,或极态竞妍、缨立望幸,只为一个“独夫”暴君服务,这是何等荒淫无耻!
“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一句,指出有些宫女终生不得一见秦始皇,对宫女的同情和对后者的愤慨,溢于言表。秦始皇还搜刮六国珍宝,输入阿房宫,供他赏玩和挥霍。“燕赵”三句,是横写其“剿掠”六国珍宝;“几世几年”三句,是竖写其“剩掠”六国珍宝。
这些珍宝“倚叠如山”,数量多得惊人,但秦统治者挥金如土,“弃掷温逾”,毫不可惜。作者一路写来,如列清单,把秦统治者穷奢极欲的罪恶暴露得淋漓尽致,对于理解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本质,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文章把少数统治者的享乐与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痛苦处境联系起来,揭示秦自取败亡的原因,尤其深刻。秦始皇统一六国,废除封建制,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他并没有继续下去,给人民造成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力的机会和条件,反而变本加厉地征发各种劳役,大兴土木,筑宫室、造坟基、修长城,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单是被征发去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基的所谓“刑徒”,就多达一百五十万人,耗费的财力更是无法胜算。本文开篇“蜀山兀,阿房出”六字,就是对秦始皇为修建宫室而不惜刮尽民财的做法的高度概括和讽刺。“使负栋之柱”以下,又连用六个对句进行具体揭露,指出:阿房宫所用的柱子比地里耕田的农民多,椽子比在织布机上纺绩的女工多,钉子比仓库里的粮食多,瓦缝比人们身上的纱线多,栏杆、门槛比全国的城墙多,奏乐歌唱之声比市人的说话声多。实际就是一多一少:耗费资财多,从事生产的人少。
在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下,繁重的徭役、沉重的租税、苛暴的刑罚,使广大人民忍无可忍,不堪其苦,“不敢言而敢怒”,必然要起来推翻暴政。“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两个对句,固然有对劳动人民用双手和血汗建造起来的阿房宫被焚毁表示惋惜之意,但更主要是对秦统治者劳民伤财、奢侈误国、自取灭亡的尖锐押击和讽刺。
杜牧写这篇赋当然是有其用意的。此赋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唐敬宗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即位以后,广征声色,兴修宫室,耽于淫乐,致使朝政日趋败坏。杜牧素有经邦济世的雄才大志,希望朝廷振作起来,恢复统一和强盛的局面,因而借古讽今,用秦亡的历史教训,对最高统治者提出警告。他得出结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是统治者不爱惜人民,反而拼命奴役人民,终于失去民心,激起民愤,从而使自己走上灭亡。“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作者委婉地警告唐敬宗,如果不以秦亡为般鉴,改弦易辙,振兴朝政,就必然“使后人而复哀后人”,重蹈秦国自取败亡的复辙,徒给后人再增添一个历史教训。这个结尾十分有力,恰如《古文笔法百篇》所说:“以‘哀’字作结,言有尽而意无穷,一篇主脑在此。”
这篇赋结构缜密。起句突兀,高唱入云;结末深邃,揭示主题,而又含蓄不尽。中间逐次铺叙,波澜起伏。前半部分极写阿房宫之繁华壮丽,正为后半部分写灭亡作伏笔。有铺叙,有议论。铺叙有层次,有详略。议论精警独到,有强烈针砭现实的意义,不似汉赋的劝百讽一,“徒逢君之恶也”。富于想象,通篇多用排比、对偶,而不流于板滞。词采警拔,句法工致,篇内凡十三换韵,读来锋锵有力。全篇气势奔放,笔力道劲,文彩斑斓,不愧为唐代文赋中的名篇。据《唐搪言》载,大和二年(828)洛阳举进士试,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崔鄙,吴武陵把《阿房宫赋》推荐给崔鄙,大受赞赏。杜牧果高中第五名进士。可见此赋在当时已有较大影响。
杜牧(803-852),字牧之,号类川,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宰相杜佑之孙。二十六岁举进士,为弘文馆校书郎。历官监察御史,黄、池、睦请州刺史,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诗、词、赋及古文兼善,而以诗的成就最高,尤善七律和七绝。后人称为“小杜”,以别于杜甫。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别集》各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