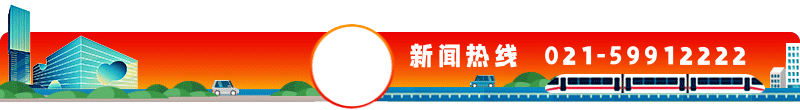
2021年9月26日,我和陶继明、顾建清陪曹伟明去了趟安亭,除参观翥云博物馆、震川书院,伟明提出去原安师校园看看。
这应该是我自1998年夏离开安师后第五次回到这里。事后比对几次回去所拍照片,不必说,乍一看这些不同时间拍的照片变化明显。通常我也的确会在这儿用到“变化”这个词,但这一次我却觉得,这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表述。好比我们偶遇一位多年不见的熟人,有时我们在反应上会特别纠结于对方“有变化”还是“没变化”。当我们告诉对方“没变化”时,其实也未必全然是恭维,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更恰当的表述。

安师办公楼旧址
我想说的是,安师真的像是我的一位老熟人。固然她的周边环境已大变样,整个地区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的校园几无改变,我离开时的那些建筑物一一俱在。就是原先的校门,虽早已废弃不用,也还能在原址找到。1998年改换校名后,原来那堵留有当代书法大师费新我左腕运笔书写的校名痕迹的矮墙也还在。1990年建造新的教学大楼和办公楼时,按规划应拆除却被保存下来的那栋简易如工棚的二层办公楼,至今仍在。教工宿舍楼旁边一片篮球场也还是那个样子,在它东北角边有一口老井,花岗石井栏,我记得当年断水时会用到它,今天也仍在。更不用说校园中央那棵辨识度最高的植物——雪松,今天依然枝叶繁茂。除了校园西部的大操场已被改建它用,其它的场地、道路等都也还在。安师校园既不像我年轻时呆过的其他地方,多数已面目全非,也不像一本纪念册,或可以“常翻常新”,或被藏之于高阁,成为所谓“尘封的记忆”。每次见到她,她就像是一个久违的熟人,很熟、很不寻常,不管不见多久,内心总像是会有一种顿时被她唤醒的感觉,记忆的碎片伴随昔日的情景纷至沓来。事实上,在比对那些不同日子拍摄的照片时,深深吸引我的“变化”,是岁月流逝刻下的印痕,是季节变幻化出的妆容。而面对她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安师校园里辨识度最高的雪松
我前几次回去,第一次是2005年12月29日,我和吴斌两人临时起意;第二次是2010年5月8日,我被邀请参加8506班毕业25周年回校活动;第三次是2015年6月21日,我参加了原安师教职工的回校聚会;第四次是2019年3月9日,我应邀参加9003班同学的回校活动。
在每次回去留下的照片里,被拍到四次以上的有:教工宿舍楼区域,包括篮球场、实验楼等;旧办公楼;每年举行毕业晚会的大礼堂。可见这几个地方给我印象之深。竟也有我在记忆里搜寻不到的,如一栋四层砖瓦房,位于学校锅炉房后面。2019年9003班回校聚会时,该女生班的几十名同学在这栋曾经的女生宿舍楼前的空地上流连忘返,这是她们的记忆。因为有此情节,最近一次回去时,我也有心拍下了一张它的照片,和两年半前相比,如今它已完全掩映在草木丛中了。

安师教师宿舍楼(约摄于1984年)
对自己住过的宿舍楼,我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情。第一次回去时它还在使用中,外墙新近粉刷过,干干净净,只是西侧入口处围了栅栏,设了铁门。当时觉得刺眼的是,楼西的篮球场四周,压着边线安置了水泥板凳,这岂不很容易造成球员受伤?第二次回去时,自1998年安师撤校后走马灯般在此驻扎过的华东师大安亭实验中学、上海市安师高级中学、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等均已停办或撤离,校园空置,教工宿舍也人去楼空,铁将军把门。但从照片看,因为是春季,楼前墙旁草木长势旺盛,郁郁葱葱。后来几次回去,我则每次都感觉到,此楼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去过了。我自然也被挡在隔离带外,视线也被越来越茂密的草木遮蔽。

安师教工宿舍楼(摄于2005年冬)
不必说,校园物业方面对此楼所作出的处置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我也不妨将此看作是一种保护。我不知道楼里现在是什么状况。其实,我宁可不再进入。对我来说,这栋楼就是原来的样子。它还就在眼前,从外面眺望和窥视也的确没有改变。我不免会自以为是:它是为我们的记忆留存着吗?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近十数年间,出现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紧挨着铁栅栏门的是底层西侧顶头一间“耳朵房”,当年住着一位叫尤学忠的语文老师。我上大学时课堂上讨论过一个题为《春天》的话剧剧本,编剧就是他。他也写过小说和电影剧本。尤老师的才情和爱好不止于此,年轻时当过文艺兵,擅长多种乐器。酷爱打篮球,吃辣,嗜烟。这个房间后来应该还住过别人,但尤老师的“重口味”已令这间房在我的记忆里“百味莫辨”了。
按这样的个人记忆逻辑,我每说起这栋楼里的人和故事来,很容易有如数家珍般的自爱。就从尤老师的“耳朵房”数起,每层七间都会像是一个个内容不同的藏室。我听说,有的房间里的确还留有当年未及带走或清理的个人物品。会不会有金德明的译著手稿?有蔡福华为吴惠谱写的曲子?有钱欣明画笔下的崔老师?有李亮之劫后余生的人物素描?有柴继兴尚未整理的陈年旧照?有陆伟民论高加林的片纸只字?有宋文治《放学归来》的另一个版本?

《安师职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钱欣明作于1980年代在安师工作时)

《放学归来》(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宋文治作于1950年代在安师工作时)
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的臆想。事实上,不只是这栋楼,包括也还留存着的布满爬山虎的实验楼、大礼堂、老办公楼、学生宿舍等,和我们的记忆相比,它们只是“还在”而已。好比楼旁那片篮球场,只是我们还叫它“篮球场”。这些被关闭空置的房子年久失修,本身建筑质量不高,并无保存价值,某时某刻被拆除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它们满载的记忆是多么有价值,它们依然可以被叫“篮球场”“大礼堂”“实验楼”是多么有意思。虽然我们可以用文字图画等记录下这个地方,但怎么比得上它还能留给我们一砖片瓦?何况,对安亭这座短时期内变大变新的城镇来说,她怎会不需要百年安师这样珍贵的记忆?

《花季》(胡然青,曾是安师美术老师,作于2010年代)
我不免暗自琢磨,假设这里有某一栋楼,当然最合适的莫过于眼前这栋曾经的宿舍楼,它被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加以修缮改造,成为一座在本地值得永久保存的历史文化标志性建筑,且在功能上被建设为别具特色、内涵丰富的安师校史及人物档案博物馆,假设在安师原址具备这样一座建筑,与一箭之遥的震川书院遗址遥相呼应,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一座城市来说,该是一件多大的幸事。
2021年10月13日,原安师美术教师、现为美术学教授的李亮之将他四十年前在安师工作时根据校园周边风物所作的两幅水彩画,捐赠给了嘉定区档案馆。这会是一桩意义非凡的善举的开始吗?
撰稿:张旻
编辑:刘静娴、武利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