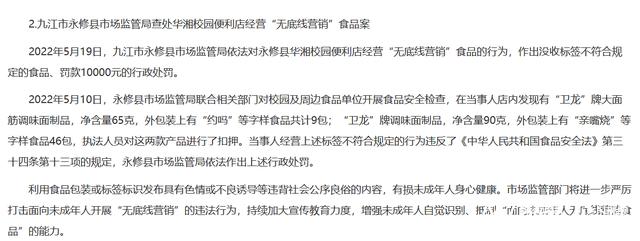涝池边上的土墙就要被拆了。

土墙(图片由合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几十年了,那一排土墙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残缺的顶部凹凸不平。夕阳从低矮处斜着照在涝池的水面上,更加显示出它单薄、清瘦、孤独、寂寥的悲壮。秋风吹皱的水面涌出阵阵血一样的通红,这样的景象无法用一支笔临摹出它们惺惺相惜的悲伤情绪。
几株野草在瘦弱的墙头,被一阵阵的秋风吹拂着弯下腰身,似乎它也在安慰即将被拆除的土墙,亦或是有一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绝望。可怜的秋草,枯黄的命运,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随风飘散在风中的草籽,好在来年的春天,为生命举起生生不息的一抹绿色。
几位当年参与垒土墙的老者,腰身弯成一张无法搭箭的弓,和土墙一样苍然。议论他们可以骄傲的过往,有人叹息:“好汉不提当年勇!”附和声、叹息声,都隐藏在夕阳下浑浊的眼神里,越来越迷茫。不说它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那一年二狗儿子溺水就是搭在土墙上才把喝进肚子里的水吐了出来,挽救了一条性命。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土墙灵得很,因为当年在垒土墙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太岁,年轻人不懂也不知道害怕,说长论短,当即被年长者制止,说是见了太岁不能出声说话,否则以后会有灾祸。大家一致商议,决定让移民来村不久的老王负责把太岁送走,凡是见过太岁的,都要烧香磕头奠酒,才能消除灾祸保平安。大家还凑钱买了一条大红被面,给老王披了红,才算结束。
土墙垒起来后,传说便慢慢淡了下去,在实际生活中,它只是矗立在涝池边上的一排土墙而已。也是小孩子们爱玩耍、捉迷藏的好去处。我家离那不远,小时候经常约几个年龄相仿的同伴在那玩耍,除了胆子小,不敢下池,几乎没有我们不敢玩的。虽然我个头矮小也曾靠自己的毅力爬上过土墙的墙头,威风凛凛得像是干成了多大成就一样趾高气扬。日复一日,墙头的草被磨得没有了生命,光秃秃的在太阳下还能发出一些亮光,墙头丝毫不会被雨水冲刷得凹凸不平,光滑的程度,甚至鸟儿都不愿落在上面。
通上自来水后,涝池不再是村民情感的寄托,挑水、饮牛的人越来越少,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再也不会把风姿绰约的魅力和念想留给那些借挑水挑逗的小伙们,热闹了多少年的场景,成为那一代人大脑里拷贝的底片,被逐渐荒废。周围的野草一年比一年稠密旺盛,我们也长大了一些,胆量也大了一些,每年在仲夏时节,几个要好的伙伴背着大人偷偷跑到涝池游泳,衣服都搭在了土墙上,天气炎热,抵不住水里的清凉,在缺水干旱的地方能畅快地戏水,填补了我们少年时光的缺憾。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被大人发现,每当这时候我们就像是他们的敌人,一脸的憎恶,挥起皮鞭,钻心的疼痛,满身的伤痕,很晚了还不忘再训斥一番,以恫吓的口吻警醒我们,谁谁谁以前掉池里再也没上来。
时光过得很快,今天的村庄早已今非昔比,水泥路面明晃晃的,两边的绿化早已成行,头脑里乱七八糟的场景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比不上城市的设施,但相比过去也是十分的整洁利落,整个村庄的变化从各个方面,每一处角落都能体现出来,每次回家我都会出来走走看看,倒不是欣赏村庄的美丽与时尚,而是用背离的情节,找回一些当年的回忆和感觉。离开村庄多年之后的记忆越来越少,触动心弦的事物在大脑中变得模糊,能找到情感寄托的事物,被时光的变幻埋进了岁月的沟壑当中,即使偶然被提及,也难有当年的万千感慨。不是说情感变淡,也不是忘了曾经拥有过的快乐,只是生活的节奏太快,早已身心疲惫无力再纠结于那些瘫痪的情景,唯有屹立的土墙还孤独地在那。陪伴他的老槐树早已不知去向,墙头也没有了当年的光亮,残损了是它唯一的结局,像一个走向暮年的老者,低下了矮小的身段,在岁月的风霜里苟延残喘。秋风中枯黄的草色犹如轻轻唤醒的浪花,再也没有了拍岸的激情!感叹世事也好,凭吊经年的美好也罢,生命就是在无限的轮回里彰显生命独具的魅力,土墙再次融入泥土当中,以另一种方式生存,用它更加宽广的胸怀容纳生命茁壮地生长,哪怕是一株或无数株野草,因为生命的价值大于一切。
秋风中的土墙似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已经完成了它作为土墙的使命,拆除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所有事物都是在轮转中生生不息,我眼前的土墙也有着同样的宿命。停靠在我心灵左岸的是对故乡的眷恋,熟悉的人物和场景在回味中就像一道爽口的饭菜,越嚼越有味,故乡一直都在清风明月里,在我难眠的梦乡,久久地,久久地难以割舍。
土墙伟岸的身躯真的成为了往事,成为一代人情感复杂的谈资。传说也好现实也罢,伟大的历史进程和自然轮回相辅相成。面对欣欣向荣的新生活,我们由衷地高兴,日益改善的民生工程更是符合当下老百姓的愿望和心声。一场轰轰烈烈的涝池改造项目被提上日程,当铲车、挖掘机嘶吼着挥动臂膀,伸向土墙的时候,轰鸣声掩盖了人们的感叹和议论,土墙连同那些荒草被一同铲倒,留下空旷的缺口和心灵上一番撕扯的纠结。(西藏阿明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