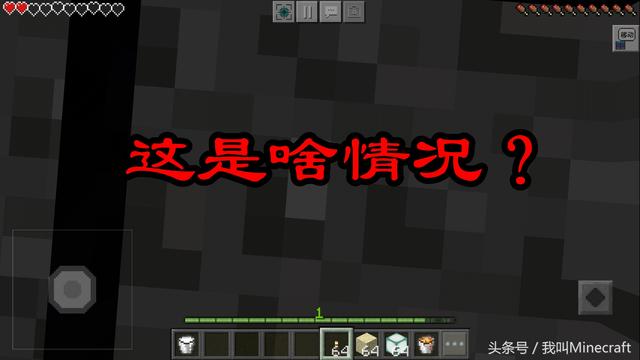此文是我发布在我个人公众号《杨衡》上的文章《研究生培养体制才是我国科研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其改革已刻不容缓》,已得到几位专家认可,也有顶级学术期刊的统计数据做支撑,广泛宣传推动政策落地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能得到您的认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可以举办线下讲座讨论。谢谢。
作者简介:杨衡,生于1983年,36岁,山东大学化学博士,北京大学化学博士后。邮箱:yangheng29@qq
世界顶级学术期刊《Nature》近期对博士生生存状况进行了持续关注,发布了《2019年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全球6300余名博士生参与调查统计),紧接着又发表了三篇调查数据的分析讨论性文章,最后重磅推出中国博士生调查结果。
2019.11.07,《2019 Nature PhD Students Survey Data》
2019.11.13,《PhDs: the tortuous truth》
2019.11.13,《The mental health of PhD researchers demands urgent attention》
2019.11.20,《A message for mentors from dissatisfied graduate students》
2019.11.26,《PhD students in China report misery and hope 》对
全球博士生调查结果显示,博士生存在抑郁、学术难搞、工作难找等严重问题,并重点强调四分之一博士生想重选导师,五分之一博士生认为与导师的关系不利于自身发展。《Nature》官方呼吁重视博士生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博士生的焦虑和抑郁感正在加剧,需要系统的改变研究文化来改善下一代研究人员的健康状况。
在对中国博士生的调查中发现, 5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导师的单独交流每周不到一小时,而在中国以外这一比例为49%。有受访者说:“不幸的是,许多导师没有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帮助和指导,因为他们正忙于申请基金和其他项目。”一些受访者抱怨说,他们的实验室感觉更像是一个商业工厂,而不是一个培训场所。就像有人说的,首席研究员拥有所有权力,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是工厂工人。还有受访者表示,许多实验室都有打卡机,记录每个成员的到来和离开时间。她说:“与其说这是一种师生关系,不如说这是一种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我国的博士生生存状况似乎更加艰难一些,特别是在导师指导和师生交流方面问题颇多。
《Nature》从关心每一个研究人员身心健康和自身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改善博士生培养状况的重要意义,这个角度具有非常浓郁的西方特色,但好像还不足以使我国充分重视博士生的培养问题。
我的研究发现,具体到我们国家,改善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培养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关怀的范畴,博硕士的培养状况是决定我国科技进步的最重要因素,不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所有关于科技进步的政策改革和经济支持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效果。(注:下文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统称为研究生。)
早在2015年5月份我在北京大学化学院博士后出站以后就开始思考研究生培养的问题并着手系统写作,于2015年9月在个人博客公布了《带你了解科研界》一书,呼吁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详细论述其中的道理。2016年10月又经过一年的思考和改进,增加了多个章节。之后的时间一直到现在,我曾经尝试过博客公开、给全国数千名学者发送电子邮件、书籍出版、制定商业计划引入商业支持、改编成剧本用影视剧的方式宣传理论、现场讲座等各种方式,也给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各部门邮寄了50多封纸质信件,希望我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充分重视,可惜全都没有太大进展,期间所历艰辛一言难尽,但我一直坚信我的理论能够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贡献力量,把理论宣传出去并付诸实践始终是我应尽而未尽的一份责任。
现在看到了世界顶级期刊《Nature》对博士生的关注,我非常高兴。《Nature》的权威性比我个人更会让大家相信研究生培养体制存在问题,将来一定会是自然科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甚至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借助这个研究热点的兴起,向大家传播思想,讲解具体到我国,现有研究生培养体制给科技进步带来的种种顽疾,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一起完成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的重任。
虽然我国科技事业起步晚、底子薄,能取得现在的成就已经殊为不易,但我们依然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在科技领域还存在很大差距,美国敢于挑起贸易战的底气之一就是其巨大的科技优势,在科技领域不突破不领先,我们就会一直受制于人,我们必须要在科技领域寻求改变,不能满足于现有成绩。
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科技领域改什么?怎么改?改成什么样?
我认为在改什么的问题上,大家并没有选对方向,这一步没做出正确选择,后续工作就毫无意义。我的思路是找到一个科研领域最关键的点,这个点与科研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关系密切,并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后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个点的问题,通过一点作用到全局,以最小的付出收获最大的成果。
之前我们的关注点都聚焦到了院士、长江学者、教授、副教授等“导师”的身上,认为他们是科研主力军,不断围绕他们一方面加大支持,一方面减压减负,期待他们能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上,发挥出最大能力,贡献出优秀成果,但是具体效果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并不是十分理想,这就说明我们并没有找到关键点。
怎么找这个关键点呢,我们可以使用不断显微化的思路,在“细胞”层面找到突破口。由于之前我一直在高校进行科研活动,我的思考和论述也都是基于科研院所的经历和调查,但应该也适用于其他科研部门。科研院所中进行科研活动的“细胞”级单位就是成千上万的课题组,他们承担着所有研究课题的研究任务,要找关键点,就要先从课题组的日常运转模式开始研究。
课题组一般由导师和研究生组成,肯定会有一个导师是课题组长,如果课题组比较大,还会有一个或多个助理导师,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相互关系由导师负责制限定,导师对研究生选择研究方向、把握研究进度、发表研究论文、获得相应学位等都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一个课题组获得研究经费以后,开展研究的具体模式如下图所示。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决不能一杆子打倒一船人,肯定不是所有导师都在以下图所示模式运转课题组,这一点也有统计数据作为证明。但他们却一定要拿出精力来与这种模式作斗争,因为以这种科研论文流水线模式运转的课题组在抢占科研基金方面效率更高,可以占据大量科研资源,最终形成的局面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用这种模式,课题组就会面临巨大的生存问题,成果“不多也不快”,拿不到或者不能拿到足够多的科研基金开展研究,最终所有人都掉进了恶性竞争的漩涡。这种模式打乱了节奏,影响了心态,使大家根本不能全身心的按照客观的科研规律开展科研活动。

中国课题组运行的具体方式
(1)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用导师负责制联系起来,导师在决定研究生论文发表、毕业签字等方面都具有绝对权力。
(2)研究生负有毕业和找工作的压力,必须要发表论文,导师在指导上可以有较大选择空间,即使不正确的指导或者不指导,研究生也会自动加班加点做实验。
(3)研究生进行具体实验活动,导师则可以远离实验室。
(4)研究生本来就有毕业找工作的压力,想要毕业找工作,就首先要满足导师的要求,而导师的要求却不一定是合理要求,他们常常利用这种权力迫使研究生快速发表大量高水平论文。
(5)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不会去冒险进行开创性尝试,他们会选择退而求稳,选择趋势已经比较明显的研究方向,这样肯定能出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则可以成为导师的工作成绩。
(6)导师们用这些成果向国家交差,课题结题,再次拿到科研基金,并参加学术会议。
(7)由此我们产生了大量原创能力不足、实用性差的论文,并无太高价值。
(8)这种模式造成了导师和研究生共同的智力浪费,导师们远离实验室,研究生们则偏离正常科研规律开展实验,都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
这就是我国课题组的基本运行方式,科研界很多顽疾例如原创能力不足、科研经费总是不够、论文成批产生、高压之下铤而走险学术造假、恶性竞争身心俱疲等现象都可以从这张图中得到解释。
可以先拿出两个证据来证明上图的正确性,第一是一个小范围的调查统计(104名研究生参与问卷调查)。
(1)问卷调查:您的导师以何种方式参与科研活动
A 只负责拿到科研基金,既不指定大方向也不参与具体实验过程3.85%
B 负责拿到科研基金,指定大方向,但不参与具体实验过程 13.46%
C 负责拿到科研基金,指定大方向,参与讨论,但不参与具体实验过程 58.65%
D 负责拿到科研基金,指定大方向,和研究生积极讨论,参与具体实验过程,偶尔一旁观察实验也算具体参与 24.04%
统计数据表明,只有24.04%的研究生导师会进入到实验室,其他导师们顶多是以讨论的方式参与研究,而常年以讨论的方式参与研究,只会是一种纸上谈兵式的指导,没有太大意义。
(2)还有一位院士在国内某次最顶级科学大会上的公开发言:“我已经几十年不做实验了,只有在照相的时候才穿一会白大褂,我做实验干什么呢?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多打几个电话,多搞一点科研基金。”
一位院士能在国内顶级科学大会上公开这么说,而且当时还获得了掌声,很多与会科研人员感觉好像取到了科研的真经,从此有了飞黄腾达的指引明灯,可见问题已经多么严重。
多数导师滥用了导师负责制给予的神圣权力,以决定研究生发表论文、毕业签字等为手段,把研究生变成了导师的廉价劳动力,这也是研究生不断扩招的内部驱动力,研究生越来越多,但指导却越来越粗糙。研究生本来就科研能力不足,却主要从事具体科研活动,再加上导师利用导师负责制对研究生施加了额外压力,要求他们快速大量生产科研论文,导致他们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根本不敢做冒险性尝试,只能做已经探索出明显发展趋势的延续性工作,贡献不出创造性的高水平科技成果。还有一种情况是导师们在校外有工厂或企业合作项目,直接就把研究生当做工人派进企业工作,到毕业前挤出一点时间草草完成毕业论文,根本不以培养科学家为目的指导研究生。
而导师有了研究生这个替身,则可以远离实验室和科研活动,只做方向性指导,以讨论的方式参与课题,对课题具体进程根本不了解,其讨论和指导的价值不会很大,也不能贡献太多创造性高水平成果。他们远离实验室和科研活动以后,就有了大量时间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兼任各种职位,不参与科研活动的同时却能从研究生那里源源不断的获得具有一定水平却不是最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向国家交差,获得荣誉、职位和金钱。
国家的投入换来的却是一堆一堆没什么意义的科研论文。这种局面导致了导师和研究生共同的智力浪费,使科研活动成为大量“模仿”性论文的生产线,使科研资金投入全都消耗在购买各种仪器和药品上,使各种科研政策,包括为科研人员减压减负、减少科研人员社会兼职、避免纯粹以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等一系列努力都达不到预期效果。
特别是我国的科研基金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仍显不足,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要不断增加科研基金总量以外,也一定要考虑怎么花钱的问题,打断科研论文流水式生产线是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不做无用功,不浪费,这也和研究生培养体制密切相关,因为研究生是这些论文的具体生产者。
这一切乱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培养体制,其核心是导师负责制。
我们还可以用目前一个热点话题--曹雪涛院士论文造假问题来验证这个思路的正确性。
2019年11月13日,曹雪涛院士在人民大会堂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面对现场6000名以及全国各地观看网络直播的约80万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做了精彩演讲,他的报告题目是《弘扬科学家精神,打造新时代中国学派》。其中提出,青年学者是推动科技变革的先锋,勉励青年学者们,要做爱国奋斗、诚实守正的科研人。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19年11月14日国外一位学术打假专业户就公开质疑了曹雪涛院士论文数据造假,后续又有几十篇论文被质疑。曹雪涛院士于2019年11月19日对质疑进行了公开回应,特别指出,自己作为领导者难辞其咎。目前此次事件还没有一个确切结论,大家还在等待最终调查结果。
我们先不管曹雪涛院士事件的最终结论,只研究他的那句:“作为领导者,我难辞其咎。”难辞什么咎?他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管教无方,领导不力。所以他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位领导者,一位指挥者,或者说指导者,言外之意,他并不完全了解研究生所有的实验过程,还可以推导出对于造假他可能毫不知情,是研究生们在造假。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既然你毫不知情,为什么又是论文成果的拥有者?既然毫不知情,怎么指导研究生?既然毫不知情,没参与实验,平时那么多时间都在做什么?很多关于此事的网络文章下面的留言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做实验基本都是研究生的事情,导师们不用参与太多。这和我上面的分析是完全吻合的,也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更是我国科技界最严重的问题。试问如果不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的思路还能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2018年12月18日,韩启德院士在中国科协和北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科学文化研究院”成立大会致辞中重点提到了一个问题:已经提了半个多世纪的科研人员“要把5/6时间花在科研上”至今未能实现。这个问题不仅是至今未能实现,实际上很可能越来越严重,连最起码的科研时间都保证不了,别的就更无从谈起了。而不用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科研上的原因本文早已经论述清楚,就是因为现有研究生培养体制为导师们提供了研究生这个替身在实验室进行科研活动,已经有了替身,自己当然可以不用再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研究生们也早已不把导师当做导师,而是当做老板,平时就是这么称呼。我的思路能完美解释韩院士的问题。
(韩启德院士简介: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大医学部主任,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研究生培养体制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吗?肯定不是,至少科研界绝大部分人是知道的,但为什么没有人指出来呢?因为对于“导师”来说,这是大家共同的“饭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网上充斥着从各个角度论述科研体制不合理的文章,也有言辞激烈的,也有温文尔雅的,但是却看不到会有一位研究生导师站出来说研究生培养体制有问题,因为谁公开说出这句话,谁就等于得罪了“整个科研界”,触碰了底线,砸了所有人的饭碗,不能在科研界有任何发展了。而对于研究生群体来说,他们位卑言轻,没太有发声的机会,况且学习时间就只有几年而已,咬咬牙就过去了,不值得为此付出太多。科研圈内人不说,圈外人不了解,这个问题就长久存在下来了。
不仅现在科研界的种种问题都与研究生培养体制有关,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研究生还是我们科研的未来,他们将来要成为导师、课题组长和技术人员,要进入高校、企业等各个科研部门。不合理的研究生培养体制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学到应有的科研技能,没能按照合适的节奏成长,特别是对科研活动的理解产生了巨大误解,将来会体现为偏离科研规律的科研行动,这些行动又会深刻影响下一代研究生,一代一代发展下去,会彻底毁掉我们科研的未来。
随着我国的逐渐崛起,必然要摆脱依赖留学体系得到高水平科技人才的现状,建立自己的优秀的博硕士培养体系,应对已经开始出现的某些发达国家对我国留学生的收紧政策,这也迫使我国现在就必须要着手进行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
所以研究生培养体制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导师负责制是最核心问题。
研究生培养体制要改成什么样呢?我想基本原则是使课题组运行管理公开透明,给导师一个合理比例的权力即可。可以为课题组引入多层监督机制,学院、学校、研究生院和学生代表都在一定时间点考察课题组运转状况,参加组会和讨论,条件允许时也可以进入实验室实地考察,督促导师进入实验室,使师生按照客观科研规律开展科研活动,使研究生健康成长。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我想肯定还需要大家组织起来一起研究出一个最佳方案,前提是大家已经充分认识到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讨论或组织论坛讲座,我的讲座课件已经完成,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原因讨论、科研管理的基本困难、我们如何突破、科研问题对其他社会问题的借鉴等很多很有价值的问题,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此文内容仅为讲座课件的两三页。
在此我提出一句口号: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导师们穿起白大褂,回归实验室。相信我们的科研会越来越好,让我们共同为之奋斗吧,多多发朋友圈,多多转发,越多人看到这个问题,就会有越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就能越快得到解决。
相信宣传的伟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