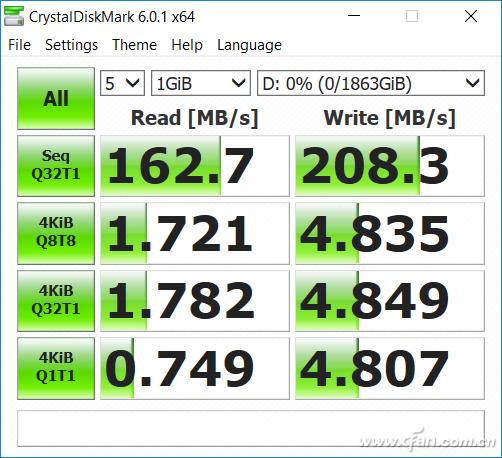▲题图:郭庆丰 油画作品《瓦豹》布面 50×60cm

文 常文树
曾在陕北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王克明先生2007年出版了研究陕北方言的专著《听见古代》,搜集了3900多个词语,并尽量从古代典籍中找到出处,称“听陕北人说话,如同听古人言”,对陕北方言钩沉探玄,做了大量的工作,终成巨著,一个外地人成了研究陕北方言的行家,令人感佩,用陕北话说叫“强龙压过了坐地虎”。好在陕北土生土长的王六先生于2010年出版了《把根留住》的大型陕北方言成语词典,也搜集了3900余条,与之堪称伯仲,令人欣慰。以前,只是看过一些零零星星的陕北方言研究专著,觉得不够足劲,这两部巨著的问世,标志着陕北方言研究进入了高峰期。我想,现在只缺一部陕北方言熟语大辞典,如再将陕北流行的惯用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搜集几千条,同前两部鼎立,汇成陕北方言大全,岂不美哉!
只有期待了。
不过,王克明先生“听陕北人说话,如同听古人言”的感受是准确而深刻的,因为陕北方言虽然属于北方方言,但其保留了大量的文言词汇,并在千百年的口口相传中沿袭了一套独特的语音系统。在语汇方面,随便抓一句做个解剖,就会发现有文言词的存在,例如“缠甚叻,咱走吧”这句常用的土得掉渣的劝人的话,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来说,就要说成“纠缠什么哩,咱走吧”,这“缠”和“甚”就是两个典型的文言词语。在语音方面,从声母韵母到声调,同普通话比较,有同有异,在陕北人看来是大同小异,因为陕北人听普通话基本无障碍,可在其他语系的北方人看来是大异小同,因为他们听纯正的陕北方言,只能听懂一小点;而语音中的最大不同在于入声,陕北方言中保留着古代语音中大量的入声字,普通话则不存在入声。如石、菊、竹等入声字,在普通话中都读成平声中的阳平了,一个只会说普通话而不懂得古代音韵学的人是无法读出入声的。所以,王克明先生才会得出“听陕北人说话如同听古人言”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陕北方言得到了“语言中的化石”的美誉。但王克明先生对陕北方言的考据,最早只追到了隋唐,也就是音韵学所谓的中古时代,大量的是宋元明时代,这虽然符合陕北主体方言的实际,但够不上化石级语言的标准。其实,陕北方言中还保留着一大批上古甚至远古时代的语汇,这些语汇才堪称语言中的化石。
这里略举几例,以与读者共赏。
旱魃,天旱时易出现的龙卷风。《山海经》记载神话传说:黄帝擒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里单用了一个“魃”。《诗经·大雅·云汉》则写为“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意为旱魔为害很暴虐,好像大火在燃烧。后来旱魃也被称为旱神。我们小时候,老农一见到这样的龙卷风,就会喊叫:“呀,旱魃来了。”现在较少听到了。在有典籍可查的陕北方言中,这个词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它穿越上古,直达原始部落的远古时代。
永世,永远的意思。《尚书·微子之命》:“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典籍,这里记录的微子,是商末周初人,可见这个词语的古老。陕北方言中常常听到这个词语,如“人家的光景好,咱永世也撵不上”、“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
让,谴责、责备的意思。《左传》记,僖公五年:公使让之。《史记·项羽本纪》:二世使人让章邯。这个词,在陕北方言中读为平声,如“你那是夸人呢还是让人呢”、“你那算让答谁叻”、“我美美把那狗儿的让责了一气”。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他的《古代汉语》中,将这个字的责备和谦让两个意思的读音全注为去声,这是不够确切的,一方面说明他没有听过这个词的平声读音,另一方面又与他上古无去声的主张相悖。
觳觫,因恐惧而发抖的意思。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中有“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个词在陕北是连小孩都常用的口语词汇,如“怕得我觳觫一下”,而《现代汉语词典》却注为书面用语了。
灰搏,用碗盛灶灰击打怪异,引申为最严厉的击打,一般用于警告。如“缠老子灰搏你狗儿的叻”,这是陕北人警告式骂人语言中最严厉的一种了,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再纠缠老子,老子就彻底砸扁你狗杂种”。这个词语起源,最迟也应在战国时。因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春秋时羌部落曾建义渠国,其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战国时为秦所灭。现在,陕北的老年人及懂阴阳道术的人和甘肃、四川的羌族人都保留着用灰碗击打所谓鬼怪的旧习,虽然我们无法考证这种习俗是羌人传给陕北汉族先民的,还是陕北汉族先民传给羌人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一习俗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在陕北形成的最晚时间也应在战国时秦灭义渠之前。
提,打的意思。《战国策》荆轲刺秦王一文中有一句“侍医夏无且以药囊提轲”,文后对“提”这个字,注音若“底”,释义为打击。意思是对的,但注音值得商榷。此文虽然是燕策,但秉笔人像秦人,因为直到今天,三秦人还保留着“提”做“打”的古音,关中陕南一带读若“叠”,陕北一带读为入声字,音若陕北人说“跌倒”的“跌”,如“提了那小子几棰头”。
归孙,语出《尔雅·释亲》“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谓侄之子为归孙”,意思是妇女称娘家侄孙为归孙,可见上古无骂人义。后因归孙为小字辈,引申为小子、小人、宵小之徒,有骂人义了。陕北方言保留了这个古代词语。这里的“归”字显然用的是它的本义,《说文解字》释“归”本义为“女子出嫁为归”。《诗经》有“之子于归”,就是“这个女子出嫁”,用的就是它的本义。与“归孙”相关的陕北方言中,骂人词语还衍生出“归之子”“归之儿”“归儿子”,意为女子出嫁时就有的娃娃,自然是杂种,骂人挺厉害的。这里要指出,这些词与另一个骂人的词“鬼子”是大为不同的。“鬼子”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骂心术不正之人的,在古代使用并不多见。现代汉语中被大量运用,但,是专骂外国侵略者的,不能用于国人。再说,现代汉语中,“鬼子”的“子”字读轻声,更不能写成“鬼子子”,与陕北方言中骂人的“归之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从以上几个上古时就有的陕北方言中,你是否也产生了研究陕北方言如同研究文言文、听陕北人说话如同听古人言的感受呢?
随着普通话的不断推广,随着全国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随着现代传媒下的全民多层次的大融合,陕北方言与其他方言一样,总有一天会淡出历史,我们没有必要去遗憾,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们一切文化工作者却应像王克明和王六先生那样,尽自己的努力,记录下陕北方言,把它像档案一样存放起来,为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提供最好的历史资料,这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