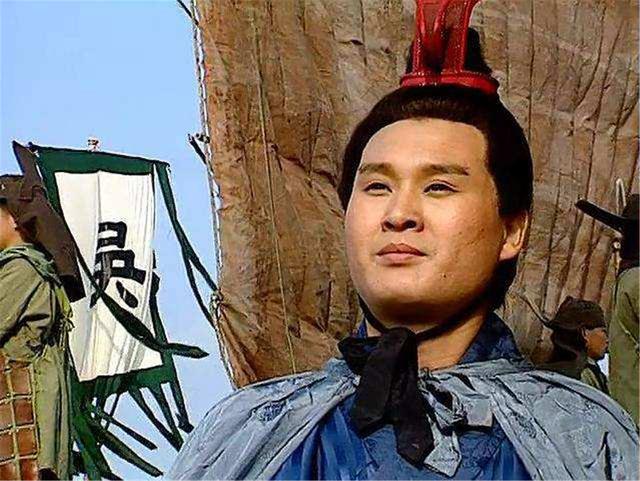引言:全历史、半历史,“儒、文、道”三位一体
先区分一个概念:“全历史”和“半历史”。全历史就是基于整体历史的,以整体的历史为历史;半历史则是基于局部历史的,以局部历史为整体历史,错把局部当整体。
从文明、文化研究上而言,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半历史”问题,其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都是半历史的。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文明史而言,传统上一直是一个三皇五帝框架,这是一个整体史。但是现在人却自以为高明地认为古人是瞎说,任意地切割,认为中间某个位置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典型者如以农业出现为起点,以汉字出现为起点,以政府出现为起点,以城市的出现为起点,如此之类,五花八门,总之都是半历史的。
在当下所流行的所有的半历史观点中,有两种非常值得注意。一个是民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所捣鼓出的5000年说,选定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另一个则是出现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德国,但最近一二十年逐渐开始在中国走红的“轴心时代”说,认为中国文明的起点在春秋战国时期,本来被孔子斥责为“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孕育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成为中国历史的起点,实属荒唐。
“儒”、“文”、“道”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三要素。也可以说,“儒”、“文”、“道”是三位一体的,三者密不可分,同时起源,一直并存,共同组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历史就是“儒”的历史,也是“文”的历史和“道”的历史;中国文化就是“儒”的文化,也是“文”的文化和“道”的文化。
“儒”就是“大人”,是社会的中坚和基石,基于道德威望承担着消除分歧,促进合作的社会治理职能。“文”则是“儒”的赖以治理社会的工具,最先是契约之“文”,包括结绳和书契,后来是文字之“文”。而“道”则是“儒”在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所秉持和总结的道理,其根本目的是,既让人能够充分顺应和发挥个体的本心本性,又能使得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互助协作,最终实现社会的和平有序,即“天下太平”。
“道”是本于人心的,本于“大人”之心,本于“儒”之心,同时又通过“文”来体现,先是通过契约之文,然后通过政府的礼仪制度之“文”,以及文字之“文”。
“儒”是“道”的总结、发明者,践行者,传承者。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道不远人,远人非道”。“文”是“儒”行道的工具,也是“道”的呈现和表达载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以载道”。当然,“文”也是由“儒”所发明。
这样,在“儒、文、道”三者之间,唯有“儒”具备主观能动性,是核心、主体,而“道”和“文”都是依附于“儒”的,为“儒”所发明,又由儒所践行。
因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更根本的角度,就是“儒”的历史和“儒”的文化,即“大人”的历史和“大人”的文化。儒的职能是在尊重个体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即治理。治理社会就是行道,为了更好地治理、行道,就是需要“求道”。
现代人会把“求道”看成是知识积累,属于“学术”、“学者”的范畴,把治理看成是“政治”。其实,对最初的“儒”来说,“行道”和“求道”是一体的。即便是治理,实际上也与现代的政治不同,更多是一个说理、评理的过程,一个说服和教育的过程。
当然,随着历史的推进,儒的存在状态也发生了不断的变化,原本一体化、集中于一人之身的各项职能也开始专业化和分离。譬如政府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学术的出现等。在这个过程中,“儒”、“大人”这个群体就是一个不断分裂的过程,不断分化成不同的职业团体,甚至不同的流派,譬如战国时的所谓的“诸子百家”。下文将详细展开讨论。
前通过甲骨文研究,我们基本说清了“儒”的内涵问题。本文将对“儒”的存在状态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演变过程做一个俯瞰,帮助大家对“儒”有个更立体的宏观把握。
整体来说,儒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包括五大阶段。第一阶段,从伏羲到尧舜:契约中介;第二阶段,从尧舜到甲骨文:官员化;第三阶段,从甲骨文到春秋:文字化;第四阶段,从春秋到戊戌变法:学术化;第五阶段,从戊戌变法到现在:沉寂和复兴。
第一阶段,从伏羲到尧舜:契约中介
这一阶段就是传统所说的“三皇五帝”时代,是五大阶段中最漫长的,时间跨度至少在6000年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最美好的时代。那时的中国社会还只有一重,没有政府,没有官方、庙堂,只有民间,只有江湖。
现代人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会想当然地认为,那将是一个混乱的无序世界。事实上,那个时代不仅有序,而且令人神往。《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工)以治,万民以察”,正是对那个时代治理方式的记录,是“结绳而治”,“书契而治”或“刻木而治”。“刻木”就是刻写制作书契。
结绳和书契是什么?是中国历史,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而治”、“刻木而治”实际就是“契约而治”,即以契约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这个时代也可称之为“契约时代”,纯粹的“契约时代”。
老庄、道家最崇尚的就是这个“契约时代”。老子说的“自然”,“民自为”、“自化”其实就是指契约时代的契约秩序。老子说的“无为”,也是反对政府的存在,政府要“无为”,而让社会保持单纯的契约秩序。老、庄子也都认为“契约时代”是“至治”、“至德”的。
《老子》中专门拿出一章对契约时代的社会状态进行了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什伯之器”就是十倍、百倍与人力的机械。
《庄子·胠箧》引用为:“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整部中国历史也就分为两大阶段,两大时代:契约时代和政府时代。中国文明的内核正是在契约时代形成的,并延续了很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就是“契约文明”。契约的起源在中国,也只有中国的上古时期存在一个漫长的契约时代,中国之外任何文明的契约思想和契约文化,包括古两河法律化的契约思想、犹太教的神学契约思想、以及近代西欧的政府契约思想,都大大晚出于中国,且突然出现,都不曾存在独立的契约时代,没有独立而漫长的契约实践史,因此只可能是外传自中国。
但是遗憾的是,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让中国的历史出现巨大的断裂,以结绳和书契为主要契约形式的契约时代迅速消失。“礼乐”的内核就是契约,“礼崩乐坏”的实质就是契约秩序的崩溃和消失。
战国时代的老子和庄子,之所以还对契约时代记忆清晰,明确倡导“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即倡导复兴“结绳时代”,复兴“契约时代”,原因在于,在战国时期,结绳社会、契约社会的状态可能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结绳和书契的迅速消失与汉字的迅速普及是同一个过程,即被文本化的契约替代。
也就是说,结绳和书契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契约本身的消失,而是契约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文本式契约。关键的问题并不在契约形态的变革,而在与契约变革同时发生的其他领域的社会变革,主要是因法家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变得利益化、专制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这导致政府的作用大大上升,而契约的地位则大大下降。政府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契约下降为一个从属性因素。
政府在中国的肇始是在黄帝时期,但是正式出现则是在尧舜时期,也叫唐虞时期。在整个三代时期,尽管存在政府,但是,就整个社会治理而言,政府居于次要地位,契约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即“三代”依然是契约社会。契约社会的迅速消失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结果,也可说是法家文化冲击的结果。在尧舜之前,则是一个纯粹的契约社会,因为社会的治理工具只有契约,而没有政府。
结绳和书契都是无字契约,结绳和书契本身也都是一种符号,信用符号。更详细的契约条款还是语言化的,与结绳和书契本身一起,构成完整的契约。当春秋战国之后,汉字的使用开始迅速普及,契约的形式开始文本化。此前以语言形式存在的契约条款,被形成文字。而之前的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信用符号:结绳和书契,则被制成平面化的符号:印章。
印章实际是结绳和书契的遗存,而成为现代契约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从甲骨和金文字形上看,“印”的甲骨文字形为“手”加“卩”。“卩”为结绳的右绳,在结绳契约中,右绳代表借据,相当于现在的欠条。“印”甲骨字形的含义就是手拿着借据(凭信)去要账,其原始含义是凭信,而且是结绳凭信,是实物化的、三维化的。
“印”的甲骨字形与“令”、“命”、“要”、“索”等都是一致的。“命”的本字为“令”,后来多加一个“口”独立出来成为“命”。“令”的字形为上“亽”下“卩”。“亽”就是“合”去掉“口”,意思与合相同,为相合。“卩”为结绳之右绳,相当于借据式的凭据。“令”甲骨字形的整体含义是,拿着凭据去相合、要求。“要”和“索”的甲骨文或金文字形都是双手捧着绳子,意思与“令”相同,拿着结绳凭据去要求、索要。
“章”没有甲骨字形,但有金文字形,是对一对新刻写完成的书契的刻画。

但是,印章的主体是汉字,印章是信用符号,实质上也是汉字就是信用符号。文字化的“印章”是中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其实质内涵是,汉字具备信用符号的职能,汉字中存在可以让人信赖和崇尚的独立意义。
与契约印章文化并行的,是篆刻、书法文化,这也是中国所独有的。一副书法,甚至一副小小的篆刻,都可成为独立的艺术品。
汉字的信用符号功能,还体现在古代的货币中。中国古代的货币中,只有汉字,而没有神像或国家元首肖像。古代中国的皇帝们从未考虑把自己的头像印在钱上。西方恰恰相反,那里的货币都要印上神像或国家元首的头像,因为他们认为神和国家元首是最重要的信用保障,只有这些东西才可以充当信用符号。现在美元上除了印有华盛顿的头像外,还写着“GOD WE TRUST”。
如此种种都表明,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文字崇拜”,象西方对神的崇拜一样的崇拜。文字在中国的确起到了神的作用,也正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字文化,拥有强烈的文字崇拜,也导致中国没有出现对神的崇拜,没有出现宗教。
汉字在中国之所以拥有如此独特和强大的功能,可以独立充当信用符号,甚至可以替代神,原因在于,汉字象契约系统中的印章一样,是对结绳和书契符号的继承。结绳和书契时代尽管在战国之后迅速消失,但是,结绳和书契符号却进入汉字之中,结绳和书契的精神和灵魂,被注入到了汉字中。
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汉字的起源问题。从根本上来说,甲骨文的字形来自对此前的契约符号的继承,因此甲骨文字形中实际上包含契约时代的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和价值理念。只是随着契约时代在战国时期迅速消失,后来人不仅对契约时代的记忆迅速消失,而且也对汉字字形中的契约符号无法识别了。而错误地将汉字认定为象形文字。至少到许慎写《说文解字》,就这样了。
契约符号就是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这是汉字出现之前,中国早已存在的记录符号系统,可以称之为“文系统”。实际上,在契约符号之外,易经的卦象也属于“文系统”,契约符号和八卦符号,都是“文”。但文系统的主体则是契约符号系统。甲骨文正是在“文”的基础上出现的,所以叫“文字”,即由“文”所孳乳的孩子。
“字”和“文”最大的区别是,“字”有读音,与语言相结合,而“文”则没有发音,与语言无关。
甲骨文最大的价值是其字形中的契约符号,基于这些契约符号的造字原理,包含着契约时代的历史信息和价值理念,这些都是中国文明最内核,也是最纯真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文化的“初心”。遗憾的是,对这一重要的宝藏,已经被人们忽略和遗忘2000多年。


从甲骨文“儒”、“夾(筴、侠的本字)”“朿(朿、策的本字)”、“介”的字形中,我们不仅可以得知,“儒”就是“大人”,而且还可以得知,作为“大人”的“儒”,与契约密切相关,是契约时代的契约中介。他们凭借道德和义理水平的威望,为契约双方进行评理、讲理,帮助其消除分歧,形成共识,最终实现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参见用甲骨文和《易经》追溯“儒”的起源和真义(一)
通过帮助契约的制定和执行,“儒”、“大人”实际上承担着社会治理的职能,“结绳之而治”、“契约而治”实际上也是“大人而治”、“儒治”。因此,“儒”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社会治理者,最早的政治家。“契约时代”实际上也是“大人时代”,“儒时代”。
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政治形态,一种是有政府的政治形态,另一种则是前政府、无政府的政治形态,也就是契约政治、大人政治。
现代人已经无法想象无政府的政治了,实际上,在孔子的时代,依然不觉得政治与政府必然有关,认为存在无政府的政治。譬如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对于那些蛮夷地区,即便有了政府,还不如没有政府的中国。
《论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政”的辩论: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大意是,有人问孔子他为什么不做官从政。孔子说,社会秩序的根本在“孝悌(友)”,孝悌就是最大的政道,如果能够向社会推行“孝悌”,就是按政道办事,就是在从政。
显然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政治必然政府相连,政治就是政府的政治。从政就必须加入政府,去做官。但是孔子还是在秉持一种更为传统的观点,政治与政府无关,政治的本质在治理社会,让社会维持良好的秩序。
与无政治的政治相关的还有“素王”、“天爵”的概念。孔子被称之为“素王”,即没有官位的王,孟子认为爵位有“天爵”、“人爵”之分,“天爵”就是为社会的治理做出实际的贡献,或者具备实际的社会治理能力,“人爵”就是政府的官位。
实际上,在契约时代,作为契约中介的“儒”,都是无政府政治的从政者,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家,他们也都是只有“天爵”,而没有“人爵”的“素王”。
老子说的“无为”实际上也是指无政府的政治,但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认了大人的存在和作用,否定了“儒”的存在和决定。
即便如此,老子还是对“儒”进行了记录和评判。《老子 79章》:“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段话很重要,需要详细地来解释一下。
整个这段话,实际上在在讨论和比较两种政治模式,即两种帮助人建立正确关系,消除纠纷的模式。“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说,一旦大怨形成,再去调解,是很困难的,很难真正消除。王弼对这句话的注解是:“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将“大怨”产生的原因直接归因于此前没有订立契约,或者没有人帮助他们订立契约。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这句话是在说作为调解人,作为契约中介,应该秉持的正确的态度,不能有任何的强制,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要充分地尊重契约双方,纠纷双方的意见,在双方真实情感和意愿的基础上,形成共识,达成契约。“左契”是借款人所持,就是借款人,欠钱者。“圣人执左契”,就是一个伟大的调解中介,契约中介,应该秉持借钱人的态度,要象债务人尊重债权人一样,尊重所调解的双方的意见,而不应该相执右契的债权人那样,拥有责求于人的权力。
“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就是两种政治模式,前者是“大人政治”、“契约政治”、“无政府政治”、“儒治”,后者就是“政府政治”、“官治”。“司契”就是充当契约中介,帮助契约双方建立契约。“司彻”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威,进行事后的法律仲裁。
一直以来,学界对“彻”解读,乃至对整个这段话的解读都是很混乱的。“司彻”和“司契”是相对立的,理解了“司契”,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司彻”。帛书《老子》将“司契”写成“司介”,现代学界直接说“介”是“契”的通假,是不对的。实际上汉字中几乎不存在所谓的“通假”一说,这是后人由于不理解汉字的字源意义了,而臆造出的一个概念,凡是不理解的,都是归之“通假”。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从甲骨字形看,“介”与“儒”的结构是一致的,都是契约中介,只是“儒”更强调作为契约中介,一定是“大人”,而“介”则更强调中介的义项。因为“介”原始含义就是契约中介,因此,“介”可以“契”通,而有“通”而无“假”。不过就这句话来说,“司介”,比“司契”更能直接说明意思。“司契”并非是作为契约的一方签订契约,而是作为中介,帮助契约双方去签订契约,就是使用契约进行治理,就是搞契约政治、无政府政治。对“彻”的解释有很多,总之都可以归结于政府式的治理。政府的治理有几个特征,拥有强制性的政府权威,事后的审判,政府官员需要税收来养活等等。老子直接将政府政治说成“无德”。
这段话也反应出老子思想的矛盾之处,纠结之处。整体上老子、道家是不承认“大人”、“君子”的存在的,但是,又非常重视“司契”这一“大人”的职能。事实上,“司契”的职能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承担,而只有“大人”能够承担,只有“儒”能够承担。如果社会中没有“大人”,没有“儒”,就没有人能够承担“司契”的职能,那么契约秩序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建立,结绳而治也就不能存在。而结绳而治、契约而治恰恰又是老子心目中的最理性的社会状态。
老子所不明白,或不愿意承认的是,结绳而治、契约而治,就是“大人之治”,就是“儒治”。或许,老子为了反对政府里的“大人”们,连前政府时期的大人,契约时代的大人也一块否了。

“儒”、“大人”的职能是“司契”、“司介”,而“尹”字则更具体地说明“司契”的一项工作,就是刻写书契。“尹”的甲骨字形为一只手拿着一只竖直的细棍。王国维将手持的细棍解读为“笔”,尹就是手握笔。甲骨文“聿”是“笔”和“律”的本字,而“聿”的字形则为“尹”的中的细棍下端多一个倒V,这个倒V应该是“笔”所书写的笔画、内容。因此,将“尹”中细棍解读成“笔”是正确的。“尹”就是持笔之人。
但是,“尹”所持的笔,由于现代的笔有本质不同。“尹”其实就是“大人”、“儒”,也是“司介”、“司契”的契约中介。作为契约中介,“儒”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帮助契约双方刻写书契。因此,“尹”的笔更准确地说是刻刀,所刻写的也不是文字,而是契齿文。“尹”所刻的内容就是“聿”,这个字最初也指代刻写工具,后来加“彳”和“⺮”成为独立的“律”和“笔”。“律”就是要去遵行“聿”,以尹所刻写的内容为“律”。“聿”其实就是契约条款,包含着三方意见,契约双方的,以及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儒”、“尹”的。
“卿”的甲骨字形显示,这个字的本意也是契约中介,也是“大人”、“儒”。关于“尹”、“卿”,我们还将在第二部分继续分析,因为这两个字设计到民间的“大人”向政府的“大人”的转化。
“父”与“尹”本是同字。商汤的著名辅佐者伊挚,被尊称为“伊尹”;周武王的著名辅佐者姜子牙,则被尊为“尚父”;项羽尊范增为“亚父”。这里“尹”和“父”意义相同,都是一种官员式的尊称。“父”后来从“尹”中逐渐分化独立出来,一方面更侧重家族、甚至家庭关系,后来干脆只指代“父亲”。另一方面,“父”则被用来指代职业、行业,譬如“渔父”、“农父”,就是以打渔为职业的人、以务农为职业的人。
以“父”作为一个职业称呼,用于指代各行各业,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行业分工是从“尹”开始的,即从“大人”和“儒”开始的。后来用“尹(父)”去指代其他的一切独立的行业。“大人”、“儒”是与中国文明同时起源,是中国出现文明化的主要标志,这意味着,“尹(父)业”、“大人业”、“儒业”,也是“契约中介业”,也是“政治业”,都是在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有的。但是,在契约时代,“大人业”尚不是完全职业化的,尽管是一个很重要的职能,但是,确实免费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契约时代的开始于农业出现之前,横跨渔猎采集和农业两大阶段。现代人会想当然地把农业当成文明的基本前提,事实上中国文明内核的形成早于农业的出现。而且中国传统文献对此有明确的记忆、记载。三皇五帝的第一皇一般认为是伏羲,而伏羲是早于神农的,神农代表农业。
随着考古学的深入,也越来越发现,在农业之前,已经存在发达的文明。考古学界也在逐渐抛弃农业是文明的原因的错误假设,而开始认为农业只是文明的结果。
事实上文明的孕育因素不是农业,而是由稳定的食物供给作保障的稳定的定居生活。谷物的确是稳定食物供给的主要保障,但是,获取谷物并不一定非要去种植,发展农业,靠着采集野生的谷物也可以实现。考古学已经证明,无论是西亚的小麦,还是中国北方的小米,南方的大米,在被正式种植之前,都以野生和被采集的方式,为人类提供食物保障。定居生活的出现不是靠着农业的,而是靠着采集野生谷物的。而且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推测人类定居生活最早可能出现在中国的黄淮平原地区。结合陶器的传播资料,这个时间点可以上溯至16000年前左右。这个时间点就是中国文明开始的时间,也是伏羲时代,契约时代开始的时间,也是“大人”、“儒”出现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