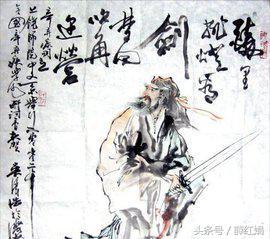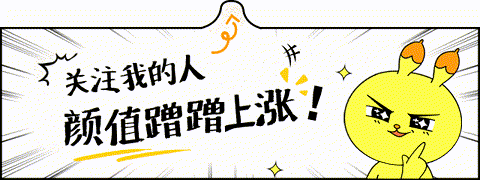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虽然是以词名蜚声词坛,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文武奇才。这首脍炙人口的《破阵子》,俨然有一股冲天的豪放气。许多人吟诵之后会顺手点赞关注,双击666。只知这首词牛气冲天,但究竟牛在哪里却搞不明白。其实要理解这首词,只须明白“八百里分麾下炙”一句的意思就足够了。
有人误以为“八百里”是词人的艺术夸张,描述手下兵多将广,连营有八百里之多。其实,这里的“八百里”说的是牛,更确切讲是历史上最牛的猛牛。
严格讲来,“八百里”这头牛的全称是“八百里驳”。八百里,是说这牛跑起来风驰电掣,就算是上了高速飙车的话也不落下风。
“驳”,外形象马却长着一只角,白色的身子,黑色的尾巴,叫声象鼓鸣,据说是一种可以吃老虎的猛兽。

据记载,齐恒公有一次骑马出行,途中碰到一只母老虎。就在齐恒公犹豫着要不要拔马落荒而逃的时候,那老虎却一溜烟的闪避了。
齐恒公见状有些傲娇,得意洋洋地对管仲说,寡人听说霸王之主出,猛兽都得主动回避,今天这老虎见了寡人就跑,莫非寡人身上当真有王霸之气?
管仲听了不以为然,得了吧您,您骑的是不是白色黑尾巴的马?老虎远远望见以为是驳,当然避之惟恐不及了。
“八百里驳”的主人名叫王恺,是晋武帝的娘舅,也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有钱烧包和石崇斗富的那个家伙。王恺家里不差钱,养的牛也非凡品,不但有专人喂养,而且每隔几天就要花钱给牛做美容,把牛角漆的光亮晃眼,就连四个牛蹄子上也抹着五颜六色的指甲油。
与“八百里驳”比起来,石崇的牛单从卖相上看就明显差了好几个档次。可是让王恺郁闷不已的是,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才知道,石崇的牛卖相不行,但是一跑起来就象是打了鸡血,每次比赛总要甩“八百里驳”一个牛身。
或者有人会哑然失笑,就算是西晋那个年代没有玛莎拉蒂、劳斯莱斯那样的豪车,日行千里的宝马总有吧?
这一开口,就彻底暴露出你是历史菜鸟的本来面目。因为,彼时上至天子、下至黎庶坐具都是牛车。所不同者,除了牛毛色是不是纯正,车的装饰、颜色、大小、型制都有严格规定的。普通百姓只能是老牛拉破车,天子、贵族的车除了外饰,就连辐辏轴轮这些都要坚实豪华……
究竟是先有的牛车,还是先有的马车,估计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据文献记载,车的发明人是黄帝,“少昊时略加牛”,车的出现虽然早,但却是由人驾驭的,最早的畜力车是牛车。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人类驯化六畜是分先后的,与猪、牛、羊、鸡、狗不同,给桀骜不驯的马套上笼头非常不容易,马是人类最晚驯养的家畜。单从驯化次序上来分析,就可以推测出牛车的出现要早于马车。与牛车相比,马车的轴心距离地面要高出许多,更容易翻车。因此,“安步当车”中的“车”只能是牛车。试想,如果是马车,早把骨头颠的散架了,那自然不能叫安步,最多勉强可以称为竞走。
牛车,无疑是古代最为安稳的代步工具。
马车最终替代牛车,是有原因的。马车虽然不是理想的代步工具,但也有着牛车无法比拟的长处,除了速度要快,坐在上面比较拉风之外,奔驰在大街上,车主可以高高在上指手划脚,让路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话事人。
俗话说有钱讲究、没钱将就。历史上,牛车并非穷人专利,皇帝是最大的地主,但到了地主家也没余粮的时候,皇帝的专车也得用牛拉。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大概是史官为尊者讳的缘故,并没有直接说汉高祖刘邦也坐的是牛车,只是委婉的说“不能具醇驷”。
驷,是指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醇、同纯,醇驷,意思就是同毛色的四匹马。

虽然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终于一统江湖,但因为多年战乱破坏的原因,大汉王朝境内居然找不出四匹同样毛色的马,搞得那些追随他打江山的文武重臣只能乘坐牛车出行。估计刘邦坐的也是牛车,最多是四头毛相同的牛而已。史官没有秉笔直书,应该是为尊者讳的缘故。
因为家底子太薄(大量缺乏战略物资马匹),刘邦死后,匈奴单元居然提出了令所有汉人汗颜的无理要求——要和吕后耍朋友(汉武帝不计成本的与匈奴死磕,与受了此事的强烈刺激有关)。汉帝国知耻而后勇,刘邦后裔子孙孜孜求治,汉文帝、景帝适时与民休息,推行无为而治也是无奈之举。等到国力略有恢复,牛车立即没了市场,汉景帝专门颁布了各级官员的乘车标准,规定只要是商人,生意不论做得多大,也“不得乘马车”。
汉武帝刻薄寡恩,搞得一些诸侯倾家荡产,这些人死要面子,为了撑门面出行又套起了弃用多年的牛车。这些诸侯虽然成了破落户,但毕竟是寻常百姓眼中的龙子凤孙,这些家伙乘牛车,事实上等于再次提高了牛的社会地位。
著名大孝子王祥卧冰求鲤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一度上了热搜榜,统治者得知后征召他入朝,坐的也是牛车。所以如此,估计是希望车子走的慢一些,让天下黎民百姓一睹大孝子风采,大张旗鼓的宣传孝悌有助于治道,倘若乘了马车一溜烟进了京城,岂非衣锦夜行?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在关中一度吃土流离失所。手下赵岐主动要求前往荆州,游说刘表前来勤王,他惟一的附加条件就是要借用汉献帝御驾“牛车”一用。搞得曹操亲自迎接汉献帝都许时,狼狈不堪的汉献帝居然连个专车也没有。
曹操节约闹戈民,带头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于是乎节俭成了手下文武清廉与否的重要标准。时间一久,大家也就习惯成自然,因此东汉末年出行乘牛车获得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尊重。
至西晋初年,乘牛车已经蔚为风尚,牛的身价直线飙升,养牛业成了最赚钱的生意。家中有名牛、猛牛是贵族王公豪华富有的标志,就连名士也不能免俗,茶余饭后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吹牛皮,且美其名曰“玄谈”。

书归正传,辛弃疾在朝堂上不受待见,而他又时时刻刻想着北伐中原,这首《破阵子》可以视为他的请战血书。“八百里分麾下炙”,说的是在“沙场秋点兵”的时候,即使是再名贵的牛他也得杀了,与手下将士一起来撸串。凡历史上举大事者,无一不要歃血为盟,每到这个时候,第一个倒霉的往往是牛。杀牛,代表了举大事人义无反顾的信心。为了鼓舞人心,这会儿的音乐最好是“塞外声”,有杀伐之气才合时宜。
辛弃疾不愿意作权贵豢养的“八百里”,“八百里”再牛皮,也只是一头牛,他希望自己是一匹可以驰骋沙场的“的卢马”。理解了“马作的卢飞快”,可以更好的理解辛弃疾悲愤填膺的心情。
众所周知,的卢马的主人是刘备,的卢马除了跑得飞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妨主,谁骑谁倒大霉。即便如此,辛弃疾仍不以为然,妨主就妨主好了,他要的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只可惜空有满腹经纶、一腔热血,而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白发生”,人生理想也没有实现,只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自我安慰一途了。
人生的悲哀,莫过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