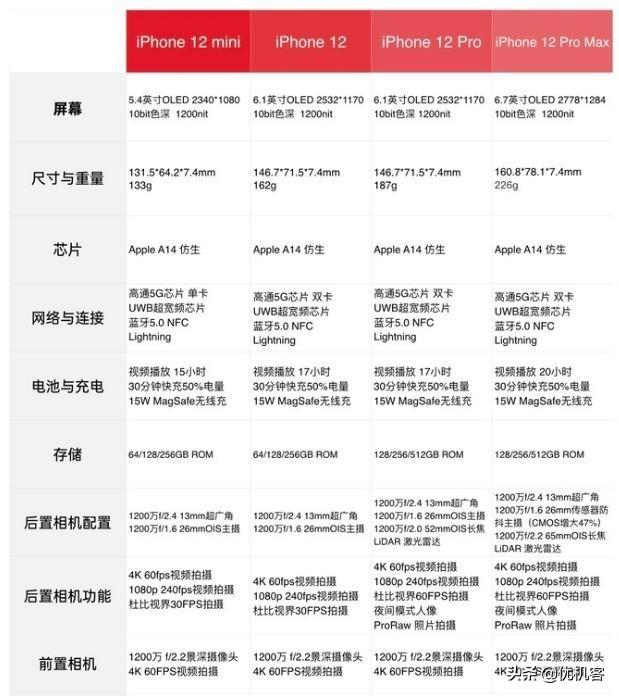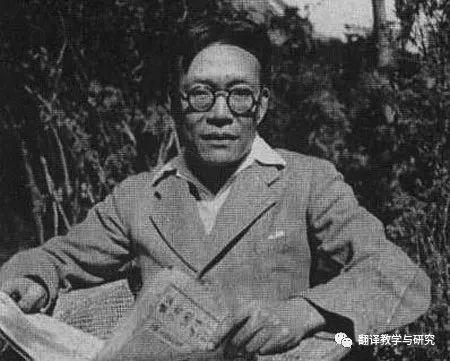
摘 要:金岳霖的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翻译要意味并进,“翻译”需要哲学。而他的翻译哲学思想主要包括:翻译的方法是非唯主,翻译的本质是官能对外物(语言和文化)的非唯主呈现,翻译的过程是语言间的实证与分析。
关键词:金岳霖,翻译思想,翻译哲学思想, 《知识论》。
一、翻译与翻译哲学
关于“翻译”的定义,一直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不同的翻译家都有对“翻译”定义或内涵的不同理解与把握,这是由翻译的复杂性与外物性所决定的。尽管翻译理论中有很多关于翻译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大多是语言学及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从文化、语言翻译角度去理解的,较少看到从哲学的角度去把握,也较少看到哲学工作者(尤其是哲学家们)考虑这个问题。贺麟先生很早就给“翻译”下了明确定义,他:“从哲学上讲,所谓翻译又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乃是译者( interpreter )与原本( text )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 communication ),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 translation ),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
“翻译”概念事实上是包含三个外延,一是通常所说的不同语言间所进行的语言翻译行为、过程或结果;二是同一语言内,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所造成的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与符号之间的转译和理解;三是同一语言内的不同语言符号单位之间的解释与沟通。同时,这三种翻译还有人为的和机器的区别,不过我们认为一切诸如以电脑为手段的机器翻译都最
终是受人的操纵的,因此我们撇开机器翻译而只管人为的翻译了。
第一种“翻译”可以称之为“语言翻译”( translation ),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翻译”,通常我们所说的“翻译”也就指这种“翻译”。第二种“翻译”可称之为“释义翻译”,简称“释义”( comprehension ),第三种“翻译”可称之为“注释翻译”,简称“注释”( annotation n)。“语言翻译”比较于“释义”与“注释”,对人、对物(包括对语言)的要求要高得多,“释义”与“注释”只是“语言翻译”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一个层次,解决了“翻译”的问题,“释义”与“注释”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因此,我们所谓的“翻译”通常就只是指“语言翻译”。
“什么是翻译哲学”( Translation Philosophy )?翻译哲学实则应是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范畴,它是翻译的过程(步骤)、技巧(技术)、方法、方式(模式)、环节(层次)、原理(原则)、价值、本质、心理、道德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所谓一般性的总的看法。它离不开人们的抽象与概括,总是人们对翻译实践的具体分析的结果。离开人对翻译的分析无所谓对翻译的一般的总的看法,一切翻译理论与翻译观点,都以对翻译进行分析作为原初的动力。同时,所谓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翻译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体指导于翻译本身,而往往是那些就事论事的翻译观点却总是对类似的事(翻译)奏效的。因此,翻译哲学是一个非本体论体系,它在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它应该被定义为:关于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精深分析及其总的一般的看法。这表明,翻译哲学有两个层次的研究对象,一是翻译,二是翻译理论。前者是翻译哲学的直接对象,形成对翻译的直观的实证的哲学认识(分析),后者是翻译哲学的间接对象,形成对翻译的总体的理论性的哲学认识(分析)。我们也不完全排除对翻译及其理论形成一些总的一般的看法即翻译观,我们只是说总体的、一般的翻译观或者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翻译观不仅仅才是翻译哲学所要得出的结果。而其它的东西(对翻译和翻译理论精深的分析)也是翻译哲学所结出的“果实”,而且,我们认为结出这样的“果实”更为重要更为必要,是翻译哲学的首要任务。另外,翻译哲学不应是呆板的对其研究对象的静态描述,而更应是对其研究对象的动态分析。对于直接对象(翻译)而言更应是动态分析,对于间接对象(翻译理论)或许静态描述(分析)的成份要多一些。当然,翻译哲学的主体手段是静态描述与动态分析的结合。由此,翻译哲学不是简单的“翻译加上哲学”,诚然翻译活动需要哲学思考,翻译实践、翻译研究需要哲学指导,翻译教学需要哲学为方法为工具,但这都不能叫做“翻译哲学”,因为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究其本质只是思考者操持某种哲学理论去评价翻译及其理论而已。例如,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翻译的过程、功能与本质等,固然这些内容或许可以发展升华为翻译哲学的内容,但这不可能成为主要内容,翻译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于就事论事,在于对翻译、对翻译理论作实证的直观分析。
二、金岳霖的翻译思想
我们曾经以金先生所著《知识论》使用或引用英文为例,从中得出金先生的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翻译要意味并进
语言翻译应该意味并进,即使不能完全译出“味”来,译出部分的“味”也是必要的。他所讲的“味”就是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思想及情感,这样的情感通过元语言的转换或诠释,使掌握元语言的人能心领神会。但事实上,这并不容易做到,金先生在《知识论》通过中英文对译的大量事例对此作了阐述。例如,( 1 )中国人心目中的“麒麟”,其意念与非洲的动物“ giraffe ”所表示的含义大不相同,尽管这二者在英汉互译时成对等词,但把“麒麟”译成“ giraffe ”其“味”未能完全溢发( 386 — 387 ,指《知识论》一书中第 386 — 387 页,下同);( 2 )“ I love you ”与“我爱你”在其各用寄托的情感上,也不完全相等( 827 );( 3 )“英国人看见 rose 和中国人看见玫瑰大不相同”,把中国的“玫瑰”译为英国的“ rose ”,也不尽准确,中国人的“玫瑰”蕴涵丰富情感及思想,并非“ rose ”能传达的( 282 );( 4 )有些“在意义上相当的字不能引起相当的意味”,“大江东去”中的“大江”虽然可以译成“ big river ”或“ great river ”,但“大江”所寄托的情感却难让英美人去感受到。中文的“子曰”与英文“ and The lord said ”也有类似的道理( 281 — 283 )。当然,君、皇帝、太太、哥哥与 rule 、 emperor 、 wife 、 elder brother 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283 )。语言是各种情感的寄托,这使得两种语言的对译,译意容易,译味难。译意只需另一种表达,译味则需要“化”;( 5 )对于文字本身,持不同的母语的人也有不同的情感,“中国人对于‘父子'两字所有的情感,决不是英美人对于‘ father and son '这几个字所有的”,反过来,英语中的 Father 和 Son 所蕴涵的宗教意义也是汉语‘父子'所没有的( 800 );( 6 )中国人已无“君”,英国人还有“ king ”,美国人从来没有。到中国来留学的英美学生即使认得汉语词“耶稣圣诞节”,但他们对于“耶稣圣诞节”这几个字和对于“ Christmas ”这个英文词所产生或寄托的情意是大不相同的( 80 );( 7 )至于“道”与“ logos ”( 817 ),兰花的“兰”与 orchid ,“空谷”与“ empty valley ”( 824 ),不论是在文字本身或字型上,还是在文字意义上,前者所寄托的情感的意味深长远非后者所能表达的;( 8 )“句子底综合的意味”更非一般的翻译所能传达的,把“大江流日夜”所引起的“思古幽情”传达于英语中的困难,与把“ That which we call a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既是玫瑰,取与他名亦芳香)这样一句情感丰富的英文译成汉语所遇到的困难,是同一的( 810 )。
金先生认为在意味不可兼得的时候,应偏重于意。众所周知,对于起源与形成过程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而言,完全对等意义(还不包括上文所说情景意义)的字、词、句实在是不多。因此,即使只注重“意”,翻译也不见得很成功。尤其是在金岳霖先生撰写《知识论》的时代,汉语或中文欧化或西化的程度还不高,一些近代专业术语在汉语中或不存在或在社会生活中未被广泛使用。
2. “翻译”需要哲学
为什么《知识论》要直接使用或引用很多英文语词或句子,除了语言翻译方面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金先生对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哲学认识,就在于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就在于他主张心物并重又着重于物的新实证主义观,就在于他基于哲学来理解翻译。
《知识论》的英文使用是金先生表达思想、阐明哲理的需要。一方面从知识论自身思想角度去着想,既然知识论是以“知识的理”为对象,其目的是求得知识理的通,性的真,借用不同语言能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某一思想或观念;另一方面从哲学的角度去思索,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样型和凭借去展现,而且语言就是思想,就是意义的付与和情感的寄托,要理解某些非母语的词或句,从非唯主的观点去看,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使用这种非母语的语言去理解、去把握、去领会。
金先生在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时候有个突出特点,就是贯穿着反对“唯主方式”的鲜明的立场。他说,“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主要潮流底出发方式——无论只承认此时地官觉内容或同时兼有主观的官觉者——就是本章所说的主观的或一时一地底官觉现象出发方式。我们简单地叫这方式为唯主方式。……这方式有本书所认为是缺点的地方。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非唯主'几个字表示相反的出发方式或相反的思想。”他不主张以“唯主方式”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而需要用“非唯主”的方式为出发点。他以“有外物”为前提,肯定“有独立存在的外物”,反对形形色色用主观去吞并客观的唯主学说。对于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而言,英文是外物,但是存在的;同样,不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汉语是外物,但也是存在的。不论是把英语作元语言去分析、研究中文,还是使用汉语作元语言去剖析研究英语,若都以“唯主方式”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就不可能达到金先生所说的“符合”。金先生的“符合”,其基本精神是:主观的认识必须受客观实在的制约,必须符合客观实在,力求达到“其底客观性、独立性、超越性”( 918 )。金先生在坚持外物独立存在的同时,又主张“所与是客观的呈现”,他称“官觉内容”为“呈现”。他论述道,所与面两方面的位置,它是内容,同时也是对象,对内容而言,它是呈现,就对象而言,它是具有对象性的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内容和对象在正觉底所与上合一”。他进一步说,所与作为内容来说,它是随官能活动而来,随官能活动而去的,就所与是外物说,它是独立于官能活动而存在的。我强调所与的呈现是“客观”的,是同种正常的官觉者都能得到的“类观”。它没有受某某特殊官能个体私给的影响。但不同的官能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于一个外物常常得不到同一的呈现,尽管这样的不同一也是符合自然律的。之所以如此,对于语言翻译这件事,就不易或不能达到“客观的呈现”,如果强加给某些英文以“呈现”,就不见得是“客观”的。“ and The lord said ”对中国人是外物,强加它一个“子曰”,并不是“所与的客观呈现”,“ Free will is the will that will is itself ”对中国人肯定也是外物,如硬塞给它一个“呈现”:自由愿望就是愿望使愿望本身得到自由。这只能是一个盲人摸象般的主观呈现。那么外物是不是不可认识呢 ? 金先生曾坦言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尽管他在书中倡导的观点或思想实际上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后某些哲学传统的继承,但他的哲学没有为“上帝”的存在留下地盘,他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上帝”的影子。《知识论》中,他承认“外物”是存在的,不过“外物”有“在内”与“在外”之分,并且“内外有别”,“在内”是“自然”的,“在外”是“本然”的,总的来讲,“外物”是可知的。何以能知 ? 他没有继续阐述。根据他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追求“何以能知”的本身就是“何以能知”,“何以能知”是一个川流不息的过程,这过程就达到了“何以能知”;同时,要对外物有所知,去知其外物的过程和结论本身就都是对外物的知。要官能并领会英文“ and The lord said ”,不仅所求得的“客观呈现”是知,而且何以能知其“客观呈现”也是知,二者的结合就是“何以能知”。
三、金岳霖的翻译哲学思想
1. 翻译的方法论:翻译的方法是非唯主的。
2.
作为语言的词与句,既是意义的再现(体载),亦是“情感上的寄托”。即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如果翻译从唯主的方式出发,注定是要失败的,即是说站在自己的语言(母语)的角度,站在自己固有的思想的立场上去翻译另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必定不能成功。如英文“ That which we call a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一句,如果单以汉语去思索这句英文是不能领会此句英文所表达的丰富内涵与情感的,要深刻领会此句英文,只有跳出自己唯主的框框,从英语言的情感和观念去揣测和把握。他又指出:如果站在非唯主的知识论立场上,对象语言就是外物,外物虽可以认识,但外物是客观的呈现,“要使认识(主观)与客观结合,是不容易的,因此散文(包括小说)翻译有相当困难,哲学上的东西更不易翻译,至于诗差不多不能翻译。”一种语言的词与句是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不同时空无数个体的思想的付与和情感的寄托,要使两种语言的思想和情感得以相互对应和相互沟通,金先生认为:必须以思想去思想(翻译),以思想作为翻译的前提。这里所谓的思想是指独立于翻译者之外的为翻译者所官觉(知觉)的对象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不是翻译者唯主的思想。总而言之,金岳霖先生倡导的翻译观就是:从非唯主的方式出发,站在对象语言的思想立场上去翻译对象语言,力求达到“意味兼得”。
2. 翻译的本质论:官能对外物(语言和文化)的非唯主呈现
金先生所谓的外物,就是非唯主的共同的、独立存在的、有本来的形色状态的、各有其同一性的客观参与。也就是说,外物必有以下四个特征才成其为金先生所要求的外物:( 1 )外物必须是非唯主的、共同的东西。只有非唯主的共同的东西才是“公”的东西( 62 );( 2 )外物是独立存在的而不依靠观察者的官觉而存在的;( 3 )外物有它的形色状态,而它底形色状态是本来有的,不是官觉者所赋予的( 63 — 64 );( 4 ) 每一 个 外物都各有其在时间底绵延上的同一性 ( 64)。外物无论如何地变 , 一件东西是该件东西的时候 , 成其为 一 件东西 。一 个 外物之所以成其为这一 个 外物 , 而不是成其为那一 个 外物 , 就在于这一件东西、这一 个 外物有区别于其它任一件东西 、 任一 个 外 物的特殊属性或保持同一的性质 。同时 , 在金先生看来 , 外物总是相对于官能的 。相对 于官觉者的 “官 能活动不必有外在关系 , 但是有外在的关系 ”( 159 ), 这样的 “ 外在的关系 ” 就是 “ 客观的呈现 ”。
金先生 尽管没有给出 “ 翻译 ” 的直接语句定义 , 但 从《知识论》中对“ 翻译 ”的理解看,金先生的“翻译”包含以下内涵 :翻译 不仅 是不同语言间的文字意义转换 , 而 且还有语言情感的转换 ;翻译是力求意味兼得的语言逻辑分析的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相互综合的活动 , 在意味不兼得时应偏重于义 ;翻译活动只局限于一部分语言文字的转换 ( translating) 领域。事实上,金先生 的观点也可理解为:翻译是外物与译者之间所进行的、非唯主的沟通,即,翻译是外物(语言和文化)参与其间的译者非唯主的活动。
根据金先生的思想,可以从哲学角度的给“翻译”这样的定义:翻译是译者与对象符合(对象语言)之间所作的元符号(元语言)释文( comprehension )、注释( annotation )、解读( explanation )和领会( understanding ),是心物交织的客观活动。由此,翻译不是仅仅局限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行为;语言对于译者都有外物与主体(译者思想与心灵)沟通的成份,母语对于译者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把握与理解,母语中许多东西或成份也是译者未必知晓的,相对于译者是外物,至于外语相对于译者的外物成份那更多了;翻译当然不仅仅是将非母语翻译解释为母语,在本质上是将一种符号理解、改变为另一种符号,因此是对象符号(被翻译的符号)与元符号(用于翻译的符号即工具符号)之间活动;翻译涉及“外物”,尽管也有主体(心智与思想)的参与,有时也有直觉、顿悟与灵感,但总不可能随意的杜撰与臆想,是非要考虑对象符号的一切社会、文化、学科等内涵的,因此翻译不可能完全是主观活动,本质上是客观的活动;翻译又非要译者的心灵与智慧参与不可的,翻译是带有较浓主观性的活动。
3.翻译的过程论:语言间的实证与分析
金先生在谈论翻译时 , 突出 地认为:语言文字是外物 , 翻译是外物间的实 证 与分析 , 外物非参 与语言活动 ( 包括翻译活动 ) 不可。
在金先生看来 , 语言文字必然有以下特性 :( 1) 语言是交通工具 。“ 语言本来是有交 通性的 , 不然不成其为语言 ”( 222)。“ 交通是可以办到的 ” ( 222),但 也必须 承认 有 不能交通的情感或思想。( 2) 语言文字是 “ 社会的收容与应付工具 ”( 225)。语言文字的约定俗成性即决定了语言文字的社会性 ,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 , 以语言文字去弥补记忆的不足决定了语言文字必然是人的思想与情感的收容与应付工具 。( 3) 语言文字是客观的所与 ( 外物 )、 也是 “ 官觉底所与 ” ( 223)。语言文字是客观的所与与官觉中的呈现的结合 , 客观的所与与官觉中的呈现是语言文字成其为语言文字的必要条件 ;官觉中的呈现必然以官觉所与为前提 , 而官觉所与 反过来又必然涉及语言文字的样式与凭借 。( 4)语言的外物性。对于 语言文字 自身而言,也被 寄托 了 社会、文化、民族 等的情感因素 ,这些因素可能以不容易察觉的形式附加在语言文字上。
由于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有金先生所认为的以上四大特性,决定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必然有以下特性:( 1 )翻译首先要注重原作义理的了解、意义的把握。“意一言多、意是根本”是翻译的哲学基础。( 2 )翻译有“译意”和“译味”之区别,“翻译”的完美价值在于意味兼得,即完整地转达原作的意义与被寄托的情感等因素。“译意只要求达求信”、“译味也有达也有信的问题”( 813 )。前者只是一种技术困难,总可以实现,而后者“不但是意义而且是意味”,“译味也许要重新创作”( 813 )。因此,译味不一定能实现。( 3 )语言文字是客观所与、是外物,又是官觉者的所与和官觉的呈现,这决定了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文字 (不同外物)间的转换或交通,同时翻译又是非要官觉者参与不可的,所以翻译又是与官觉者的所与和官觉的呈现极为关联的,翻译(除了“命题”的翻译)或多或少都有创造或创新的成份,所谓的“直译”是不可取的( 827 )。( 4 )翻译的必要条件是“正觉底所与”( 812 ), 客观的官觉是掌握语言文字的必要条件,翻译过程的最初是要得到文字的意义,文字的意义“总是要从正觉方面所得共同的所与(引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们底共同的所与)才能得到。两种不同语言文字中的字底相等,最初总不是由语言文字看出来的,而是他们同样地指示某种官觉呈现。这种官觉呈现与语言文字的及语言文字被寄托的客观所与紧密相关。
参考文献
1. 金岳霖 . 知识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
2. 贺麟 . 论翻译 [J] ,今日评论, 1940 ( 4 )(贺麟,论翻译 [C] ,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 ) [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3. 刘邦凡,杨炳钧 . 论《知识论》的英文用语及翻译哲学思想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哲社版 ), 1998 ( 6 ) 14-19 。
作者简介:刘邦凡( 1967 —),重庆涪陵人,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逻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