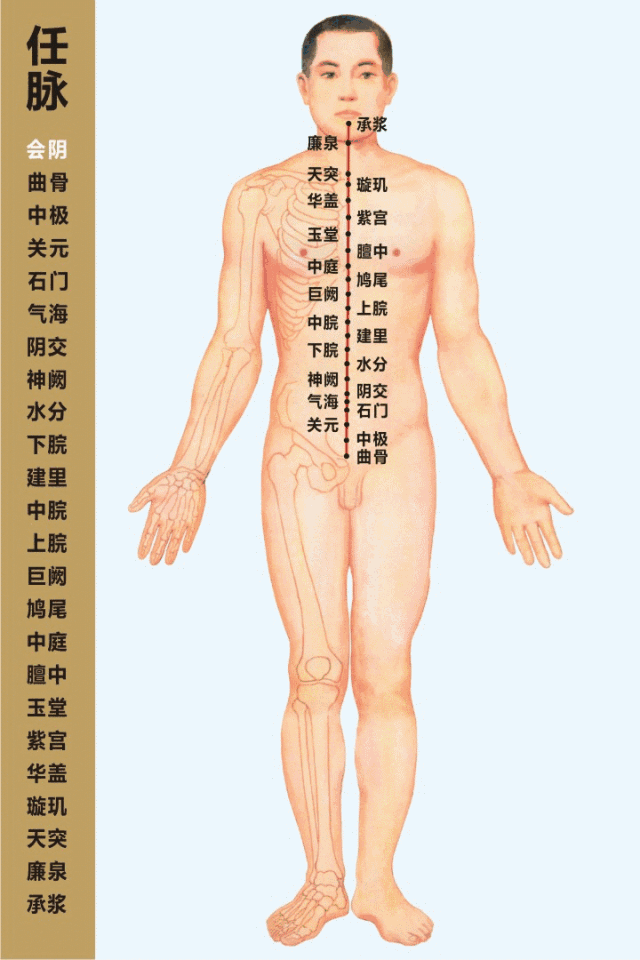文/徐志达
插图/杜卉

【编者按】
语言本身是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惠州话,堪称鹅城惠州别样的文化景观——古典雅致、韵味悠长的 “语言景观”。
惠州“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文化强市,丰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涵。探寻惠州历史文化脉络,从惠州话入手,或许能另辟蹊径。专家认为,客观地弄清惠州话的语系归属,认同并重视本土文化,这对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惠州城内多细女,朝朝担水到西湖,正放下桶梁洗净脚咧,又问明朝割草无?” 每当默读这首古老的惠州民谣时,心中就会涌出许多唐人的诗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朝省入频闲日少,可能同作旧游无?”(张籍)、“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两者一野一文且时空相隔久远,然其韵味却是极为相近,特别是“又问明朝割草无” 一句 ,既浅白如话又古典雅致,宛如一道美妙的“语言景观”。
为何惠州话中的许多口头俗语透出一种古汉语的文言韵味?其属独立方言还是应该归属何语系?这些问题颇为学术而又饶有趣味,本文试作探讨。

【壹】 地域文化色彩鲜明
惠州话,指现今惠州桥西(古称惠州府城,亦称鹅城或鹅岭镇)、桥东(古称归善县城,亦称东平或鹤峰镇)及其近郊原居民所讲的本地方言(俗称本地话)。
惠州话不但古雅,而且兼收并蓄,以开篇的那首惠州民谣为例:“惠州城内多细女,朝朝担水到西湖,正放下桶梁洗净脚咧,又问明朝割草无?”(“细女”即少女;“朝”即早上,“朝朝”指天天早上;“担水”即挑水;“无”,用在句末表示疑问,相当于吗或否)。类似的民谣还有不少,例如:“白鸽公,白鸽乸,飞落墙头担草芽。担了草芽立立转,大姐爱嫁刘知县,老妹爱嫁李探花。两度衙门相对面,麒麟狮鼓插金花。”(“担”即衔,用嘴咬着;“立立转”即打圈转;“老妹”即妹妹;“度”即间)“稔哩目目娘撒谷,稔哩开花娘莳田,稔哩好食禾好割,让得有闲到姐边。”(“稔”即山稔树的果实;“哩”助语词,无义;“目目”即胀卜卜状;“让得”即怎能够;“姐”即妈妈)
这些民谣唱出惠州世态风情,表现手法也不俗。如《稔哩歌》将稻谷播种、插秧、收割等劳作情形与山稔的物候现象以及感人的亲情相结合,朴素动人,教化儿童,可谓完美。闻说已故省文史馆馆员吴仕端先生曾称其可入《诗经》,所言不无道理。
从这些民谣可以看到,惠州话除有其独自的词汇外,还含有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和客方言(以梅县客家话为代表)的诸多特点,其遣词造句与粤、客方言有颇相类似的地方,但语感腔调却迥异。讲惠州话的本地居民,无论男女老少,多能以广州话或客家话交谈,而且字正腔圆。究其原因,应该与惠州话的语音、词汇等含有粤方言和客方言的元素有关。正因为惠州话存在这种现象,长期以来,学界将其视为客家话的变异,或为深受客家话影响的粤方言等,可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惠州话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在广东方言中,客方言最接近中原古汉语,几乎可以与中原汉人通话交流。然而惠州话却是让岭北人难以听懂的“鴃舌啅噪”之声。唐代诗人刘长卿以诗《送韦赞使岭南》赠好友出使岭南番禺,诗中有“岁贡随重译”句,可见那时的岭北人与岭南广府人公差交往,是需要译员随行的。苏过在惠州时亦曾诉说“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感叹惠州话像鸟语般,不便交流。想必当年,豁达、洒脱的苏东坡寓居惠州期间该是操着“唔咸唔淡”的本地腔,比划着手势,“笑口吟吟”地向桥东白鹤峰的林婆婆赊酒饮吧。
惠州话存在纯属自己的口头语言,例如:“那里”说“盖哒”或“盖邓”;“这样”说“拱”或“拱样”;“害怕”说“恇”;“疼爱”说“切”;“挂”说“刻”;“把玩、摆弄”说“捺”;蜂、蚊等叮蜇说“针”;“肮脏”说“泥”;表示批、群、帮等量词用“纲”;有表示完成体的体态词“抛”,如吃完了说“食抛”;变高声调说我、你、他,表示这三种人称的复数等。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贰】深受古代岭北人的语言影响
惠州话究竟是独立的方言,还是归属何种语系?学界对惠州话的系属争议从未停息,争论点归纳起来主要为:属粤方言说;属客方言说;客、粵语混合方言(俗称客白话)说;与汉语七大方言平行的独立方言说等。
探讨惠州话系属问题,需正确判明东江中上游本地话土语群的基本源头、历史背景、文化渊源。从广东各地和惠州博罗春秋战国墓考古出土的钟、鼎、盉、戈、矛、剑等铜器以及连平忠信出土的虎纽于(古代一种铜制乐器)等物品中可以看出,那个时期东江中上游流域如同岭南大部分地区一样,深受楚文化的影响。
从地理位置,抑或历史背景来看,惠州都与珠江三角洲区域有着紧密的关联,而珠江水系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鼻祖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故惠州诸邑皆立于南支万山之中,其水西流入广城以出,则惠真广郡也。”可见惠州与珠江水系及广州的关系。

那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已是岭南开发的先进区域,因此成为岭北移民的首选之地,致使人口增长过快,再加上当时珠江三角洲部分地方还受到“海涨咸潮”的影响,遂使部分岭北移民沿着人烟稀少、荒地较多的东江干流及其支流溯江而上,向东江中上游流域迁移,寻找新的家园,并与当地原土著或早先迁居于此的岭北移民的后裔,即新的移民土著交错杂居,相互融合,繁衍生息。故此东江中上游流域本地话与粤语方言相近,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各个朝代,岭北入粤移民浪潮从未休止。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广东区域相继形成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板块及方言。而今广东这三种主流方言,以及那些变异了的亚方言,都应与古代岭北人的语言有着亲缘关系。
由于历史时空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又显示出其特殊性与差异性。惠州话日常口语中有不少基本词汇与广州话是相似或近似的,虽发音有变异,但其用字组词和表达的意思几乎一致。这是因为两地的方言中仍有不少古越语和古楚语的遗留。例如:睇(观看之意)、畀(给、让之意)、翼(指翅膀)、妗(指舅母)、老母(指年老或年轻的母亲)、今朝(指早上)等等,不可胜数。
在广州话与惠州话的口语中,有不少基本用字和词汇让说官话方言的人觉得古雅,而且颇具“文言味”,显然,这类方言词是从古远的楚秦汉时期保留下来的。(参看刘叔新《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方言还保留古越语和楚方言的成分,恐怕还吸收某些阿拉伯、印度等外国语因素”。(见载袁家骅主编《汉语方言概要》)由于惠州话受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其语音基调元素和词汇底层成分有可能保留得更“原汁原味”,古风犹存。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惠州话也受到客家话影响,同样含有不少客家话的词汇、语音等元素。语言学家指出,汉语方言之间都存在着古代词语的共同传承与词语相互影响、搬借以及存在着受近现代普通话词语等因素影响的复杂现象,广东三大方言及其衍生的亚方言如是,惠州话也不例外。因此,只要把这些潜藏着的、大量的同异事实发掘出来,进行考察、梳理、排查,寻找出其历史源头,惠州话归属何系必能理出个头绪来。
【叁】学界对惠州话的系属争论从未停息
学界对包括惠州话在内的东江中上游本地话归属尚未定论,然而,老百姓对自己讲的是什么话却了然于心。如果询问籍贯是东江中上游区域的朋友属何方人氏?但凡母语是使用本地土语的,其必定强调回答,自己是说本地话的本地人,就连土客杂居地的客家人亦认为如此。正如清嘉庆年间进士、和平客家人徐旭曾《丰湖杂记》中所说:“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其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正如各地客家人都有“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祖训,讲本地话的亦然,生活在东江中上游流域使用本地话的居民,都认为自己说的是和客家话不一样的方言,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祖传话——本地话。
近二十多年来,关于惠州话的归属问题,学术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现象。例如:何志成在《失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缚娄古国 》一文中指出,惠州方言是缚娄古国的“国语”。这一推断虽然还有待于专家学者去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具体论证,但这种开创性的思考和开放的学术态度,无疑值得赞赏;而包国滔从历史的维度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包括今惠州市区在内的东江中上游以本地话为母语的人群的祖先,应当是早在明中后期客家移民浪潮到来前已世居当地的原住民,故而本地话的底层应为粤方言。”(见载包国滔《东江中上游本地话方言系属的历史考察》)在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刘叔新带领学术团队经历近十年对东江中上游本地话群考察研究,最终论定:东江中上游本地话群各成员的语音系统彼此相似,语音向粤语倾斜;本地话群语法特点与粤语白话基本一致;本地话群各成员的基本词汇大同小异,词语量也彼此接近;相当多一部分特殊基本词语同粤语一致或相当近似;本地话群中以“最有威望的惠州话为代表”包括惠州话在内东江中上游本地话群实为粤方言一支系,东江中上游本地话是客家族群迁入粤东和粤中之前的本土语言。
刘叔新的研究认为,惠州本地话与客家话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如同汉语几大方言之间的关系。刘叔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惠州话的历史面貌,其论证惠州话系属为粤方言惠(州)河(源)系(参看刘叔新《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此说在学术界引起重视,获得不少学者的赞成支持。而以刘若云、傅雨贤二位教授为代表的惠州话属客方言说,同样根据惠州话语音、语法、词汇方面与客家话相同,而认定惠州话属客方言。黄淑娉认为:“两说都各自根据部分事实,也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都无法说服对方。”
针对这种学术现象,窃以为,应该把学术的视野更拓宽一些,把研究的范畴外延至与方言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包括历史、文化、社会、民俗等。客观地弄清惠州话的语系归属,认同并重视本土文化,于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脉记忆】
演绎歌曲 音律独特
文/苗理洁
外省人来到惠州,常惊讶惠州话的别具特色。的确,惠州话与普通话所要表达的感情色彩截然不同。如叫太阳“日头”、叫月亮“月光”、叫闪电“火蛇”、叫婴儿“伢仔”、叫筷子“箸”、叫儿媳妇“心布”等等,惠州人用独特的语言表达多姿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惠州话演绎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惠州人称之“古仔”。用惠州话演绎的“古仔”出神入化,别有韵味。清末至民国,惠州城有种戏曲叫木鱼书说唱。说唱者多为本地妇女,主要用惠州话说唱,其实就是从“讲古仔”,变成敲着木鱼“唱古仔”。当年,有木鱼书唱的一出“古仔”叫《金叶菊》,说的是女青年遭受封建家长的虐待和摧残,日子过得非常痛苦。因为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和黑暗,《金叶菊》受到惠州百姓的热捧。至今老辈人说起当年惠州人看《金叶菊》,“十人看,九人哭”。
据地方志记载的惠州山歌、民谣、童谣以及西湖棹歌异彩纷呈,有上千首之余。惠州人用惠州话唱出其独特的音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劳动人民在这方土地辛勤劳动和繁衍生息的切身感受。如惠州人代代传唱的童谣,是惠州历史文化宝库中一朵奇葩。童谣中颇有趣味的摇篮曲,押韵顺口,音调悠扬。其中一首“嗳嘞嗳”,言简意赅,唱来缱绻缠绵:嗳嘞嗳,嗳我亚咕(惠州人叫小婴儿咕咕仔)乖乖瞓哩(瞓:睡觉),亚妈带咕瞓觉觉哩,嗳嘞嗳,我咕一觉瞓到大天光(天亮)哩!宝宝在母亲温柔的催眠歌谣中幸福地入眠。惠州的爱情山歌,更是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如《岭冈顶上种布惊》:岭冈顶上种布惊(岭冈,山上的意思,布惊是贴地而生的蒲松),唔使(不用)淋水(浇水)也晓生,亚哥亚妹情义重,无使(不用)媒人也晓成。在男女婚姻不能自己做主的封建社会,这首《岭冈顶上种布惊》,不仅表现的是男女青年相互鼓励,准备勇敢冲破封建婚姻桎梏,也是男子对女子大胆直白地表示爱慕之情。

曾几何时,东江边和西湖畔的男女对歌,“万众雀跃,欢呼声不绝于耳”。男女歌手一唱一和,情绪激昂高涨,人们将之称为“山歌擂台”。山歌擂台,是惠州话在语言表达上的完美体现,在历史档案中记下浪漫的一页。
惠州话是惠州人的重要符号。无论走到哪,乡音萦绕心头不会忘却,自然而然融入惠州人生命的血脉中。
【文脉调查】
讲好惠州话从学唱童谣开始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
“查莲子,子连牵,查到观音脚面前……”这首《查莲子》,惠州人再熟悉不过。它是每个老惠州人的童年记忆。随着惠州本土方言的逐渐流失,以及娱乐方式多样化的冲击,这些耳熟能详的童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相关专家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大工作力度,更好地保护传承童谣。
惠州市民协副主席刘汉新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童谣,社会各方力量积极行动。2019年年底,由惠州市文联和惠州市教育局主办、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了“惠州市童谣表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896位参赛者,以朗诵、歌舞、游戏以及工艺美术等形式诠释童谣内容,这也是惠州首次以多种艺术形式表现惠州新老童谣。除此之外,近几年来,惠州市民协更是积极整理创新童谣,多平台推介传播了数百首童谣,引发社会关注。

童谣的传唱跟惠州话的继承有着紧密的联系。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表示,童谣是惠州话传承的载体之一,童谣朗朗上口,有旋律,容易学。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持续推出系统化的活动,让孩子们发现童谣的乐趣和惠州话的韵味,“不仅能够唱好童谣,还能讲好惠州话”。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朱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