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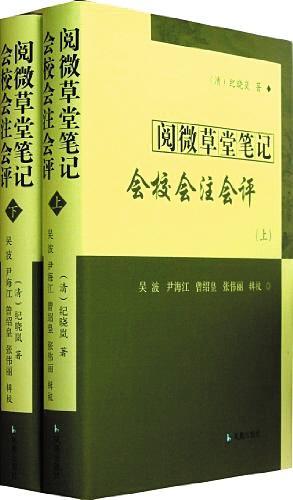


夏天是读书的好时节。
这是句正确的废话。对爱读书的人来说,一年四季都是读书的好时节。而对拿起书本就昏昏欲睡的人来说,夏天处处都是读书的阻碍。尤其入伏之后,灼热的烈日蒸腾着水汽,空气成了一面扭曲的透镜,无形的火焰炙烤着建筑和马路,就像颜料融化的油画,给人一种出离真实的焦躁。
身体和感知也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明明被潮气包裹,体内郁积的燥热无法释放,但每一个毛孔却又争先恐后地向外排出黏稠的体液,在毒辣的阳光下,像开了瓶的伏特加一样迅速挥发,只留下磨人皮肤的粗糙盐粒,一面毛孔不断由内向外释放蒸发,一面汗浆又把肉体包裹得严严实实。释放与郁积之间,就像一个失去了气阀的高压锅,似乎总有个声音想撕破这身黏糊糊的外壳,从里面直冲出来:
“好热啊!”
夏日读书的目的,正是安抚那颗郁积焦躁与烦闷的心灵。或是将它泡在浮着冰块的清冽甘泉中,让那被烈日炙烤得沸腾的血液恢复平静,用一颗冷静的心去窥破被骄阳热浪扭曲的真实世界。或是点燃一把真正欢快的火焰,像烟花一样绚烂而彻底的盛放。
因此,我们选择了《阅微草堂笔记》《那年夏天》和《权力与荣耀》三本书作为夏日开卷的不完全的代表。它们貌似互不相关,但内在却含有默契。它们都是因夏天诞生的书。《阅微草堂笔记》来源于清代文士纪昀在漫长夏日的构思,它所代表的东方志怪传统,正是用尚奇好怪之心带来的丝丝寒意解暑纳凉。《权力与荣耀》则是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对炎炎酷暑支配下的大地的思考,一如那些以夏日为题的文学作品试图捕获这个季节的精髓。《那年夏天:美国1927》顾名思义,这是对历史上一个重要夏天的回顾,在这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改变了这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命运。从内在的心灵,到外在的观察;从现实的大地,到历史的回顾,以这三本书为起点,循着它们提供的线索搜寻阅读,你将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夏天。
《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上下)》
作者:纪晓岚
校注:吴波、尹海江、曾绍皇、张伟丽
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纪昀不喜欢夏天。夏天对胖子着实太不友好,所谓“六月火云蒸肉山”,而他偏偏就是个胖子。“夏日汗流浃背,衣尽湿”。哪怕是入禁中南书房轮值,也要想方设法脱衣纳凉,赤着双臂晃着肚腩求一凉爽痛快。由此可以想见,乾隆五十四年那个炎炎夏日,他在承德行宫一面光着膀子编排校理秘籍,一面慨叹昼长无事。于是便在这个夏天写成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第一卷《滦阳消夏录》。
“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纪昀在序言中对自己著书缘由轻描淡写,但却在这个昼长夏日创作了一部足以与《聊斋志异》比肩的志怪笔记。纪昀尽管学识广博,但他恐怕并不知道,与他隔海相望的日本,此时正盛行一种夏夜围坐一起讲述诡怪故事的“百物语”游戏。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时代,闷热夏夜讲上几则令人寒毛耸立的恐怖故事,既能勾起人的好奇心打发不眠苦夏,又能借胆寒以祛暑,一举两得。
但纪昀笔下的志怪故事,却与日本的怪谈迥然有别,后者一如浮世绘中的“无惨绘”,追求感官上极致的恐怖效果,而在恐惧之外,既没有也无需思考的需要。与这种近乎“为恐怖而恐怖”的怪谈相比,纪昀笔下的志怪故事,却如他在序言中所述,虽无关于著述,但却蕴道德劝惩之意在兹。《谐鬼》中的那位冥吏,就是个讽喻高手。他自称可以看到读书人头顶的灵光,因此从一间破屋中看出了一位“室上光芒高七八尺”的文士。与他同行的那位冬烘学究不禁探问自己读书一生,头顶灵光能有几许。冥吏嗫嚅许久才答道:“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尽管这回答让学究既羞且怒,但读者看来,却忍俊不禁。墨卷策略之类,都是读书人科举晋身必备之资,但在鬼神眼中,却如黑烟一般没有分毫光芒。这则寓言由作为科举考试胜出者本人的纪昀亲笔撰述,揶揄之外,也多了一分自嘲的意味。
劝诫寓言,果报之说,自然在书中占据太半,但一些文辞不长的杂志,虽然未必有警世之意,却也同样令人在齿喉心间徘徊不已。一如书中记录的一则废园廊下的小诗:“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栏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稍解诗意,闭目暗想,不由让人在夏夜中瘆瘆发凉——“墨痕惨淡,殆不类人书”。
《那年夏天:美国1927》
作者:比尔·布莱森
译者:闾佳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那年夏天,股票市场欣欣向荣,电影院里荧幕上的人物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高个子的帅小伙林德伯格驾驶一架怎么看也不靠谱的飞机竟然穿越了大西洋。1927年的夏天,如此绚烂而炽热的盛放,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仲夏夜综合征的幻觉,以为这繁荣盛景会像指针锈住的钟表一样永远地停留在这一刻。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盛放的夏天,不过是一朵夏夜绽开的昙花,随着那些藏在黑暗中的腐烂污垢在阳光下一一暴露,这朵昙花也会随之凋谢。
这本来会是个有些感伤的故事,幸而这本书的作者是比尔·布莱森,一个能把交稿前夜电脑死机苦心数月写完的书稿荡然无存的惨烈悲剧都用笑话讲出来的家伙。因此也让这场末世前的镀金挽歌成了夏天结束前最后的欢乐狂欢。本书的开篇就为全书定好了基调:一场发生在复活节前夜的大火,失火的是纽约当时最高的建筑雪莉荷兰酒店公寓。这场火灾可以说是纽约几年里最大的一场火灾。但布莱森笔锋一转,却从惨烈的火灾现场移到下面看热闹的纽约市民,足足聚集了10万人,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有钱围观者甚至掏钱在街对面订了房间,办起了“火灾派对”。尽管这个开头看似故意吊人胃口的谐趣闲笔,但美国人面对灾难时的幸灾乐祸,却种下了两年后大萧条惨剧的前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灾乐祸正是引祸上身的根源。幸灾乐祸不仅意味着对灾祸持事不关己的冷酷,更有一种乐见灾祸到来的险恶心态。只要灾难能从自己身边擦身而过落到别处,它就是可供欣赏悦目的乐事。事不关己的冷酷和麻木导致灾祸降临时各自保全,不能团结一致抵御灾祸,当每个人都想从灾祸中脱身自保时,抵抗灾祸的力量就会越分散,灾祸就会蔓延更快,波及更大。幸灾乐祸的人就像是与洪水赛跑一样,迟早会被洪水吞没。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在那个夏天,几乎无人看清。陷入繁荣盛景中的美国人甚至对发生在身边的灾难选择性失明,比尔·布莱森在书中讲述了1927年5月18日的巴斯学校爆炸惨案。包括37名儿童在内的44人死亡,是美国历史上针对儿童规模最大、最冷血的屠杀。目击者看到爆炸犯安德鲁·基欧“坐在校门口的汽车里,看到孩子们的尸体被他用残忍手段抛到半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但如布莱森讽刺指出的那样:“转眼之间,外面广阔的世界就忘了它,两天之后,《纽约时报》差不多彻底停止了相关报道”,反而把大篇幅用于追踪林德伯格横跨大西洋的飞行。人们把热情耗在了为英雄的胜利而欢呼上,却漠视身边发生的灾难。
建立在幸灾乐祸的选择性失明和盲目自信之上的繁荣,终究只能是昙花一现,当炽热的夏天结束时,秋风的萧瑟会带走一切虚妄的浮华,就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坍塌。就在举国被繁荣的夏日热昏了头的时候,却有一个人始终保持了清醒,但遗憾的是,尽管他冷静而理性,但他所考虑的,也是急流勇退的自保之策。但这个人恰恰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人,总统柯立芝。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人对记者言简意赅地宣布,他不会参加次年的总统选举。而他的女儿多年后回忆说:“爸爸说,大萧条要来了。”
《权力与荣耀》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译者:傅惟慈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3月版
天气炎热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外,还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做事情的风格,对写作者而言,夏天的炙热甚至会影响到作品的氛围,这或许也是中国古诗中描写夏天的诗词数量远不及秋冬的原因。
在外国文学中,提到炎热难耐的氛围,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下的“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中写下的“那个地方好像搁在炭火上一样热,也仿佛就是地狱的入口”。在仿佛只有夏天的季节中,村庄中的居民在睁不开眼睛的困倦中模糊了梦境与现实。拉丁美洲这片土地似乎正具有这么一种魔力,吸引着作家的文字走向它们的密林。不信的话,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格雷厄姆·格林的大多数小说都是典型的英国风格。但在1938年,格林前往墨西哥待了两个月,其中有五周左右的时间只身一人在墨西哥南部跋涉。他根据这段经历写出了《权力与荣耀》,结果,在墨西哥的环境影响下,如果遮挡住作家的名字,这本小说的语言会让人误以为出自一位拉美作家的手笔——人们在炎热的空气中等待着一次雨季、院落里的人坐在桌子旁吃辣椒、被蒸发的云彩让人觉得前方不存在什么前途之门、只有神父推开小教堂破旧的大门看着鸽子在地上跳来跳去。在谈到这次墨西哥之旅时,格雷厄姆·格林说:“我在墨西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抑郁症,对它产生了一种近似病理性的仇恨。”
作为温带的居民,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被夏季炎热支配的一年,但我们也很幸运,可以体验四个季节形成的不同世界。阅读这本小说或许无助于消暑,不过,它的文字可以将我们引入异域,既然无法改变暑热的到来,那就不如好好地体验它,感受酷暑的沙漠,泥泞的雨林与嚼烟草的神父,同时用身心感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魅力。
撰文/李夏恩 宫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