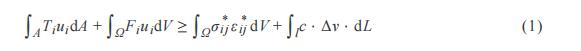最初接触到《万象》是在本地的一间小书店里,那是家很小的旧书店,位于潘家湾收藏市场最后一排的角落,可巧它也叫做“万象书店”。店主小林是会泽人,来昆明经营旧书和旧字画已经很多年了。和店主攀谈起来,他说取这个名字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只是借以显示下自己的图书品种繁多,包罗万象。我常在午后去拜访他的书店,这个时候他一般在忙着收拾整理旧书,把新到的货挑拣一番,按着他的分类排放到书架上。我倚在柜台上翻看他的《万象》,这些封面花花绿绿的杂志被堆在书店的墙角,其中一些已经很旧了,说明它们曾在很多读者的手里传阅过,另一些则干干净净的,倒便宜了我悉数收到我的书架上。
读着《万象》里面的文章我总会有种奇妙的感觉,仿佛在听一些有着不凡经历的人在一起聊天,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我虽然插不进话去,却能尾随他们的思路去作一次次遥远而奇异的旅行,那种旅途中的见闻可以让我回味好一阵子了。听说这个《万象》和民国的《万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说沿用了老名号,也不是说请出了老《万象》主编柯灵来顾问,而是它的创刊思路与老《万象》真的有种前世今生的渊源。老《万象》的首任主编陈蝶衣先生,是位浑身上下都沾染了海派习气的才子,爱写香风氤氲的文字,在旧上海为周旋写歌,后来到了香港为邓丽君填词,搓酥揉红的雅趣始终未变,最后以百岁高寿下世。
无论是老《万象》还是新《万象》,讲述的都是红尘万象的故事。那些文章大多不是道德文章,少的是点刻板和冬烘,多的是点生动和才情,往往是作者的点滴心语,在黄昏自家的院子里以拉家常的方式讲出来,所以读来总是有趣的,决不会让人未尽一篇就哈欠连天。那些文章或诙谐或庄严,甚或带点小小的俏皮和狡黠,无不有作者真性情的流露。也难怪,就凭老《万象》的传统,就凭那种哀而不伤的怀旧情调,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谁还能无动于衷呢?
话说单老《万象》的民国海派风骨就足够吸引人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快一个世纪,但那个如梦如幻的旧上海还是不真实的存在于许多人的心里,而且各人心中对于它的印象都会有所不同,即使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会因 着各自看待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谁跟谁会一样呢?也许旧上海是程小青孙了红笔下鬼魅般的怪异世界,是张爱玲构造出的旗袍面上零落的胭脂香粉,抑或是后半生潦倒的李恩绩寄到柯灵手上的那部《爱俪园梦影录》手稿,也许还是政客黑幕,帮派恩仇,潦倒不遇的文人梦魇。是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影影绰绰的传奇,阴霾里静默矗立着的光怪陆离的城市危楼,一幅幅车轮碾过青石路面渐行渐远的长镜头画面。人们任由着自己的趣味尽情地妆点着那个东方大都市迷雾般的幻境,当这种幻境戛然而止后,一些东西幻灭了,但它终究延伸到了后来的香港,同样的东方明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脱不了与旧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难怪叶灵凤会将下半生托付在了那里。
老《万象》仿佛是一面旧时代的镜子,它会一直在幽暗的角落里诱惑着没有过那种经历的后人,新《万象》试图走同样的道路,虽然它们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些幻影和碎片,虽然那些东西飞在高空,但它们的影子依旧紧贴着地面,它们时不时从窗外掠过,让我们能够激动地窥视到一些不属于我们的秘密。周梦蝶《花心动》短诗中有一阕:那蔷薇/你说/你宁愿它/从来不曾开过。是的,有些意境我们愿它永远珍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