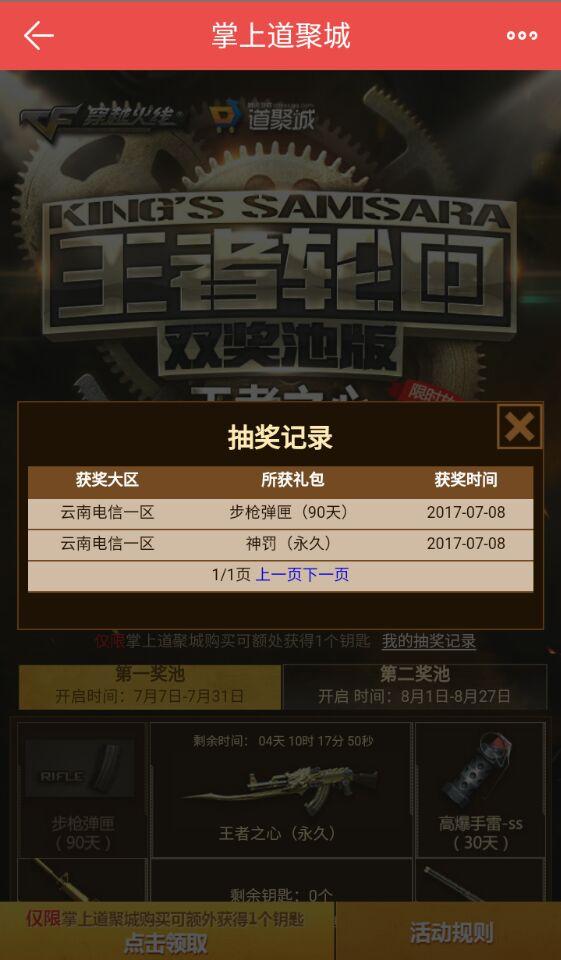释文如下:
雪泥鸿爪 剑生题 (口实口华) 剑生 肖愚 剑生 凤鸣 书剑馆 画痴 西阳山人 肖愚 林凤鸣 书剑馆 笔生花 笔生花 糊涂 笔墨兮一生缘 信手拈来 素位而行 梧林居士 凤鸣 肖愚
西阳山人 愚不可及 一味懒 人福容天地
此三方为家严手刊时民国四年秋月五日 林凤鸣 林氏 肖愚
弟毕业将别无以为赠自思有自刊名印几方然粗劣实属不堪转念同学爱友厌拙竟何妨足下留此纪念而细思余为人可也挺英吾兄惠存愚弟剑生拜赠(剑生)
林风眠的这幅印谱,原来刊于1929年李金发主编的《美育杂志》第三期上,并在印谱上注明:林风眠十年前之图章。确定是林风眠在梅县中学时期的遗物。
这是林风眠非常难得的年轮痕迹,或许是最早的墨迹与印章,从中可以读出林风眠的少年志趣所向、理想情怀与执着精神。虽然青涩犹在,但生气勃勃,大有客家农家子弟的高远心志与坚韧奋发。
林风眠对母亲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不但为其画了不少画,也留下刻骨铭心的文字。至于父亲,除了祖屋门楣上所书“敦裕居”三个大字外,还找不到其余留痕。但在印谱中,意外收获了林风眠父亲林雨农刻的三方印。林风眠毕恭毕敬注明:此三方为家严手刊时民国四年秋月五日。根据时间记载,为一日之内,一气呵成为儿子刻的。在自己赠送师友的印谱中,将父亲的印章置于其中,自然是一种感恩与孝敬。尽管父亲不是什么篆刻大家,但父子之情在,金石长寿,天长地久。这也是这幅印谱的特别之处。三方印为:林凤鸣、林氏与肖愚 。印谱中林风眠自刊的“肖愚”印章就有两方,“肖愚”可能是父亲为林凤呜取的小名或是谦称。从父亲刻的三方印章中,林风眠的篆刻启蒙家学渊源,可见一斑。
林风眠偏爱郑板桥字体的洒脱,摹仿挥毫,笔性神韵,行云流水,不偏不倚。行文落款,彬彬有礼。无须点评朱白刀法,“剑生”“书剑馆”“画痴”“笔生花”“笔墨兮一生缘”“信手拈来”“素位而行”,是理想,是追求,也是座右铭。号为“剑生”,显然是种家国情怀;“书剑馆”,读书报国;落到实处,就是酷爱绘画,“笔墨兮一生缘”。方方印章像是铺向未来的基石,成了林风眠生命的图腾,在印谱中都可以一一得到解读。

林勇军先生提供的林风眠早期的花卉,由于不是十分清晰,难以鉴定。凭笔者直觉,真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妨探讨一下:款为“为屏良友大雅正 西阳山人 林凤鸣笔”。虽与印谱字体不同,但笔致相近;自号西阳山人,应该无疑,印章就有多方;其中钤印会否是印谱中的“书剑馆”?但愿相互是一佐证。林风眠早年墨迹极少,难有参照,片纸只字,都是珍宝。屏良何人,同学或是乡邻?希望还在梅州。
行文至此,搁笔数年,原因是“挺英”为何人,一直无法认定。
推理的讲法是,李金发,别号挺英,自藏的赠品刊于自编的杂志,所以没有注明出处,也有道理。但据李金发在《林风眠与我》中回忆,“他在梅县中学读书,因为图画画得比同学好——不过是摹仿高奇峰式花鸟山水之类——我已久耳大名,我还是读高等小学,还没有资格跟他高攀。”李金发与林风眠二人都是梅县人,都生于1900年11月,日子仅相差一天,李金发是21日,林风眠是22日。李金发读书较晚,1917年初才从梅县高等小学肄业,后往香港皇仁书院读书,所以林风眠在梅州中学与李金发不可能是同学。而梅县高等小学并入梅州中学,那是后话。挺英不可能是李金发,可以断定。


梅州林文铮故居被发现,引来刘奕宏先生述评,文字严谨,考证缜密。其中对《梅县桂里阅书报社书目》作了解读:“1918年的名录里记录的梅州中学学生,除了林风眠(林凤鸣)、林文铮(林铎云)、黄访(黄药眠)外,至少还有李金发的堂侄李挺英(比李金发大三岁左右)”。再据刘先生证实,“挺英应比风眠低一两届,因1919年仍在书报社”。
如此,真相大白,李挺英是林风眠的同校挚友。至于又是李金发的堂侄,作为李金发久耳林风眠大名的媒介自然可能,最终为他们留学时的密切交集作了铺垫,那已是法国的故事。
这幅充满乡土气息的印谱,诞生梅县,情系四方。印谱一般会有多幅,毕业期间,分赠师友,雅趣横生。原件何在?李挺英后人家中,还是早已易手李金发而漂洋过海?其余若干幅印谱,散落乡间,有望再期出现?这也成了地方史学者的新课题。
不管怎样,应该感谢李金发为林风眠印谱留下影印,林风眠纪念馆落成后,可以扩印装裱悬壁展厅,让人瞻仰。这里有着林风眠父子的手泽,少年同学的友情,书香印痕,日月同光。
【文】徐宗帅
【作者】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 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