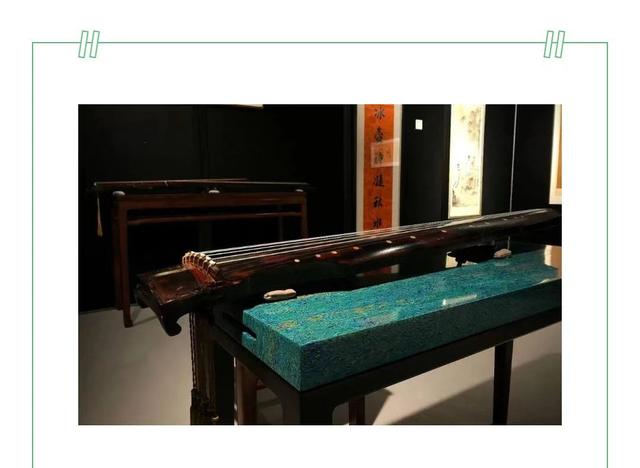上周,天津《今晚报》编辑陈女士约我写水浒专栏,建议我删去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比较分析。我的回答是:开专栏事小,删去我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事大。宁可不开专栏,也要保持学术的完整与纯洁,呵呵。
昨日,3月6日,应人文学院学工办主任张毅哲老师邀请,本人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讲《水浒心学》,受到深职院红学协会会长黄仕巧同学,学生助理苏丽莎等同学的热情接待。互动环节精彩,感受到了90后思想相当开放,看来以后她们才是我的新新红学与水浒心学的受众群,出差在外地的李华基教授看了视频、图片,也如是说。

精选演讲部分如下:
本讲稿以宋江为中心人物,领先使用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着眼历史比较,通过宋江与鲁智深(佛)、晁盖(儒墨,还有林冲)、武松(道)、(卢俊义、朱元璋、张士诚,这三人略讲,或者不讲)等形神比较,挖掘水浒历史取材,探微作者国士情结,触摸水浒主题动脉,以达重读水浒之新境界。
从小说创作角度解密历史宋江如何蝶变小说宋江,正心诚意与您探讨小说宋江是英雄还是奸雄!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中国文化也在革新,明朝长篇小说的出现,是一大亮点,《水浒传》一马当先,横空出世,影响中国500年,并且波及日本、东南亚等国家。
水浒研究领域,也是百家争鸣,近年涌现了许多革新的观点,与大家分享一下,从三个层面:作者说,思想性,艺术性。

作者说
主流观点认为水浒诞生于元末明初,但却解释不了水浒版本最早为何出现在朱元璋一百年后的嘉靖时期。
问题很多很杂,但我们从避讳角度看,却很简单,也许和历史上的朱元璋与小说中的白秀英有关系,您说,这俩人八竿子打不着啊。
那我来设问:白秀英为何姓白?
是啊,她父亲是白玉乔啊。白玉乔姓乔,让我们想起大小乔之父即东吴乔国老。
安徽庐江是大小乔的故乡,小地方,山东郓城更是弹丸之地,也出了俩东京来的舶来品歌手:白秀英与阎婆惜,你看白秀英牛气冲天,连都头雷横都不放在眼里。
如果白秀英姓马,水浒则在明代永远被禁被焚。因为朱元璋是皇帝啊,马皇后的名字就是马秀英!
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和乔国老算是一省老乡。
如果朱元璋看到此书,居然有酸文人拿他老婆的名字开涮,那还罢了?这就是水浒当初不敢出炉的一个原因。
现在你明白了吧,白秀英是大脚,因为马秀英是大脚,所以不写白秀英“金莲”。
且看作者如何酷爱金莲描绘:“淡黄软袜衬弓鞋”之金翠莲,“金莲窄窄”之阎婆惜,“尖尖的一双小脚儿”之潘金莲,“绿罗裙掩映金莲”之玉兰,“莲瓣轻盈”之九天玄女使者,“翘尖尖脚儿”之潘巧云,“弓鞋尖尖剪春罗”之刘太公女儿……
作者通过描绘美女用“金莲”,可能意在调侃马大脚,从而调侃朱元璋,因为朱元璋不仅杀害了许多功臣,连“吴中四学士”这样的文人也经常滥杀!
事实上,马皇后是个好皇后,仁慈、善良、俭朴,用金玉良言劝诫朱元璋昭雪了不少功臣。但中国文人历来感情用事,“恨屋及乌”,小说家未能免俗,“株连”了马皇后。
作者说金莲好倒还罢了,还经常出现“贼秃”、“秃驴”……等关键词,而朱元璋曾经两次当和尚,所以建国后最忌讳别人提起“和尚”二字,而作者不仅不避讳,还开篇就写鲁智深喝酒吃肉、见佛杀佛,这不是和朱元璋顶牛吗?
居然还有海和尚勾引潘巧云之事,这不是把朱元璋与马大脚一锅煮了吗?
所以,水浒一书诞生于元末明初的主流观点是极为可能的,只是水浒的正式出版不可能在元末明初,这不是当着和尚皇帝骂秃子吗?还有,那就是古代出书没有如今这样草率,两、三个月就可以完成一部小说的出版、上市、炒作。
大明王朝开始于1368年,施耐庵死于1372年,没有生逢明朝流通白银的时代。
主流观点的形成,来源于郎瑛,他是(1487~1566)明代藏书家,著水浒模仿本:《英烈传》,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红楼脂砚斋一样的第一位水浒学家、水浒索隐派鼻祖。
他在《七修类稿》中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可见,他在这句话里,也拿不准作者是谁,原创多少回。因为那水浒没有著作权意识,诗歌、文章才正经,那时候的小说好比现在的网络文学,自由挥洒。
因此,金圣叹是拿“宋江投降”说事,是对国变的心态改变,并非金圣叹就认为“宋江投降”是水浒的关键和重心。
关于水浒古本原创,可能原名《宋江》,是50回、60回、80回、90回乃至100回,绝非金圣叹所肯定的70回这一种解释和实情!

思想性
那么,水浒的主题是什么呢?
被称为 “异端之尤”的泰州学派一代宗师李贽(1527~1602)则称水浒为“绝世奇文”,影响了后来出版商家、编辑家 冯梦龙(1574-1646),制造了“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即是我们现在所言四大名著雏形,只是用《红楼梦》替换了《金瓶梅》而已。
现代水浒研究第一人是鲁迅,早在1912年就辑录了自汉至隋的古小说36种,编成《古小说钩沉》,即是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1920至1926年间在北京高校作为讲义,自然离不开《水浒传》。
继明代郭勋、清代金圣叹之后,真正为水浒研究做出历史性贡献的现代学者谢兴尧先生首先作《水浒传人物考》,紧接着余嘉锡先生又作《水浒传36人考实》,之后王利器(《水浒的真人真事》)、侯会(《水浒、西游探源》)、马成生《水浒通论》把考证的对象从36人发展到108人以至五代至明朝历史人物,陈斯园《重读水浒》,则是“水浒取材说”的集大成者,统一了500年水浒历史取材(在这方面是提倡者),着意水浒主题千年文化批判说,可谓“新新水浒”诞生!
在下愚见,重读水浒,主题分三层楼:起义说还是忠义说(文学角度),市民说(侠义说)还是反元说(史学角度),千年文化批判说(哲学角度)。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 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
赫然把宋江当成忠臣孝子,如汉代梁孝王保国卫汉与范仲淹人在江湖心在朝堂!
金圣叹起而反之,拍案而起,“痛恨宋江奸诈”如曹操:“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清末“西学东渐”,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以后,水浒研究也开始着重从社会政治角度来观察,说水浒是“社会小说”、“政治小说”,提倡民主、民权。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臆断,在《谈金圣叹》中嘲讽金圣叹腰斩水浒是蚍蜉撼树。
《水浒传》不是历史小说,也非写实,而是写意,如《金瓶梅》一样是截取一段故事而大肆渲染,好比蛇变龙,也好比基督教里《创世纪》说男人肋骨变女人。
《水浒传》截取的是历史宋江故事,《金瓶梅》截取的是潘金莲三角恋。
宋江史有其人,但称不上影响历史的大人物,不过小说出来后,就成大人物了。
“宋江起义” 和黄巢起义比规模太小,被海州知州张叔夜一千人就收服了。方腊起义是标准的农民起义,数万之重,规模宏大,哪里是宋江能对垒的,历史记载征方腊的领导,却是臭名昭著的宋徽宗的宦官童贯,可见是水浒是小说,非历史。
而小说宋江起义则在第七回末被写成数十万之众:“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历史宋江是昙花一现,小说宋江,则是农民起义领袖。
因此,一些学者对宋江农民起义质疑(例如没有土地诉求欲望),从而提出 “市民生活说”、 “游民文学”说、“侠义文化”说,重谈金圣叹老调。
例如,牛肉是个好东东,但水浒英雄吃牛肉则是反叛的标志,因为宋朝吃牛肉的大多是胆敢犯法强盗,合理宰杀耕牛,在大宋是被立法的。
可见英雄们“大块吃牛肉”非写实“社会风俗史”,而是小说虚构宋史。
当然,作者也客观反映了宋、元、明三朝的局部“清明上河图”,但非素描、工笔,而是中国大写意、西方印象派油画。
水浒看似写宋末,其实是影射五代、宋初,取材元末明初历史。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破辽故事虑亦菲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
阮小七曾唱“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也是忠宋,即是反元。
宋代即有巡检制度,市镇之有巡检可追溯至元代,明代天顺《重刊襄阳郡志》说:(郧县之南门镇)“元时置巡检司于此,今不存”。
可见水浒的官职等印记,是宋元明三朝杂揉而成“五粮液”,非一朝一代的客观描绘。
水浒成书,是渐进过程,非一人一代所为,出现明朝印记,是很正常的,但纵览水浒信息,深究水浒当初反元主题,可能是《水浒》的“原名《宋江》”成书于元末是可能的,《水浒》成书于明初也是正常的。
水浒主题当初反元,正是拿宋江说事。然而作者及后来作者,延伸、深化了这一主题,变成了文化批判。
若说孔子是中国雅文化的人大代表,而施耐庵则是中国俗文化的小说教主(清朝学者钱大昕提倡)。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有“寓教于乐”的传播接受学,周公“制礼作乐” 是“乐以教人”,孔子游春也说“吾与点焉”,施耐庵梦游梁山泊,也是“不亦乐乎”!
且看开篇词: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评议前王与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绕绕乱春秋”
按照当时的观点看,这是何等国士气魄,不仅批判“五胡乱中华”,而且批判宋代重文轻武的文官制度造成“大头巾”(秀才)误国,还批判了朱元璋的卸磨杀驴(李俊逃亡,鲁智深出家,即是反照),譬如李逵忠于宋江死,燕青忠于卢俊义生,即是忠告。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 "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的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
这也是“宋江版水浒”在明初没有出现刻本的原因,和《石头记》一样被尘封百年才面世,施耐庵后人、朋辈,有哪个不怕文字狱?
水浒作者进行千年帝王批判,倡导人文主义,也通过武松等自由主义行为艺术彰显平民意识。
作者看似英雄崇拜,也有对英雄的批判,例如 “三打祝家庄”是因时迁一只鸡引起的蝴蝶效应,攻打曾头市也为一匹马,这只是出师有名,结果是宋江所欲:“即目山寨人马众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的此庄,倒有三五年的粮食……”
梁山英雄一把火将独龙山烧作白地,直惊得李家庄庄主李应“目瞪口呆、言语不得”。
宋江征方腊,也是“自家杀起”,暗喻朱元璋灭张士诚、方国珍,所以作者描绘江南风景,非闲闲之笔,是劝谏帝王罢兵之意;所以让鲁智深、武松出家、火并王伦的林冲病倒,是马放南山之意。
而批判矛头,直指朱元璋,这一气概,如司马迁对抗汉武帝。
因此,水浒主题如水,是动态的,多重的,因为非一人所创,而是主创笔名施耐庵者主创《宋江》后,多人增补,才有120本《水浒全传》。
但其“千年文化批判”主题,一脉相传,始终不变,体会到两代作者的雄心壮志:国士情结。
古代的索隐与后来的考证本是中国学人的左右手,能具体分析问题,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就是千里马夜视猫!
别以为水浒是武打小说,作者明白告诉我们“试看书林隐处,才识俊逸儒流”,譬如鲁智深之顿悟,晁盖之义气,公孙胜之飘逸,武松之豪迈,燕青之快活,李师师之风雅,琼英之兼美,李俊之高远……
宋江看似水浒主角,其实作者是当“反面教材”(领袖语录)来写的 ,金圣叹更是把宋江当水浒第一反面人物,明褒暗贬也。
所以,红楼略写甄士隐(如公孙胜)、甄宝玉,大书贾雨村(如宋江)、贾宝玉,也是此等笔法。
至此,水浒取材五代到明初这一时限被发现,从小说创作角度分析人物取材,重读水浒千年批判主题,才使水浒研究更上一层楼。
打开视野,我们就明白水浒主写大宋开国之初,也有明朝开国之初。
开篇洪信引出武将,暗喻洪武开端,而先说朱武聚义少华山,陈达含徐达之名,杨春含常遇春之名,朱武是朱国瑞与朱升合姓,后来芒砀山的樊瑞入伙梁山,才凑成“朱国瑞”之姓名。
如果这个比较复杂,看鲁智深开场水浒,可不是朱元璋这个小和尚最后“得成正果”,哪里是鲁智深顿悟,言外之意是“朱元璋得了天下”,这即是水浒让鲁智深与宋江结局的原因。
宋江征方腊,历史悬案,八成是没有,但却暗喻朱元璋大战江南四大天王,而宋江又取材于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比较多,而陈友谅则是混江龙李俊的量身定做,宋江血染浔阳江口,即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江西鄱阳湖。
即是水浒中间,也穿插明朝历史,例如二潘是张士诚部下二潘将叛变投降朱元璋,曾家五虎是方国珍五兄弟,方国珍曾投降元朝,所以被骂“是大金国人”。
然而,最难厘清的水浒取材,那就是宋、元、明的野史、话本、杂剧,而这些,恰是水浒作者的最爱,也是最让水浒研究者迷茫的一头雾水。
单就话本而言,南宋罗烨《醉翁谈录》里的《花和尚》、《武行者》还比较好认同,而无名氏《大宋宣和遗事》就有南宋说、元朝说,而这部书里的宋江36人,就是水浒最早故事起源。
元杂剧水浒戏,更有几十种,现存十种左右,其中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等比较有名。
譬如李逵,真实的历史是《宋史·高宗纪》:建炎三年闰八月,知济南府宫仪及金人数战于密州,兵溃,仪及刘洪道俱奔淮南,守将李逵以密州降金。
李逵原型实在不堪,居然是没有骨头的“投降派”。
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里,李逵见郭念儿与白衙内通奸私奔,其夫孙孔目到衙门告状反被监禁。李逵打抱不平,用蒙汗药麻倒狱卒,救出孙孔目,放走满牢囚犯,又伪装成随从混进衙门,杀死白衙内及郭念儿,还蘸血在白粉墙上写下自己的大名。
可见,小说李逵非历史李逵,也非“诗人”李逵,而是高文秀所创造的李逵,但其“蘸血在白粉墙上写下自己的大名”却分明被写在了武松身上。
郑振铎认为南宋即有《水浒传》底本,元杂剧中水浒故事与今本《水浒传》相去甚远,是因他们零星取用元中叶的《水浒传》,各自取舍,各自想像。
固:着眼水浒前500年历史取材研究,打开新视野,打通文史哲,明白了水浒主题和故事取材,也是作者的知音了!

艺术性:写意还是写实?
将水浒定位为标准的现实主义小说,是值得反思的,因为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作者没有现实主义的现代概念,小说却具有很多现代主义特色。
现实主义小说具有小说三要素,我们就从三要素来分析:人物,环境,故事情节。
先说人物描写,英雄出场,大多用白描,的确是现实主义特色,但武松一口气喝18碗酒,就是“传神”了,即是当时高度烧酒并不普遍,属于啤酒类,以“三碗不过岗”为标准,武松也是天神,非人了,成酒缸了。
这就是小说为打虎造势,非写实而是写虚,是表现而非再现。
宋代没有打虎案例,“武松杀虎”,是在杭州刺杀被称为贪官的“蔡虎”(蔡京的儿子),小说武松打虎自然是五代时期李存孝打虎传说的演义,这也是表现主义创作,而非现实主义实录。
历史宋江是侠盗,小说宋江有帝王之气,这已经非写实,而是虚构了。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调小鲜,水浒作者也会玩帝王游戏,把“宋明”帝王糅合于“宋江”身上。
红楼作者会“一人两面法”(脂砚斋批云分身法、合身法),想来是从水浒作者学来。
再说环境描写,北宋历史梁山哪里有八百里水泊,那不过是元代杂居水浒戏的说法,而被水浒传作者采用了,正好比红楼梦里大观园,不必拘泥到底是南京与北京,而是融合。
水浒看似宋末的《清明上河图》,但我们明白了其取材是宋、元、明三朝,这个说法就矛盾了。
例如宋元明服装混搭、官职错位……让“水浒专家”也眼花缭乱,可见,水浒梁山泊如红楼大观园,不过是杂剧舞台而已。
因此,水浒非宋末《清明上河图》,而是“多朝版”,不过宋代的特色多了些。
水浒不仅着意都市故事,而非农村,还有魔幻现实主义倾向,例如开篇以洪信放魔,结局以宋徽宗入梦,都非现实主义写法,而是古代作者对现实主义的习惯超越,更如密布全书的魔道斗法,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以为是封建时代科学不发达所致,其实,这样创作,不过是作者要打破人与鬼、生与死的界限,更好地表达主题而已。
我们称颂蒲松龄的系列小说是当代版的《人鬼情未了》,却视水浒作者为迷信落后,这是不公平的!其实,这也是古代小说惯例笔法。
就故事情节而言,从历史宋江到小说宋江,也是作者魔幻现实主义制造,把老虎写成了大象。
水浒虽然以宋江为主线人物,却也安排了鲁智深、林冲、晁盖、武松、卢俊义的“十回书”,并且穿插了其他英雄的传记,宋江如母球,撞击其他球落袋后,再撞另一英雄。
宋江是长江,其他是支流,宋江是树干,其他是枝干。
例如林冲是80万禁军教头,而东京当时也就100万人口,岂不荒唐?这就可见,水浒不是复制东京生活,而是极度夸张了北宋军事实力。
后部水浒标题大多是宋公明为标题,却也暗说宋江的支流枯竭,枝干枯萎,宋江必死无疑。
如此“网络结构”,影响了《儒林外史》成其伟大结构艺术,被很多人视为“过散”,其实是水浒作者与吴敬梓的小说特色:散点透视。
现代中国小说,大多有完整的故事主线,就是古典作家结构艺术绝技失传的反证。
当然,水浒作者没有像红楼作者那样更彻底地放弃主线的决绝,还是很中庸地保持了“宋江主线”。
不过,水浒故事情节构造,却含有法国新小说派的许多特色,例如“重现”手法,梁山伯、金沙滩与陈桥驿等关键地点重复出现,是象征主义,分别暗喻宋江如周王开国,如杨业惨烈于金沙滩,如赵匡胤陈桥驿兵变。
这就是南宋“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所云:“‘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文字游戏”也是新小说派特色之一,水浒作者更深谙此道,安排两个刘太公女儿“被强暴”故事,调侃山大王的压寨夫人之梦。
再如作者就是抓住方姓做文章:方国珍姓方,方腊也姓方,这是废话,但也许作者就是要表面通过宋江征方腊暗说朱元璋征方国珍与张士诚,而其主要战场选择则是张士诚地盘,可见主要是灭张。
从现实主义的小说三要素分析,水浒具备,同时超越,可见比中国现代小说还高妙,但“现代主义”是水浒作者头脑概念里没有的,所以如定性红楼为“写意小说”是科学一样,水浒也是“写意小说”。
水浒写女人红杏出墙,是要男人离开温柔乡,奋斗抗元,红楼写女儿白玉无瑕,是讽刺清初投降派大节已失,文不如妓;二者都非写实,而是深意存焉,可惜后来人只看表面热闹,不看门道,只看表演,不亦悲乎?
同比西方文艺复兴小说,《水浒传》为中国赢得文艺复兴时期世界文学冠军荣誉。
从综合实力而言,水浒与红楼是中国小说史“两座珠峰”(很多红学砖家自诩攀登珠峰,但没有一个人攀登过世界第二高峰即乔戈里峰,水浒,就是乔戈里峰),无与伦比,《三国演义》大气磅礴但艺术性不高,《聊斋》艺术高妙但规模太单薄,《儒林外史》主题高雅但浪漫气息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重读水浒,体味作者的国士情结,学习作者的春秋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