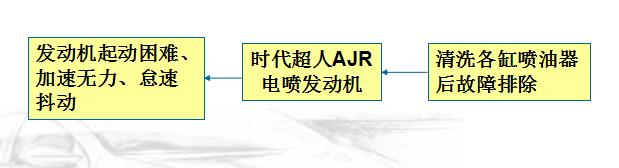在日本人眼里,牧溪大概就是他们心中山水画的顶峰。而这位来自中国本土的画家,我们却对他知之甚少。甚至于,连他的本名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姓李,是位禅僧,具体生卒年不详,只从历史碎片中,知道他隐约是南宋时期的人。
川端康成曾在《源氏物语与芭蕉》中说到:
“牧溪是中国早期的禅僧,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似乎是由于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几乎不受尊重。而在日本却受到极大的尊重。中国画论并不怎么推崇牧溪,这种观点当然也随着牧的作品一同来到了日本。虽然这样的画论进入了日本,但是日本仍然把牧溪视为最高。”
因为没有史料记载,牧溪简直变成了谜一样的人物,据说他曾在杭州西湖长庆寺当杂役僧,南宋灭亡后圆寂,这倒是让人想起了《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看着普通,却总觉得深藏不露。
这位在中国滚滚历史尘埃中,几乎销声匿迹的画僧,却在日本受到了极大欢迎和一致好评。
牧溪的画很简单,画面干净,通常一整幅画中就只有一两个简单的事物,比如这幅《六柿图》,看着确实很单调,没有什么亮点可言吧,就是随便画了六个圆圆的东西而已。
可这却被世人公认为是禅画中的经典之作,懂他的人,能从中得出不一样的见解。其笔法简逸,墨色分明,看似简约、朴拙,却透露出静远的禅思。
水墨皆禅,万法唯心,牧溪的画被归为禅画的范畴,禅画不同于文人画,不用把事物画得如何逼真,它最主要的,是要在画中传达出一种生命超脱的意涵,让人看了静心,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所以说,牧溪的画中,即便是一只飞鸟,一个柿子,其所透露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意蕴,却能被感知,这就是日本人推崇他的主要原因。
在日本,牧溪的声望不可谓不高,他与玉涧构成日本“禅馀画派”的鼻祖之一,被称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在中国,牧溪本来的资料就少,能看到的关于他的大多是批评。
比如元人汤垕着说:“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竹,粗恶无古法。” 元代庄肃说:“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明代朱谋垔也说他“意思简当,不费妆饰,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
在两个国家呈现两极分化,这可真是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也和当时日本盛行禅风的风气有关,日本人谈禅,不仅是宗教信仰,也是种文化生活。你看现在日本的庭院风格,就是禅意的体现,当然,这也是中国佛教禅宗于宋朝时期传至日本的原因。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湖南的八处佳胜,名为“潇湘八景”,分别是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
关于“潇湘八景”的文学作品很多,影响也很大,画作的话,牧溪也画过。如果说有人欣赏不来他那些简单静态物体图,那他的《潇湘八景图》,肯定能触动你的审美和内心。
牧溪的“潇湘八景”是最简单的水墨画,看上去笔触简易,但却在寥寥数笔中展现出变幻丰富的晕色,将潇湘地区的空濛之光绝妙地表现出来。你看他的这几幅图,好像就是简单又空洞的画面,但又像是将天地容纳其间,是那样旷远清淡,即使不懂禅,也能隐约感受到其中幽远超然的韵味。
在日本,“潇湘八景”甚至达到了每个人都知道的地步,就连日本上小学的小学生有时候都要学。而牧溪的《潇湘八景图》中有四景遗失,仅存的“烟寺晚钟图”、“渔村夕照图”、“远浦归帆图”、“平沙落雁图”四幅真迹,都在日本收藏。
可以说,牧溪极简的水墨画在日本找到了知音,枯淡清幽,这不仅是牧溪画中所展现出来的意境,更是日本所崇尚的独特的美,他们追崇的是那种隐隐约约、无声胜有声的美。
这就像日本著名的那句“今晚的月色真美”一样,委婉矜持,带着特殊的美感。所以说,牧溪画中的空寂和清淡,正是日本人所喜欢的那种风格,也难怪牧溪会在日本受到追捧了,这也正应了那句话:艺术不分国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