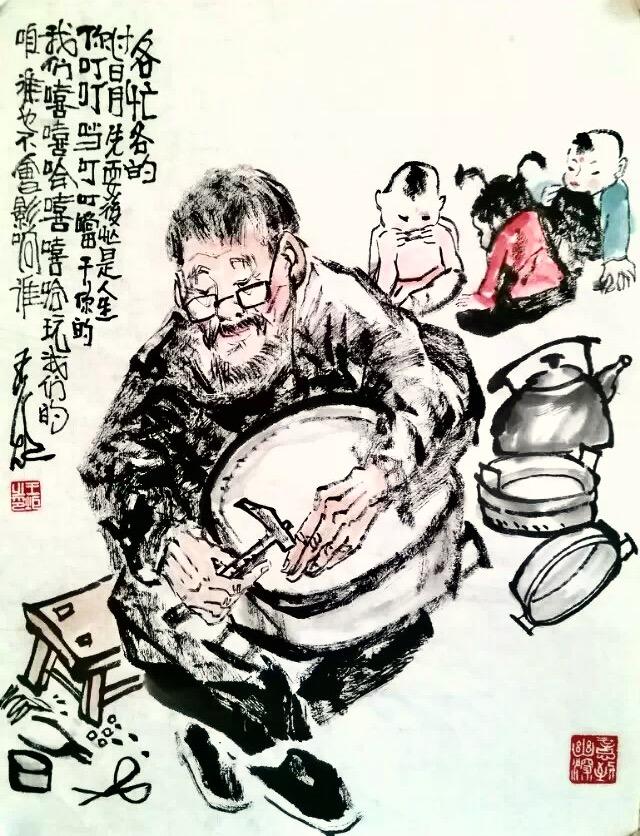来和启功先生一起探讨汉语诗歌的声律句式、对偶、用典和押韵等问题吧!
启功先生: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上)

这里要谈的“汉语诗歌”,是文言文体的汉语诗歌,至于新诗、各兄弟民族语言的诗不包括在内。要说的“构成”,是指这些旧体诗在体式方面的构成条件。好比说桌子,把它拆开了看,桌子面是一块板,四条腿是四条长木头,等等。我现在就是要解剖一下汉语诗歌,看看是什么语言条件,构成了汉语特有的诗歌体裁。同时,也要看一看在体裁方面历代诗歌的发展,表现为什么。

一
汉字与诗歌的声律
先从汉字说起。汉语的字是一个一个的单音节方块字。过去有人说它不好,应当拼音化。那是以拼音文字做标准看汉语,说汉语落后。现在看来,一个一个的单音节,正可以说是汉语的特点。汉语的字是单音节,但是在汉语的单音节中也有自己特有的变化,就是声调。一个音节可以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变化,在有些方言里,一个字的读音可以多达八个、十个调。平上去入或更多的调,可以归为平仄两个大类。现在的一声、二声,古代都是平,其它上、去、入都是仄。仄声字是低调、抑调,平声字是高调、扬调,平仄实际就是高矮,声调高的叫平,声调矮的叫仄。连起来念,如五言诗句就是“仄仄平平仄”,通俗点说就是“矮矮高高矮”。这样说就容易懂了。
汉字是单音节而且有声调高矮的变化,这就影响汉语诗歌语法的构造。我常说汉语的诗歌像是七巧板,又如积木。把汉语的一个字一个字拼起来,就成了诗的句子。积木的背面是有颜色的,摆的时候得照着颜色块的变化来。由单字拼合成诗句,它也有个“颜色”问题,就是声调的变化,汉语诗歌特别重视平仄、高矮,高矮相间,如同颜色的斑斓,这样拼成的诗句才好听,才优美。所以要谈汉语构成,先得说汉字,先得说汉字的声调。高高矮矮、抑抑扬扬的汉语诗歌是有音乐性的,诗句的音乐性正来自单字的音乐性。这是首先要明确与注意的。
注意到汉字有四声,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世说新语》里说王仲宣死了,为他送葬的人因为死者生前喜欢听驴叫,于是大家就大声学驴叫。为什么要学驴叫?我发现,驴有四声。这驴叫éng、ěng、èng,正好是平、上、去,它还有一种叫是打响鼻,就像是入声了。王仲宣活着的时候为什么爱听驴叫,大概就是那时候发现了字有四声,驴的叫声也像人说话的声调。后来我还听王力先生讲,陆志韦先生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入声字在北方话里的消失。入声字都有一个尾音,如“国”,入声读guk。有人说是后来把那个尾音丢了,所以北方没有入声字。其实不是。北方没有入声字,是读的时候把元音读长了,抻长了一读,就成了guó。这就是“入派三声”的原因。

汉字有声调于是诗歌有平仄,不过就汉语诗歌的声律而言,单从字的调说还不行。五言诗或“仄仄平平仄”等平仄句式,七言诗有“平平仄仄平平仄”等句式,我们看,五个字后七个字拼成的诗句,一句中多数的字,是两个平声字在一起,两个仄声字在一起,成为一个个的小音节。我在《诗文声律论稿》那一篇文章里,曾经说到过“平仄竿”的问题,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交替进行反复无穷,犹如竹子的节,五言、七言的各种平仄基本句式,都是从这条长竿儿上任意截取出来的。那本小册子出版后,不少喜欢古体诗的朋友对我说,“平仄长竿”很说明问题,问我从哪里想出的呢?是啊,以前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汉语的诗句要“平平仄仄平”呢?我请教语言专家,请教心理学家,都没有明确答案。有一回我坐火车,那时还是蒸汽机车头,坐在那里反复听着“突突”、“突突”的声音,一前一后,一轻一重。这使我联想到诗的平仄问题,平平、仄仄也是两个一组一组的,一前一后,一轻一重。当时我有一位邻居乔东君先生,是位作曲家。我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他说,火车的响声,本无所谓轻重,也不是两两一组,一高一低,这些都是人的耳朵听出来的感觉,是人心理的印象。人的喘息不可能一高一低,而是两高两低才能缓得过气来。这一下子使我找到了平仄长竿的规律:汉字的音节在长竿中平平仄仄重叠,人才喘得过气来。讲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单音字的汉字,反而因容易合乎某些心理规律,形成汉语诗歌的格律,如果是多音节,恐怕就不会是这样。

二
汉语诗歌的句式
汉语的诗歌里,句子的形式从一个单字到若干字的都有。一个字往往不成一句,但在一句诗开始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字,叫领字,词里头很多。比如柳永那首《雨霖铃》“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其中的“对”字,就是一个领字,在过去的有些本子中,它是单提行的。两个字的诗句也不少,如《诗经》的《鱼丽》那一首,“鱼丽于罶,鲿鲨”,以后两个字的句子更多,词里的《如梦令》“如梦,如梦”、“知否、知否”皆是。三言诗句起源也很早,《诗经》“江有祀,不我以”就是,汉代的郊祀歌里也有一些。四字句的诗大家都很熟悉,《诗经》主要的句式就是四言。四言进至到五言,就很有意思。四个字一句,形式上是方的,“关关雎鸠”,“关关”、“雎鸠”是两个字两个字的。一是内容表达上不太够,另外也显得不够灵活,有些板。加上一个字,一句中就有单字有双字,富于变化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读来既流动又舒缓,活跃多了。五言诗也是在《诗经》里就有,但还没有全篇都是五言的作品,汉魏以后,就成为了汉语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汉语诗歌的发展情况而言,一言、二言、三言及四言,都不是主流形式,六言也是如此。六言也是早就有,唐宋以来的诗人也作了不少六言诗,比如王安石的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但总的来说,六言占的比例还是很少。七言诗和五言一样,是主要形式。还有八言。对联八个字的多,但作诗八言的就很少。为什么呢?实际上八言就是两个四言,还是四言诗,所以名副其实的八言诗不好作,也就很少。九言诗作的人也少,因为九言也容易成为四言加五言,费力不讨好。九言以上的诗反而多些。我也试着作九言以上的,我有一首《赌赢歌》,编在我那本《絮语》里,有人对我说起它时,我说那不是诗,是“数来宝”,文人一般是不作这个的。

上面讲诗的语言是从少往多里讲,还有一种情况是汉语的诗句可以随便去掉字,往少里变。有一个笑话,杜牧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有人说每句的头两个字是废话,可删,于是就变成了“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既然可以不废话地减,有人说还可以减掉前边的俩字,就成了“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有人还嫌多余,再删,最后就剩下“雨,魂。有,村”了。这虽是笑话,有些强辞夺理,但也说明,汉语诗歌的句式可以抻长也可以缩短,长短自由。另外,我在《汉语现象论丛》中,曾举李商隐《锦瑟》为例,说明诗的语句中,修辞的意味要大于语法的意味。像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等四句,若不是从修辞的角度看,而是从语法角度去看,那也真像是“废话”多了。可是诗歌正是由修辞来达到营造意境的效果。汉字的单字特征,实际正影响着汉语诗歌语句的长短自由。
(根据录音整理,原刊于《文学遗产》2000年01期)

作者简介

启功
启功(1912-2005),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等。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长按二维码关注
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丨版权所有丨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林丹丹
专栏画家:黄亭颖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