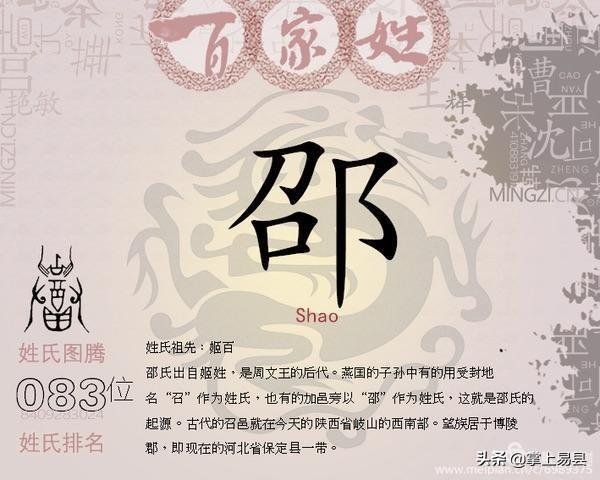01
“囡囡,走,带你去泗港吃麻尖角。”
“好,我知道了!”才睡醒还有点迷糊的我敷衍地答应着。
咚咚咚!咚咚咚!祖父生满冻疮和已经皲裂的手敲着我的房门。
“走了,早点去吃第一锅。”依旧催促道。
“马上就起。”我又往被窝里缩了缩,看了眼手表,现在不过早上五点。窗户因为室内外的温差蒙上了一层雾,不时有几滴水珠从窗户顶滑下来,外面还是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出发,还能赶上坐第一班公交车回来。
港城的冬天就是这样任性,越是临近过年,越是喜欢下雨,下了半个月的连绵小雨,只要开了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让人心里烦闷得很。“三日寒”“四日暖”,估摸着怎么也要年初五初六天气才能放晴。
小时候,我还不大喜欢吃麻尖角。
02
等到出门,天已经蒙蒙亮,东边鸭蛋黄色的一片,映衬着高楼,很是好看。祖父带着一顶深色的毡绒帽,盖住冻疮结痂的耳朵,身穿一件咖啡色的光面羽绒服走在前面,两只手像从来不知道冷似的裸露在外。真的,好像从我记事起,祖父冬天就不带手套。
我和祖父要去的泗港街在西边,路上要过两个桥,步行大概四十分钟也能到了。同往常一样,街口的桥上就有卖菜卖水果的老头老太。桥是个下坡,摊点就从桥上一个接着一个摆到坡地。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这个泗港街到底从哪里开始算。桥底下时不时会有船开过,黑乎乎、油得发亮的发动机在不知道是船头还是船尾“突突突,突突突”有节奏地响着,冒着一团团黑烟。
过了桥,就是主街。打头开着的铺子大多数都是粮油裁缝店,只有几家零星开着,还不如刚才桥上热闹。再往前走两步,右拐进一个弄堂,走到头是菜场。卖麻尖角的店就开在这条弄堂里,从前往后数第三家。
店铺也看不见招牌,被夹在中间,南北方向开着,有种被前后夹击的压迫。烘麻尖角的桶炉被老师傅摆在靠北一侧,旁边摆着一摞摞垒起来的煤炭还有一口炸油条的大油锅,沥油的铁框里已经装着两根炸好的油条。桶炉后面是一条停电瓶车的巷子。
03
“来啦,老样子?”老师傅招呼我和祖父在长桌边上的位置坐下,老板娘笑着过来用别在腰间的手巾擦净方木桌上的水渍。
“嗯,一碗咸豆腐花少加辣,一碗豆浆少点糖,一个咸的麻尖角,一根油条。” 无论来多少次,都是一样的搭配。
店里一张高高的长木桌摆在左手边,很是占地方,桌上桌下摆满了面粉袋。紧挨着长桌的是一张矮了十公分的方木桌,桌底下放着七八个热水壶,桌上黄色的搪瓷罐子摆放地整整齐齐,里面分别装着碎榨菜末、辣椒酱、小虾米、酱油、葱花和绵白糖,每个大碗配一个调料勺,边上高低错落地摞着三五空碗,竹篮里盛着刚从清水里捞出来的瓷勺还在滴水。旁边是用小木凳架起来的两个保温桶,笨重的桶盖扣得死死的。
由于店铺面积实在有限,只容得下四张小方木桌,桌子周围有的是坐两个人的长板凳,有的是单人的木头板凳,有的是塑料小板凳。这些上了年头的木桌不是这边缺个角就是那边短个桌腿,唯一的相同点就是每张桌子上都有一盒抽纸,别无他物。
上得最快的是豆浆。一个浅口的大瓷碗,里面加一勺半绵白糖便端到客人面前,回身再提来热水壶,打开软木头瓶塞,乳白色的豆浆从瓶口倾泻而出,顷刻间与碗里的绵白糖相互交融,再用瓷勺轻轻搅上几圈让白糖完全化开,勺子和碗底相互研磨的声音变得清脆。舀起一勺豆浆,无论多浅的勺子都看不见勺低,只有水和黄豆的比例恰到好处才能有这浓淡相宜的杰作。豆香里掺杂着丝丝甜味,一下子从口腔滑到胃里,连带着手脚也暖了。

“哦哟,这不是老阿龙吗?带着孙囡来吃朝饭?(方言:带着孙女吃早饭)”一个瘦瘦高高穿着尼龙黑色外套的老爷子走进店里。老爷子眼窝很深,皮肤晒得黝黄,坐在小板凳上颇为利落板正。
“欸,吃朝饭。恁也来吃朝饭?(方言:对,吃早饭。你也来吃早饭?)” 老阿龙是祖父的外号,村里的、生产大队和厂里的老爷爷都这么称呼祖父,看样子是碰到熟人了。
“来吃豆浆,再要两个麻尖角。”祖父和这位老人说着说着便打开了话匣子。
04
老师傅虽只年近不惑,但头发已白了大半,和妻子两人经营着这家早餐铺子,身形偏瘦却壮实,常年带着一副藏青色的皮袖套,围着一件白色布质的连年的工作围裙在长桌后面揉搓面团,每天上百次的弯腰贴饼使得他略有些驼背,空闲下来的时候还会和客人聊上两句家常。忙碌的店铺生意让他显得古枯苍老,像个已过半百的中年人,只有一双沾满干湿面粉的手看不出来年纪。
老师傅一边照顾油锅,一边看顾桶炉。揉在一起好拉长的的油条两根两根拧,抓、拍、一扔、夹,动作流利顺畅。这里刚下锅的油条在油锅里翻滚,发出“滋滋滋滋”的声响,本来又细又白的油条便在铁锅中慢慢变成淡黄,土黄,深黄,金黄。最后捞出来控油,微微放凉些再包上一张白纸就可以上桌了。油条蓬松酥脆,咬一口还能掉下些脆皮碎渣,不论是配豆浆还是豆腐花,亦或是空口吃,都只有油香味。

筷子的尖尖永远都是黑黢黢的
老师傅做的麻尖角是港城的特产之一,十里八村的都知道,但在外却鲜有名声。麻尖角形状似菱形,两头尖角,一面洒满黑白芝麻。港城的居民们以形为名,以此取名麻尖角。为做这麻尖角,老师傅必得起个大早将“桶炉”的炉子里装上煤炭生旺。桶炉和柴油桶差不多大小,外形相似,中间有个腰鼓状的孔,老师傅就从这个孔里将麻尖角贴在鼓壁,鼓底则是用来点碳加热燃烧的,原理有点像做传统锅贴的炉子。老师傅做麻尖角的功夫也是做老练到家,将翻来覆去揉好的面团再摔打几个来回,逐渐把面团拉长变成扁长条状,然后在面上刷一层薄油,抹上一层料,甜口的抹的是糖,咸口的撒的是盐,涂抹均匀后将条子以中线为基准折叠,用力量适中的力压实,面上再刷一层薄油,铺洒上一层黑白芝麻,用刀将面团胚子斜着划成菱形,剩余的边角料就揉进下一个面团,也不浪费。
接着,是将做好的胚子贴进桶炉内部烘熟。只见老师傅挑起胚子,有芝麻的一面放在自己的右手掌上,胚子背面涂上水,迅速伸进桶炉内,将胚子撩在桶壁上,再飞快地将手抽出来。要将半成的胚子牢牢贴在桶炉壁上,一是要有经年累月的经验,二是手速不能犹豫,进炉、贴饼、出炉都不能迟疑,否则就很容易失败。
05
渐渐地,麻尖角高温的煤炭下一点点膨胀起来。要做好这麻尖角还需要一个工具——火钳,把烘烤地正好的麻尖角一个个铲出来,一圈圈摆在桶炉面上晾着,在冬日的阳光里冒着热气儿,分外诱人。老师傅的火候是成千上百贴麻尖角练出来的,贴着桶炉的那一面焦香,被碳火烘着的一面酥脆,至于麻尖角里头的馅里包着的是师傅十来年的手艺。
吃惯麻尖角的人知道,刚出炉的麻尖角色香味俱佳,即便是被麻尖角烫得两只手你来我往地来回倒换。祖父也不待凉下来,只吹乎两下就往嘴里送。咸口的麻尖角配上甜口的豆浆,一点儿也不逊色于豆浆油条的搭配。

这个就是麻尖角
老师傅夫妇二人分工合作,老师傅负责麻尖角、油条、豆浆,老板娘收拾桌碗、做豆腐花,配合地十分默契。
相比之下,老板娘有些发福,脸上总是油亮亮的。她很少说话,可干起活来手脚十分麻利。开木桶,一手碗一手长杆平勺,手腕来回扭转,轻撇去最上一层的清豆花水,老板娘盛豆腐花时必定是大块完整的豆腐花,三平勺豆腐花就能将浅口的大碗装满,只有大块的豆腐花能细密地包裹着黄豆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散发的清香。接着,一勺碎榨菜末,半勺辣椒酱,一勺小虾米,两勺酱油,再撒少许葱花,一碗咸口的豆腐花就完成了,少哪一味配料都是不完整的。若是甜口就简单多了,在盛完的豆腐花上加一勺白糖即可。微胖的老板娘身上是一件花围裙,围裙前缝一个布口袋,收钱专用,里面都是小额一块、五块、十块的零钱和硬币,若是收到五十、一百的大额,老板娘就会塞进围裙里头的上衣口袋里,然后再将围裙系好,找零钱、收碗勺、抹桌子一气呵成。
天越来越亮,人也越来越多。泗港街后头是毛纺厂,六点到八点是生意最好的时候。老师傅夫妇俩在白花花的雾气里来回穿梭,几张小方木桌不知翻了几次台,桶炉里的碳添了又添,饱的不止是港城人的胃,也唤醒了这座城市的味蕾。
06
这一餐早饭,我和祖父两人,一碗豆腐花,一碗豆浆,一根油条,一个麻尖角各一块钱,统共花费四块钱。吃完早饭,出了弄堂,天已经全亮开了,泗港街也比来时热闹了好几分。临河有几户人家开了自家的院门,原本湿漉漉的青绿色板石已经晒得七八分干,桥上小商小贩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叫卖果子、蔬菜和手纳布鞋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打工的中年人三五成群聚在一堆聊着前两天接活的人家,脚跟前纸板上用马克笔写着自己的或打橱柜或砌灶台的手艺,真是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
这时候家家早餐店门前挤满了人,铺子前烟雾缭绕,看不清店家的脸,也看不清食客的脸,熙熙攘攘的街上人来人往,人人行色匆匆,却没有一个人落下这一餐。长江下游南边的小镇早饭吃食左不过是内馅五花八门的包子、茶叶蛋、炸米饼、饭团、麻团、南瓜粥、黑米粥、豆浆还有小笼包等等,像祖父这样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人却从未吃腻过。
家乡有这样一句农耕谚语:三百六十行,种田第一行。生意钱,三十年;衙门钱,一蓬烟;种田钱,万万年。唐人爱喝粥,宋人吃早茶。尽管一日三餐几乎是大多数人都共同认可的饮食制度,但同样的饭食在这片土地上却可以衍生出各不相同的生活节奏。简单平淡的生活有时候并不一定是迫于无奈,有时是家乡人内心深处最深的向往。
“走,买完菜回家了,囡囡。”
“好,公公!(方言:爷爷)”
07
小时候想着逃离,长大了念着回归。上大学时,和父母赌气,毅然决然地去了北方,小半年回来一趟。但人似乎只有真正远离了家乡才会深切地怀念熟悉的人,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味道。南北差异也不再是朋友圈里的调侃,而是记忆里的故事。
只是前两年回家,城区规划建设,港城处处修路盖楼,泗港街的几处弄堂悉数都拆迁了,原来的店铺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搬走之前去过两回,买了两个麻尖角吃。和老师傅聊起做麻尖角的功夫,老师傅说:“店是要拆了,手艺可不能断咯!”彼时,店里又多了两个人,老师傅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干起活来日渐熟练,不过偶尔还是会做坏两个麻尖角,挨老父亲一顿训。在旁边打下手的除了老师傅的妻子,还有老师傅的儿媳妇,最后一次去的时候,眼瞧着没两个月就要生了,不久便是三代同堂的福分。
虽然说港城不止这一家做麻尖角的早饭铺子,但坐在那个小方桌吃豆腐花,听从前村里的人和祖父聊天,不厌其烦地看老师傅做麻尖角胚子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