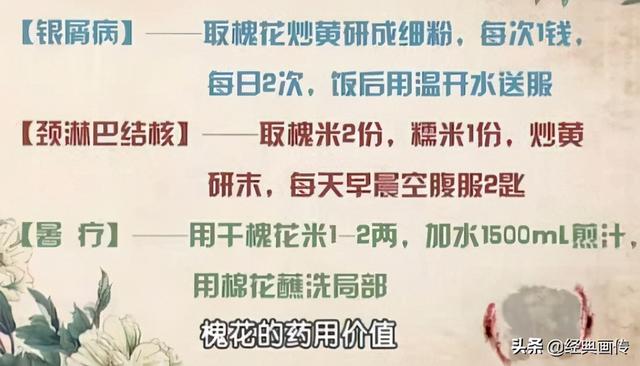近年来,随着老辈凋零,大家叹惋的不仅是哲人其萎,也在怀想或反思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范。以中文学科为例,如果可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为代表或者象征的话,民国时期成长 起来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第一届成员,已经全部谢世,基本上是在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二届成员,也可以说新中国第一代学人,目前也只有裘锡圭和黄天骥二位教授硕果仅存,且他们仍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近日,15卷本近500万字的《黄天骥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以下简称《文集》),《文集》包括《〈西厢记〉创作论》《〈牡丹亭〉创作论》《读元曲明词随笔》《诗词曲十讲》《冷暖集》《朝夕集》(均戏曲研究论文集)、《深浅集》(诗词小说论文集)、《俯仰集》(评论与序跋集)、《方圆集》(碑铭、诗词、对联与访谈)、《周易辨原》《纳兰性德和他的词》《诗词创作发凡》《中大往事》《岭南感旧》《岭南新语》(均散文集),其中《〈牡丹亭〉创作论》属于首次问世的新著。
黄天骥教授常说,他们这辈人,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我清楚自己不可能做大师,我只希望能做好一座桥梁,只要做好老一辈和年轻一辈之间的桥梁,我就完成任务了”。这固是黄先生的谦逊,但也确实可以从《文集》中看到一代学人的学术传承和新变。
一
黄天骥教授自谓其学术研究是以戏曲为主,兼及别样。从王起(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治戏曲。王先生以治经之法治曲,通过代表作《西厢五剧注》等,为中国戏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1981年教育部组织为期一年的全国高校师资培训班,戏曲学科就交由中山大学负责。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回忆当年黄天骥老师给他们上课时,文献征引翔实,辨析精审,特别是完全不用讲稿,而所引文献同学们课后核对,竟然可以做到一字不差,令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对文献材料的重视及养成的功力,显然与王先生的教导和训练有关;王先生在为黄天骥老师1982年出版的论文集《冷暖集》所作的序中,也有具体介绍。1961年他们合作《中国戏曲选》,以元代部分为例,要求他和另外一位青年老师以“聪明人要下笨功夫”的精神,从校勘元人杂剧的不同版本入手,再确定全书体例和各剧条释;不仅要坚持校勘,还要逐条写校勘记,终于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元代部分的定本和注释工作。到1973年,“羽翼渐丰”的黄先生又与王先生合作选注了《聊斋志异》。
这种合作,其实就是传承,后来也成为中大戏曲学科的传统。八十年代,王先生领衔,老中青三代合力整理校注堪称典范之作的《全元戏曲》,黄天骥教授不仅是队伍中的骨干,还担负起了主要组织的角色。而新近结项的国家重大攻关项目——《全明戏曲》编纂及明代戏曲文献研究,则是黄天骥教授领衔,与弟子黄仕忠教授共同主编的鸿篇巨制。此外,黄天骥教授还主持出版过十几种戏曲选注本。戏曲文献整理与校勘的传承,不仅在黄天骥教授这一代人中得到了很好的承传和发展,在下一代学者中,更展现出发扬光大的良好势头,而尤以黄仕忠教授为著——他不仅单独主持了国家重大攻关项目《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此前还主编出版的《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大木康教授合作编集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两书同时获得2013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更是在古籍整理出版史上鲜见。
从中大戏曲学科三代甚至四代人在戏曲文献方面的实绩中,我们既看到了扎实严谨的传统学风,也看到了开拓创新的气魄。
二
董每戡先生是知名的编剧和导演,1932年即发表《C夫人的肖像》。转入戏剧研究后,在王国维注重史实考证、吴梅强调戏曲唱腔之外,他另辟新径,从舞台艺术角度出发,强调“戏曲,主要是戏,不只是曲”“构成戏剧的东西,‘舞’是主要的,‘歌’是次要的”。分析剧本,也抓住戏剧矛盾,沿着矛盾主线的发展变化剖析,注重从戏剧人物的行动、动作阐析戏剧。《五大名剧论》的特点很明显,极少版本稽考,不做宏观论述,而是侧重精细的文本分析:“像是老导演在红氍毹上给演出者一出一出地说戏,让人们‘看’到舞台上角色的来往冲突,感觉到生、旦、净、末如在目前。”因此,董先生说“《西厢五剧》被锦绣而内藏雷电,才令人屡读不厌,累演不衰”,而陈平原先生则说:“读董每戡的《五大名剧论》,也时常有“被锦绣而内藏雷电”的感觉。”(陈平原《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3期)
《文集》第一、二卷的《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和《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就颇能体现黄天骥先生对董先生学问的传承。有两个例子最可资说明。其一是关于《西厢记》中“张生为什么跳墙”的讨论。为何在戏里,莺莺的情诗明明白白地写了“迎风户半开”,张生还是傻乎乎地来一番“跳墙”赴约呢?因为围绕这一戏剧情节的处理,不仅有助于塑造张生、 莺莺、红娘三个人物的性格,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渲染剧本的喜剧色彩,使它呈现出与其他崔、张故事不同的特质。此外,在舞台与剧场的环境下,从戏剧叙事、戏剧张力的角度,再品味诸如张生的出场、吊场方式、“赖婚”中的敬酒等诸多细微之处时,也觉搔着了痒处,赋予了原本没有生命的文字以全新的意义。
而与分析“张生为什么跳墙”异曲同工的是分析《牡丹亭》里“怎生叫做吃饭”。本来,小姐起床,要吃早饭,看似与戏剧情节的发展无关紧要,但是,汤显祖却不惜好几次提及,而且不惜通过后台发声、停顿,特别是通过舞台调度,让春香做出跑上跑下的举动,无非是要引起观众对吃饭这一细节的注意;在特定的情境下,观众自然听得懂其中意味。接下来的一段对白,则更具意味:
(旦) 你说为人在世,怎生叫做吃饭?
(贴)一日三餐。
(旦)咳!甚瓯儿气力与擎拳!生生的了前件。
诚如汤显祖非常服膺的李卓吾所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答邓石阳》)他的《贵生书院说》认为人之所以贵,在于生,在于人活着,生存着,发展着,就是人的天性;穿衣吃饭,是人的本能需要;情与欲,也属于人的本能需要,均属于“生”亦即天性,与李卓吾的观念可谓一脉相承。“怎生叫做吃饭?”这一向来为人所忽视的细节,实在是当时思想舆论界都很关心的问题,明代的观众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分析至此,黄天骥先生再回到舞台上来:“如果在舞台演出的时候,当演员说出‘为人在世,怎生叫做吃饭’的道白之后,加上一记小锣,让观众抖然一振,恐怕更能强化这一提问的效果。”特别是在处于明代“人伦物理”问题激烈争论,具有异端思想的李卓吾备受打压之际,许多观众是明白杜丽娘这一句道白话里有话,振聋发聩的。从对爱情的追求延展到对人性的追求,引导观众进入哲理的思考而言,堪称《牡丹亭》的新创造,也是它“几令《西厢》减价”的重要原因。
中山大学戏曲学科的一个突出优势是,同时拥有王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两种研究路数的大家,陈平原教授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九章《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已论之甚详。陈平原教授进而更强调了“黄天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其同时接受两位前辈的衣钵,兼及文献与舞台,融考证史料与鉴赏体会于一炉”,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使得中大的戏曲学研究不限于一家,而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三
建国初期,中大中文系“五大名师”——容庚、商承祚、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蜚声学界,黄天骥教授均受亲炙,容、商二老古文字学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周易辨原》一书;黄先生诗词创作和研究方面的造诣,则主要得之于詹安泰先生,体现于第九卷《方圆集》——旧体诗词以及碑版文字的合集。黄修己教授说黄天骥教授以浅近文言写就的碑版文字堪称绝学,又说:“天骥先生的创作才华、古文功底,不表现在这上头,他的诗词成就更高。”确实,诗词创作更是先生的本色当行,而尤以歌行体为擅,而最大的特点,窃以为当在其乐章性。歌行体本以音乐性和叙事性见长,黄天骥教授在创作中更将其像一部完整的乐曲或一部交响诗来经营布置。开篇常常以顶真的手法推进,就像交响曲第一乐章快板乐章。随后转入慢板式的铺叙,同时用每四句一转韵,每韵咏写不同事项,以增强韵律的节奏感和叙事的情节感。结尾再以顶真手法,同时变长句为短句,有似交响曲终曲快板或急板的效果,如《秋泳曲》的结句:“灯火阑干海印桥,宛如弯弓射大雕;射大雕,兴未消,归来尚觉江流转,仰看明月自逍遥。”
黄天骥教授诗喜歌行、组诗,词则喜欢组词、长调,且每每致敬前贤。像《金缕曲》可以窥见纳兰词踪。《蝶恋花·羊城十二月咏》则致意清初词坛“最为大雅”的名家曹贞吉,而在艺术上或有过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黄天骥教授长期从事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在诗词创作上有强烈的时代文体意识。认为现代人写旧体诗词,即便写得“置之古人集中不能辨”,仍不能算十分成功,至少不能代表创新和发展,也不利于旧体诗词的阅读和传播。所以,先生之诗词,几乎不用典,也几乎不用传统的典雅熟词,同时又非常注意遣词炼意,自铸伟词,自成风格。
四
因为戏曲研究与诗词研究及创作各具造诣,所以黄天骥教授能“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其实这殊非易事。陈平原先生对此有特别的观察与评价。认为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及吴梅《顾曲麈谈》问世,“中国戏曲史”逐渐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吸引了国内外很多专家,这样一来,便很少有学者同时研究“唐诗宋词”与“元明清戏曲”,即便这么做,成功的几率也不高,而黄天骥教授却是诗词与戏曲互参,而且真正“打通了,事半功倍”(陈平原《南国学人的志趣和情怀》,《羊城晚报》2015年12月1日)。这种“事半功倍”的精彩呈现,在《文集》中所在多是。比如说《牡丹亭》在创作上追求“意、趣、神、色”,自有其本色与当色之处,历代也搬演不绝,但也一直有嫌其偏于案头化,不易理解,表演上也常呈滞涩,原因乃在于人们很难理解和表达其“意”之“象外之象”与深刻哲理意味——“如果说,《西厢记》是诗剧,重点在‘剧’,是情节、人物、语言像诗那样优美;那么,我认为,《牡丹亭》可以称之为剧诗。从整体构思而言,它是剧,更是诗,是故事内容贯串诗意的作品。”正因为是“剧诗”,是“以意为主”,因此,其间的谐律与否等等,才成为枝节,汤显祖自己也在所不顾:“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成句矣!”(《答吕姜山》)在给吕姜山的一封回信中,他更是直接怼回改动他剧作以便演出的沈璟:“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见王骥德《曲律》)
但是,黄天骥教授又要求必须能回复到“以文学的眼光来看文学、以戏剧的眼光来看戏剧”;《文集》第一卷《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就是通过关注《西厢记》的文学本质与戏剧本质,最终说明《西厢记》的文学意义与戏剧意义。《西厢记》不仅是个文学文本,还是个戏剧文本,是要拿到场上表演的。因此,除了文学的眼光,还要再加以戏剧的眼光,才能凸显《西厢记》作为戏剧文本而不是诗歌或小说文本的独特面貌。黄天骥教授的诗词创作造诣,也有助于他对古人的文学创作有同情之理解,从而可以在考证与文献积累之外,有透辟的眼光,具通识,善裁断,最终从筋节窍髓中探得作品的七情生动之微。
自觉的舞台感、动作感与画面感,使黄天骥教授不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而是用观众观看的角度在审察古人的戏剧创作。在舞台与剧场的环境下,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之间的暗流涌动,究竟该如何展示?围绕这一思路,自然能看出许多新问题。
黄天骥教授的学术承传与开拓新探,也有其时代的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戏剧学科建制的原因,分属大学中文系及艺术院校,戏剧研究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格局。艺术院校注重场上表演研究;文本的研究以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为主。“先师王季思先生教会了我如何对古代戏曲作考证校注的工作;而先师董每戡先生教会了我怎么看戏、编导。”由于师承关系,黄天骥教授在较早的时候,已经开始关注戏曲这一体裁的特殊性,注重从表演来看戏剧。从《张生为什么跳墙》到《长生殿的意境》《闹热的牡丹亭》等论文看,他一直致力于突破一般从中文系出身的学人对传统戏剧研究路数的局限,即使讨论剧本,也注意时刻把它放在舞台的背景下,从而揭示中国戏剧所独有的美学标准和创作特征。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学人,黄天骥教授对自己的传承和桥梁角色颇具自觉性,而且在此过程中致力于团队建设,则深具时代性。尤其是戏曲研究方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个团队形成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剧形态等各个分支,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对此,陈平原教授评论道:黄天骥老师这话“说得低调,但很到位;作为‘不见外’的‘外人’,我可以补充一句:放眼国内外,眼下没有比中大更强大的戏曲学研究团队”。这正充分彰显了黄天骥教授“这座桥梁”的作用、意义,以及对我们当下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