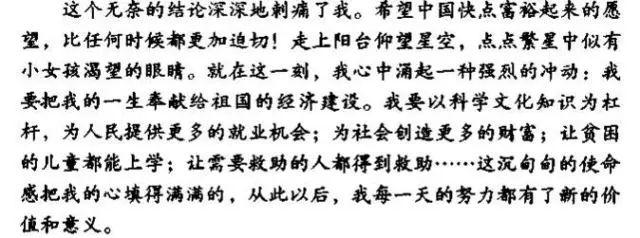文/郭晔旻

归顺朝廷的海商家族"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康熙三十八年,清圣祖玄烨题郑成功挽联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十七年的时间。在把朝廷的水师打得"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之后,郑芝龙正式接受了明朝廷的招抚,就任五虎游击将军,坐镇闽海。此时,他所拥有的海船竟然多达1000艘,部众三万余人。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们一样,接受招安后的郑芝龙的任务就是清剿他过去的同行,几年之内,他相继消灭李魁奇、杨禄杨策兄弟、诸采老、钟斌等海上势力,又统领舟师击败侵扰福建沿海的荷兰舰队,荷兰舰船"自是不敢入闽境",令满朝文武对其刮目相看。崇祯八年(1640年)郑芝龙最终灭了最后的敌手刘香。"刘香既杀……海上从此太平,往来各国节飞黄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第二年郑芝龙以五虎游击升副总兵加一级。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朝廷又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兼都督同知;后又升迁至南安伯、平虏候、平国公。福建巡抚上书为他表功"芝龙果建奇功,虏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
这时的郑芝龙利用他在福建的地位,垄断海上贸易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走私集团,已成为富甲全闽的第一号人物,从闽南沿海发出的商船,绝大多数是郑氏产业。他利用权势私自收进出口税,凡是经由福建地区的商船,必须缴纳白银三千两,购买郑氏符令,才能畅通无阻,否则便寸步难行。当然这位精明的海商也知道独自闷声大发财是不好的,郑芝龙不择手段地利用海外奇珍异物,贿赂明朝廷和福建省地方高官,以巩固他在福建的地位。
有了财富,自然还要享受生活。郑芝龙在离泉州四十里的安平镇(晋江安海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贸易基地,盖起高大奢华的宅院,亭榭楼台,雕栏玉砌,十分华丽。他还别出心裁,挖通海道,使海船可以直接驶入宅院,停泊在他的卧室门口。安平镇的守军旗帜鲜明,甲戈坚利,是他的私人武装,军饷由他自己开销。安平镇上商店林立,都是郑氏产业。郑芝龙建立起许多商行,还在京师(北京)、山东、苏州、杭州等地设有五大商行。
也是在接受招安过上安稳日子之后,1630年郑芝龙派人从日本接回了宝贝儿子郑森(幼名福松,即郑成功)。早年郑芝龙落魄时,大约在天启二年(1622年),离开澳门,到达日本平户。他初到日本,为人缝衣糊口(一说卖鞋为业),十分贫穷,后来娶肥前平户岛主田川七左卫门之女田川氏为妻。田川七左卫门原系福建泉州人,汉名翁翌皇,在日本经商已久,与一日本女子田川氏结婚,改用日本姓,称田川翌皇。郑芝龙与田川氏婚后一年,于1624年7月14日在平户千里滨生下一子,起名福松。一些书上记载,田川氏生产之时,梦见大鱼入腹,街坊四邻亦见他家火光达天,都前来称贺,道"令郎日后必定大贵。"有的书上还称田川氏生产之时在海边拾贝,仓促之间将郑成功生于一块石头上,平户至今还有所谓的"郑成功儿诞石"遗迹,立于平户河内浦千里滨的海滩,石高约80厘米,宽3米。1629年田川氏又产下次子田川七左卫门(从母姓,袭其外祖父之名)。

郑芝龙离开日本后,郑成功一直与同母弟七左卫门跟随母亲翁氏住在日本。他从小学习武艺,十分刻苦,其二刀剑术即学习于平户藩士。郑芝龙曾多次派人去接他们,都遭到日本德川幕府的拒绝。直到郑成功七岁那年(1630年),郑芝龙派人到日本活动,买通了德川幕府官吏,日本当局才同意放郑成功回国,却又以向无日女入中原之例为借口强留田川氏。于是,郑成功只能忍痛拜别母亲,独自回到中国。传说他在离开日本前,曾手植椎树,后来,这些树长成古树盘结苍郁,成为"松浦心月"的胜景。
郑成功回国后,郑芝龙为他改名森、字明俨,花重金为他聘名师授课。郑氏门第低微,郑芝龙本人又有当海盗的不光彩经历,虽已富甲全闽,成为福建地区的军事长官,但当地衣冠世族却看不起他,私下称之为"贼",不屑于与他往来。因此,郑芝龙希望儿子郑成功能跻身士流,附庸望族。
郑成功也十分为老爸争气。他从小才思敏捷,十一岁时,老师曾以"洒扫应对进退"为题命他作文。他在文章中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意境开豁、新奇,使老师十分惊诧。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成功二十一岁时,进入南京国子监,成为太学生。他拜在当时著名学者钱谦益门下,学习儒家经典。钱谦益十分器重他,为他取字大木。当时的名家对郑成功的诗很欣赏,钱谦益赞赏曰:"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当时的应天府丞瞿式耜更是独具慧眼,从郑成功的诗中看出这个年轻人"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
权倾东南的“福建王”同样是在崇祯十七年,甲申国变,明朝灭亡。明朝镇守山海关的将军吴三桂勾结满清贵族入关,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留都的明朝官员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朝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率清军攻入南京,短暂的弘光政权宣告灭亡。江山易主,山河破碎,不久前才离开南京的郑成功(时年二十一岁)目睹如此悲惨景象,心情万分悲痛。但他的老爸郑芝龙此时却很开心,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方面,郑芝龙的日本妻子暨郑成功的生母田川氏终于来到福建与家人团聚。母子相见,悲喜交集,这对于刚从南京战乱下返回家乡,痛感亡国之苦的郑成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郑芝龙早年回福建后一直与田川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年有商船来长崎","书简数通"。他多次派人与日本幕府当局交涉,日方一直不肯放行。到了1645年,郑芝龙遣黄征明带函件与礼品往日本,有一书简"为芝龙书其妻子之事,请求日本之小女十人,奴隶十人,又其小子思母之事,在唐国思念不置。"这时的郑芝龙已经被南明弘光政权封为南安伯,田川氏(翁氏)也被封为国夫人,幕府当局才同意放遣,但又强行留下了次子七左卫门。田川氏没有办法,在来华前对七左卫门说,“良人及汝兄(指芝龙和成功)数欲相迎,然我怜汝幼,辞之数矣。今汝稍长而不往,恐使汝失父兄之俱,令止汝于此,我将从其请诣彼地,请良人托每岁来舶赠银以为资给"。
就这样,郑成功的胞弟七左卫门一直侨居日本,娶妻生四子,长子名道顺,复改称姓郑,"居于平户,每年由兄成功寄赠生活费,成功薨,其子经仍资给不辍"。郑道顺亦欲回国抗清复仇,有郑道顺诉状一书,事不成,父七左卫门殁。日本正德年间(1711-1715年),郑道顺迁到"江户,住吴服街,以医为业,不仕而终",但郑芝龙的这一支血脉一直在日本延续了下来。1986年,当时的平户市市长油屋亮太郎正式确认:住在橫滨市绿区鸭居的福住邦夫(当年六十岁)乃是七左卫门的第十二代孙。福住先生是原法政大学教授郑审一(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去世)的次男,在昭和三十年(1955年)时才改为福住姓的。10月25日,日本一报纸详细登载了这一报道。报道说:"郑成功和七左卫门均是十七世纪时中国的郑芝龙和日本的田川氏所生的。郑成功七岁回到了中国,为明朝的复兴尽了大力,而七左卫门却留在日本。"
另一方面,郑芝龙像战国时代的吕不韦一样拣到了一件"奇货"。弘光政权灭亡以后,南明势力发生内讧。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明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控制浙江东部地区。郑芝龙的兄弟镇江总兵郑鸿逵与户部郎中苏观生则一道拥立唐王朱聿键,一行人入闽后,南安伯郑芝龙、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共同挟立唐王为帝,建都福州,建元隆武。
虽然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地的文武官员听到唐王隆武政权建立的消息,纷纷上表称臣,表示拥戴,令隆武政权成为名义上正统的第二个南明政权。但朱聿键本人并没有自己的班底,加上名分不足(他是朱元璋第22子的8代孙,血缘距离崇祯帝非常远),因此不能不依赖拥立自己的福建实权人物。在拥唐群臣中,最有实力的还是郑氏家族,当时"兵食大事,俱仰给郑芝龙;隆武虽拥空名,实为寄生",他们不仅为唐王的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经费,而且还有一支相当能打仗的军队。这在当时虏骑南下的情况下当然十分重要。张肯堂虽为福建巡抚,但福建的财政一向是赤字连年,张肯堂镇压四处发动的山寇也主要是依靠郑芝龙的私人军队。福建的地方行政方面也已经被郑芝龙控制。
因此,隆武帝即位后就以拥戴之功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后来更封郑芝龙为平国公,郑鸿逵为定国公,毕恭毕敬地尊他们为太师,郑氏"一门勋望,声焰赫然"。当时的郑芝龙实际上是明朝末年中国海商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与郑鸿逵等人进入南明隆武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海商集团进入帝国的统治中枢,并发挥重要作用。这年八月,郑芝龙带领郑成功朝见唐王,唐王为了笼络郑芝龙,又见郑成功少年英俊,十分器重,说:"可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明朝"。当即封郑成功为忠孝伯,赐姓朱,给他改名为朱成功。能够被赐予皇帝的姓,是特殊的恩典。从此,国内外许多人都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叛明降清成人质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攻克钱塘江防线,朱以海逃往海上,鲁王政权灭亡。偏安福建的唐王政权也唇亡齿寒,直接暴露于清军面前。七月,清军大举进攻福建,直逼闽浙交界的军事重镇仙霞关。
本来,福建地区的崇山峻岭,是十分理想的天然屏障。来自北方的清军不耐酷暑,不惯海战。郑芝龙手下有精锐的水师,坚利的战船,他据险而守,扬长避短,以水师迎战是能够有效阻击清军的。但是,郑芝龙拥立唐王不过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政治投机,作为海商,他与明朝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买卖的关系,明朝授予他高官,而他为明朝平定东南海疆,并从中谋利,获得巨额财富。朱聿键的意向是以恢复明室为己任,具体目标是首先恢复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他称之为 "半功"),进而收复北方(他称之为"全功");郑芝龙对此却全然没有兴趣,他的目的只是以迎立隆武帝作为定策勋臣第一,借隆武朝廷的名义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区唯我独尊的地位。长期来他在福建、广东购置了仓庄五百所,田产数万顷,房产不计其数。现在,清大军压境,他开始感到不能再抱住脆弱的唐王政权而放弃如此庞大的私产,更不愿离开他安乐的老巢,再过漂泊不定的海上生活。
与此同时,清军也适时展开了对郑芝龙的劝降活动。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清廷密遣使者与郑芝龙取得联系,为清朝招抚福建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和御史黄熙胤,都是福建晋江人,与郑芝龙同为泉州府人。洪承畴就以闽南同乡的身份,经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同意,写信给他,"许以破闽为王"。这正中郑芝龙下怀,他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看重自己。他在与儿子郑成功的对话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于是郑芝龙派人与清军联络,写信给清军统帅,声称决心"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贵朝非一日也",准备降清。唐王见郑芝龙如此,只好暗自垂泪。
但是郑成功与其父的想法大相径庭。有一次,郑成功进宫去见唐王,见朱聿键两眼通红,十分愁苦,便下跪道:"陛下郁郁不乐,不是因为臣父有异志吧!臣受国恩,义无反顾,定以死报效陛下。"说罢,郑成功献上他精思熟虑的《抗清条陈》、《延平条陈》),其中列有“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等具体措施。以今天之眼光看,郑成功的军事战略明显属于海洋性的,而非大陆性的。这也是郑成功日后举兵之大战略。其核心是以海外贸易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支撑其军事力量。这与大航海时代西方海洋国家、海洋社会的军事原则完全一致。
朱聿键既对郑成功的条陈十分欣赏,更为他的耿耿忠心所感动,转忧为喜,立即下令封郑成功为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剑,仪同驸马,挂招讨大将军印,前往镇守仙霞关。

仙霞关是浙、赣、闽三省交界的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郑成功扼险而守,以逸待劳,形势有利。清兵压境而来,郑芝龙却派心腹到仙霞关,授意郑成功撤回。郑成功一见到郑芝龙的使者便厉声喝道:"敌师已迫,守军粮饷不济,速请太师发饷济军。"使者不敢多说,立即回报郑芝龙,"若提及投降之事,此头已掉矣。"郑芝龙十分恼怒地说:"痴儿如此固执,我不发粮,他能空腹出战吗?"果然,郑成功多次派人请求发饷,郑芝龙都不予理睬。在饥饿的驱迫下,仙霞关守军全线瓦解,郑成功不得已,只好退回福州。八月,清军越过仙霞关,长驱直入。郑芝龙竟撇下唐王,匆匆率兵退回泉州。唐王失去依靠,没有办法,只好率领少数从人出奔江西,行至汀州被清军抓获,绝食而死。唐王政权灭亡。
九月,清军进抵泉州。博洛亲自写信给郑芝龙"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郑芝龙满心欢喜前往面见博洛,当晚便剃发留辫,换上满族装束。谁知,欢饮三日之后,博洛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并命郑芝龙随军北上,郑芝龙心知中计,但已是"神龙失势,与蚯蚓同",无可挽回了。更不幸的是郑芝龙投降清朝之后,他的家属满以为已成了大清的顺民,投降有功,不会遭受清军的伤害,因此也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清军突然开到郑芝龙的老巢安平镇,大肆烧杀抢掠。郑芝龙的兄弟眷属只得慌忙乘船逃命。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不及逃出,恐遭侮辱,自杀而死,年仅四十五岁。

郑芝龙降清之后,他的水陆大军全部瓦解。郑鸿逵率领一部分亲兵逃往金门附近。郑彩、郑联拥戴从浙江南逃的鲁王,占据金门、厦门。陈豹占据广东、福建交界的军事重地南澳。其他文武官员也散处各地,互不统属。博洛满以为,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听。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并将其送往北京软禁。
结果他大错特错了。清军偷袭安平时,郑成功人在金门。生母田川氏惨死的消息传来,郑成功悲愤交集,失声痛哭。他换上孝服,火速赶回安平,埋葬母亲。国破家亡的惨状激起了复仇的怒火,郑成功来到泉州的孔庙里,跪在孔子像前,默默地摘掉头上的儒生方巾,脱下身上的儒衫,将方巾和儒衫放火烧掉,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行礼,泣不成声地祝告说:"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说罢,换上铠甲,佩上宝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清的武装斗争道路。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郑成功怀着满腔的愤怒与悲哀,率领十几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来到同安附近的烈屿,召集抗清队伍。不久,唐王被清军杀害的消息传来,郑成功十分悲痛,当即自称:"招讨大将军",誓师起兵。他与从人身穿孝服,向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跪拜行礼,庄严宣誓说:"本藩是大明臣子,缟素报仇乃是分内之事。现在国难当头,请诸英杰与本藩共申民族大义!"为了表示与清朝势不两立,他仍然沿用隆武年号,号召抗清。

第二年(1647年)正月,郑成功到厦门附近的鼓浪屿募兵,百姓纷纷前来投效,不几天便集聚了几百人。这时,恰好有郑家的商船从日本开来,押运货物的是郑家的两个老仆。郑成功将两个仆人找来,问道:“有多少资财?”老仆答道:“近十万。”郑成功说:“拿来供军需使用吧”"。老仆说:“没有主母的命令,森舍(当时福建地区称公子为舍)怎敢擅自动用呢?”郑成功厉声呵道:“你们视我为主母何人?居然敢违抗我。”说着便拔出宝剑,杀死两个仆人,把船上的资财全部充作军饷。不久,郑成功已招募到几千人。他将部队分为左、右先锋镇、亲丁镇、左、右护镇、楼船镇,毎镇都派遣得力的将官统率,又设置了参军、总协理等官,分管军政事务。人们看到郑成功年轻有为,文才武略远远高出于郑芝龙的其他兄弟子侄,便都渐渐集合到他的麾下来。
到顺治六年(1649年),福建漳州、泉州沿海地区与广东潮州所属的一些地方,都被郑成功收复了。为了统一郑氏集团,他又击败了占领金门、厦门,与他势力相当的郑彩、郑联兄弟。金、厦两岛四面环海,可攻可守,清军不易来犯。从此,郑成功得到比较稳定的立足点。此后,郑成功一直以厦门为中心活动,加强军政建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他手下部队已发展到四万多人。他又整编了军队,设立五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中军)。在郑成功经营下,厦门人烟稠密,店铺林立,商贾往来,成为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城市。
为了寻求外界对自己抗清的支持,郑成功还利用自己与日本的渊源(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向德川幕府借兵。其实,早在1645年,郑芝龙就曾致书江户,“伏望念平素交通之谊,乞借劲旅三千”;第二年还派人带去了隆武帝的国书,德川幕府的“御三家”(水户、纪伊、尾张藩)都主张出兵,但为执政的大老井伊直孝拒绝。1647年,郑成功又一次派人送信到长崎,声言“成功故生于贵国,深慕贵国之风,今也时际艰难,贵国定应怜我,乞假以兵数万,使得复君父之仇”,其胞弟七左卫门闻知母亲惨死的消息,也“诣江户,请赴明戮力成功,灭清报仇”。江户幕府虽然终究未能出兵,但郑成功起兵抗清仍给日本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江户幕府中期的著名歌舞伎脚本、净琉璃唱词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年),在1715年创作的著名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即是以郑成功抗清复明、攻打南京城为背景写成,获得空前成功,这出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20余万人次。
枭雄末路郑芝龙被杀郑成功起兵反清之后,郑芝龙在北京的日子自然一天比一天不好过了。表面上,他先被编入汉军正黄旗,再转镶红旗,赐三等子爵,再晋封同安伯,清廷赐了一座四合院给他居住,并且给他很高的俸禄。但是实际上自由是没有的,郑芝龙就是清廷用来挟持郑氏家族的人质。
这当然不是全然没有效果的,顺治七年(1650年)闰十一月,郑成功率兵南下,准备与拥戴永历帝的李定国、孙可望部队会师,而留族叔郑芝莞守厦门。结果,郑成功勤王兵马出师之后,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乘郑成功后方空虚,命马得功率泉州守军,王邦俊率漳州守军,两路夹攻,直逼厦门,并强追澄济伯郑芝豹派遣船队运兵。郑芝豹因郑芝龙被拘在北京,不敢拒绝,只好从命。留守厦门的郑芝莞听到敌军逼近的消息,将自己的珍宝钱财搬上船,弃城逃走。厦门百姓见清军兵临城下,守军不战而退,纷纷四散逃命。郑芝莞弃城登船逃走,郑军不战而溃。清军攻入厦门。郑成功储存的几十万斤大米,九十万两黄金被掳劫一空。

张学圣以厦门地形四周濒海,难以防守救应,立即指挥军队撤退,但已经晚了一步。奉郑成功命回来协助守城的郑鸿逵赶到厦门。他命令猛将施郎(后改名施琅)出战,令清军陷于绝境。马得功只好亲自乞请他从前的上司郑鸿逵,并以郑芝龙和在安平的眷口相要挟,迫使郑鸿逵以渔船渡运,才得以返回泉州。这令郑成功十分无奈,“助虏前来的是澄济叔(郑芝豹),渡虏逃命的是定国叔(郑鸿逵),弃城与敌的是芝莞叔,家门出此助虏为虐之人,才造成这次的失利。”
这时,清朝为了迅速平息全国的抗清高潮,向西南山区派遣重兵,大力征剿永历政权。而对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则采用围剿和招抚两手政策,企图使他就范。但郑成功本人根本不相信清朝的诚意,“朝廷既失信于父亲,儿又安敢相信父亲之言“。顺治十一年(1654年)九月,清廷甚至派郑芝龙次子郑渡、四子郑荫去见郑成功,希望通过手足之情动摇郑成功的决心。
郑渡一见郑成功便泪如雨下,跪下恳求道:“父亲在北京多方斡旋,才有今日议和之事。此番哥哥不归附,全家难以保全,请你勉强接受诏书吧”。郑成功严肃地说:”你年纪轻,还不知人情世故,自古改朝换代,降者多无好结局。父亲已误于前,我怎能重蹈于后呢?我一日不受诏,父亲在清廷尚可无恙。设我勉强受诏,削发称臣,父子兄弟前途俱难预料。勿须多言”,不准他们再提招降之事。
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相攻陷福建漳州、同安、仙游等地,清廷一片哗然。眼看招抚不成,顺治帝恼羞成怒,已被软禁在北京多年的郑芝龙不仅爵位被夺,且被囚于高墙之内。这一年,郑芝龙原部下黄梧降清后,向闽浙总督李率泰进言,以为"成功父子残害生灵,实戾气所钟",于是福建南安石井的郑氏祖坟被清兵竞相破坏,其中包括郑成功的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三代直系祖先。对于中国人而言,祖坟被掘、龙脉被断是再忌讳不过的事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兵到达台湾,清廷已鞭长莫及。为了报复,九月二十四日,清廷以郑芝龙“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其子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奸细往来、泄漏军机等项事情,经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审各款俱实”为由于十月初三日诛杀了已拘禁七年之久的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翌年正月,噩耗传到台湾。郑成功望北而哭:"若听儿言,何至杀身!然得以苟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