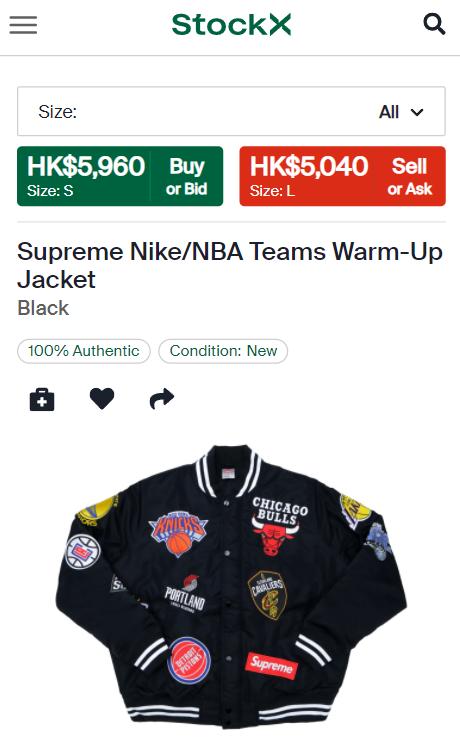“从夏磨到秋,家人终于答应过完生日就放我出家”
“还记得那天早晨4点多,爸妈没有装睡,起来煮了饺子”
……
每个接触佛学、最后选择佛教作为宗教信仰归宿的佛教徒,都应有过或长、或短、或简单或复杂的过程。
妙一法师在文章《一路向南二十年》中,从学佛因缘、出家因缘和求学因缘三个方面,讲述了自己的修学经历。
读完这篇文章,很多人都不禁泪目。

一路向南二十年
致那些想得起与回不去的时光
文/妙一法师
2010年1月4日,在当时法源寺观音殿东耳房写过一篇《十年回眸》。
2020年12月,再次写了这篇《一路向南二十年》。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过往很执着的人。
但回想2000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二十三,从夏磨到秋,家人终于答应过完生日就放我出家,激动的心情,至此20年后,仍旧激动不已,眼泛泪花……
出家后,被人屡屡问起学佛、出家、求学三个因缘,下面就回忆一下,权当是纪念过去的时光吧!

我的学佛因缘
每个接触佛教、最后选择佛教作为宗教信仰归宿的佛教徒,都应有过或长、或短、或简单或复杂的过程。
而我就属于那种特别简单的那种,以至于始终没人愿意相信。
1990年,我6岁,是能看得懂《西游记》的年龄,虽然觉得孙悟空很厉害,但还是觉得唐僧更让人向往。
向往到什么程度?我会从窗子上卸下窗帘,披在身上,装模作样地盘腿闭目,口中若有所念模仿起来的样子。大人们见到也只是笑一笑,嗔怪地说“不要把东西弄脏”。
后来遇到很多80后出家法师,大家谈到出家因缘时,大多数人认识佛教(或和尚),都是受到《西游记》的影响。而实际原因,则是那会的佛教,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除了童心的好奇和顽皮,还有住在隔壁的奶奶家。
她每天早晚都要烧一炷香。老人家只是烧香,不念佛、只过年拜祖先时,才顺带磕三个头。
我看着奶奶烧香,就特别激动。园子里种的花,开了就会揪几朵放到菩萨面前,没有什么动机,就是喜欢。

7岁上了小学,经常会“丢东西”。三天两头地就把铅笔或者橡皮擦用完。然后就正大光明地跟妈妈要2毛钱,去买文具。
因为经常“丢东西”,又不见东西没,后来被大人发现——我是把钱拿去买香了,而不是买糖或玩具。
那会村子里的小卖部,一盒香是2元钱,里面有10小袋,可以分着卖。
还经历好多有惊无险的事,比如挖野菜走丢了,体弱多病,几次差点死了又活了。
就这样,慢慢地度过了小学,对佛菩萨的情感也慢慢变得熟悉和坚定。
在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听说村子里东头有两夫妻学佛,家里没小孩,就主动跑到他们家,跟着学念佛。从此认识了好多邻村学佛的在家居士,他们会在佛菩萨圣诞日聚会,在一起念经、上供。
上了初中,每天要骑自行车6公里去镇里的中学上课,家里每天给2元钱作为午饭钱。
为了攒去县城寺院的路费,每天中午只用1.5元。盒饭是1元钱,再买5毛钱的地瓜(番薯)留着要回家时填肚子。或者有的时候只用1元钱。
后来想想,自己个子长得矮,非得要找个理由的话,跟那3年不规律的生活有很大关系。当然,这是家里人不知道的。

因为是骑自行车上学往返,去的时候就会默背大悲咒6遍,回来的时候念阿弥陀佛。
1997年冬天寒假,怀揣着攒了一个学期不到50元的路费,跟着村里的居士们到了县城东门观音寺(女众道场),正式皈依,有了法名,成为一名佛教徒。
一个人接触佛教,乃至最终成为佛教徒的因缘,是绝然不尽相同的。
在东北出生、长大的我,见惯了因久病不愈、大仙算命而接触佛教的例子。但,这正是因为佛教的包容性和社会形象所折射的众生相。不需要去批判和纠正因缘和动机,因为所有正在发生的事物都是无常的。所有美好不是最开始就被定义的,而是被过程赋予的。
我的出家因缘
关于出家因缘,更是被绝大多数人拿来问的一个问题。我从16岁开始,被人足足问到现在。这或许就是世人好奇心的一个焦点吧!
1997年皈依以后,我认识了更多资深的佛教徒,假期跟着他们到处去参加法会。
因为我识字,又会唱,重要的是听话,大家都爱带着我赶法会,自然路费也就不用出了。
就这样,只要一放假,我就跑到庙里去。
女众道场是不能有男居士常住的,我因为年龄小,长的又小,勉强住在接待信众的客堂,白天写文书,晚上就可以把床支上休息。
但吃饭是要付钱的,每餐1元钱。寺院有十来位半路出家的老尼师,她们很喜欢我,给我水果,也不用我交餐费。我跟典座师父说,现在的饭钱先欠着,等以后有了肯定多还。
直到2003年秋天,我在哈尔滨极乐寺读书,遇到了一位观音寺的师父,请她将500元带回寺院,并指定她要放到斋堂的功德箱。

那时,父母总是觉得孩子学佛是好事,可以保佑学习好,就没怎么阻拦我接触佛教。
寒暑假在寺院的我,看到很多新人来到寺院剃发出家好羡慕。而且听说可以去佛学院读书,那更是向往。
回到学校上课,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答非所问,下来看到我笔记本写满了“阿弥陀佛”,老师不知所措地叫我坐下了。
班主任对我很好,当时也不理解我为啥出家。20年后,我们在南京机场不期而遇,她们现在已经理解,在2年前皈依,做了我的在家徒弟。
中考结束,我的成绩并不好,偏科太厉害,数理化基本不及格,语文、历史、地理倒是出奇的好。
一个整天想着怎么学佛、背功课、跑寺院、赶法会的学生,是不能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成绩的。
既然没考上好高中,索性就跟家里提出说:出家!
想想都知道了,家人不会同意的,哪怕绝食!
对于我出家这件事,父母(尤其是母亲)乃至村子里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赞成的。往前50年里,整个乡镇,十几个村,近十万人,都没有一个出家的——“这是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
我出家会让父母亲在亲戚中间、在村里蒙受了巨大的难堪——根本就没人理解,也没人愿意尝试理解。
夏天中考完,我就一直以各种方式、策略跟家长沟通。秋收完,实在在家里没意思,就央求说:让我去庙里试试,不行三五个月就回来,那会再要读书、当学徒都不晚。
到任何时候,真的爱你的人都不忍心难为你,他会放手的!尤其是父母。
就这样,家人答应过完生日,放我出家。
每次第二天要去寺院,我肯定提前醒。过完生日的第二天一早,我3点多就自然醒了,等着母亲起来做早餐,好赶路去隔壁省的松原龙华寺出家。
母亲故意不做声,她一整晚都没睡好,想着我平时都是要睡到7、8点才醒,只要还是那会醒,就赶不上一天一次的班车了。
那天早晨4点多,爸妈终于装睡不下去了,起来煮了饺子。吃完了,五叔(爸爸的五弟)赶着他家的毛驴车到了门口。
东北的冬天很冷,凌晨5点的时候,满天的星星,特别亮,那个点是没有人家烟囱冒烟的。
坐在毛驴车上,车轮碾过雪地,吱呀吱呀,慢慢我的身影模糊在母亲依偎目送的大门旁,而我却兴高采烈,无比期待,头也不回地奔向他们从来没接触过的远方。
直到自己年龄大了些,才明白当时母亲是有多难过!

毛驴车经过1个小时吱吱呀呀的前进,过了拉林河,到了花园大桥,我在寒风中等待每天仅有的一班客车。
8点钟,依稀的车从对面驶来,问我是要去松原吗?我回答售票员“是的!”
五叔见我上了车,他也安心回家了。
龙华寺太大了,有很多年龄相仿准备出家的净人,他们不叫名字,直接叫年龄,比如:小十四、小十五、小十六,因为有人跟我同年,我就叫“小十七”(虚岁),还有老九(十九)。
直到现在,见到十四,还是叫他“十四”,虽然他已经是国内著名佛学院的法师。
现在回到龙华寺,还有少数几位老师兄叫我“小十七”,亲切,温暖!仿佛被岁月定格。
最初在龙华寺的二个月,热闹、忙碌、紧张。有很多常住居士照顾我们,当然也要干活:拉柴火、烧火,做饭、行堂、跑腿、扒灰、烧水、洗菜、洗碗,还要背功课,每天晚上考,背不出要打手板。
当然,做了3年“老居士”的我,只是法器不会,功课在家早就背好了,从不挨打。

但总是有突然的意外发生。
记得刚进腊月的时候,天特别冷,我每天早晨要3点钟起床烧火,供一百多人的热水。那会是全年最冷的时候,零下30几度,室外搭建的烧火棚子特冷,我穿的又不够,脚底着凉,一直要去厕所小便,有一次一天整整去了28趟。还有些时候行堂到最后,剩的饭菜不够吃饱,只能吃点冻白菜蘸酱。
去年师父六十大寿,我回去拜寿时,师父说吃点忆苦思甜的东西,我说是“冻白菜吗?”
当时,虽然苦,也没觉得过不去。现在想来,苦也是乐,只是回不去了!
我的求学因缘
虽然出家20年了,实际在师父那里就住了10个月。
第二年(2001年)四月初八剃度了,是现在五磊寺首座静坤师兄代替师父剃的,法名是我自己起的。师父太忙了!
关于我的法名,四月初八是佛诞,那会在客堂当班,下午要交票据钱款。要签名,可是我还没有法名,虽然上午剃了头,换了衣服。
灵机一动,反正第一个字不能改了,以前有个静一师兄,没有人叫“妙一”,那么我就简单点,来一“横”。到了晚上师父查看票据,问:“谁是妙一呀?”,我说“我是!”
就这样,法名就叫“妙一”,现在的所有证件都是这个名字。曾一度觉得这个名字不是我,我也不是它,好陌生。可当别人一呼唤的时候,又是那么熟悉、自然。这或许就是熏习吧!

后来的参学过程中,我遇到了全国三个跟我重名的法师,其中一个在香港宝莲寺的戒场,因为名字相同,还闹过乌龙。
2001年6月,向师父提出去佛学院读书,师父老人家是传统的老修行,不同意去佛学院,说到那没人管,会学坏。(当然,老人家是没在佛学院待过,他从前的同参有从佛学院还俗的,对佛学院的印象自然不好。)
农历八月十五过后,跟着年龄长一点的师兄们从龙华寺出来了,没有熟悉的道场。只好去佳木斯佛光寺师叔那里,只要是从龙华寺去的师父,师叔都愿意留,因为功课好,不计较。
那是人生第一次做事收儭钱(供养金),在龙华寺每个月的单资是30元,基本都倒贴在客堂了,因为写错文疏要赔钱,那是浪费常住物。所有普佛,大家都不要儭钱,给也不要。
到了佛光寺,吃得好、住得好、还有儭钱,前几次都没要,给了以后直接放进功德箱。
后来老师兄说,你以后要出门的、要买生活用品的、还要受戒,这些都得自己攒。听了人劝,就接受了儭钱。
第二年(2002年)三月底跟十六师兄,带着2000元戒费,缝在衣服里,从佳木斯到哈尔滨盖章,再坐火车到了江西宝峰寺,后又辗转到了曲江南华寺受戒。
受戒后回到佳木斯,2003年春天在客堂看到闽南佛学院的招生简章,准备材料,报名。
到了夏天非典爆发,师叔不同意去读书,实则是因为庙里没人干活。说非典,南方死了很多人,去了就没命了,就作罢了!
七月十五哈尔滨极乐寺打水陆,请佛光寺的法师们去念《楞严经》,因为年轻又机灵,就被派去打水陆。
到了极乐寺,一看有佛学院呐!太激动了!就问:“我可以来吗?”教务长说:“可以啊!”我说:“我家方丈不同意,没手续怎么办?”他就说:“你先来吧!静波法师去年刚回来,他可是中国佛学院的法师,手续的事可以后补。”

就这样,水陆结束后,回佳木斯跟师叔说:“南方去不了,那北方总可以吧!我寒暑假还能回来做事。”
师叔算是同意了,而且保留了每个月50元的单资一年。
在极乐寺的两年学习,真正接触到了佛教的教理教义,开启了内心对佛法真理渴求的引擎。
很幸运一开始,就学习到了中观、三论,并不陌生。但记得一次期末考试,始终弄不明白“空”是啥意思!
那是个深秋,东北的深秋阳光是金色的,撒在宿舍,坐在床边,看着法师发的材料,反复琢磨,利用一上午的时间,终于明白法师说的“空”是啥意思,原来就是一种工具而已。当然,这只是当时的理解。“空”可不仅仅是工具,看你如何阐释了。
沾到了一点法喜,学习、用功的劲头就更大了。
记得二年以后(2005)毕业了,因为读书期间作值班维那,服务班级,口碑不错,院长留常住,我以继续考学为由没有答应。就这样2005年6月考入中国佛学院,直到2012年6月研究生毕业,在法源寺足足住了七年。
毕业后回到广东,住光孝寺。
四年之后,又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


有人说:读书使我快乐,读书使我充实。
我觉得:读书使我更加真实,更加坚定。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干啥像啥!即使做了和尚,也要做个出类拔萃的和尚。
僧人应以学修为尊严,学会接受缘起,包容差异。努力向涵容同辈、给人方便、不吝色、不虚荣的前辈们学习。任何时候,信仰是依靠。
过去的二十年里,妙一受过很多人的恩惠,他们有的往生了,有的老了,有的还在身边,有的数年不见一面……
我在他们那里获得的感动和富足,正在尽力地传递给需要和相信我的人,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某些能力的局限,但诚意从未打折。
人都有不足,这是掩盖缺陷的借口,也是直面问题的前提。过去无论怎样,留下的更多的是回忆,美好的回忆。

经常难以入睡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年秋天,阳光洒在窗子上,透过玻璃折射的光束,看到了舞动的微尘,那是一个个安静而丰富的世界,完整而又渺小……
谁人没有梦?一路向南行;
风雨二十年,风云步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