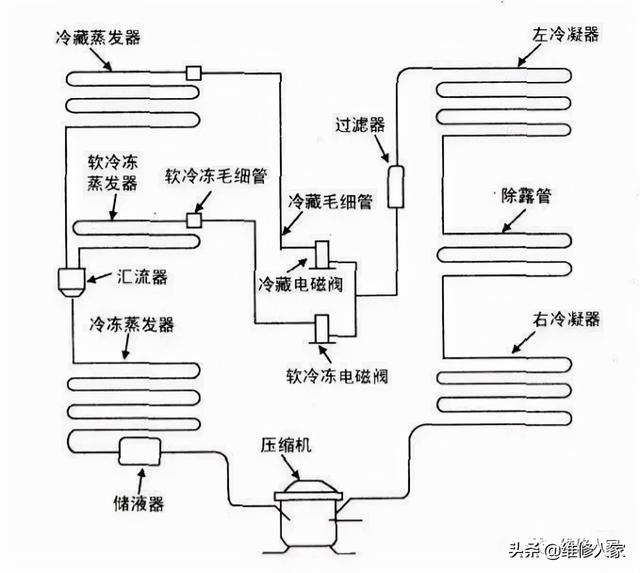今天,远近都知道乌镇的名气,却对相邻的新塍古镇知之不多。
殊不知,二三百年前,新塍的地位和影响与乌镇比一点也不逊色,不说农业、手工业的发达,也不说商业贸易的兴盛,单说人口,新塍“居者可万余家”(乌镇在民国时也仅4000多户)。
最有意思的是,外来人口迁入新塍特别多,明代“颇多儒人徙居”。清代因教书、避乱、经商等原因徙居新塍的更多,其中就有“郑官房”的郑氏。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世籍桐乡的郑氏(郑敬安)自桐乡乌镇徙居新塍问松坊,从此,新塍郑氏一门,诗书相传近二百年,并且代有名人。
新塍“郑官房”是新塍望族,是小镇的骄傲。今天,你走入小镇,说起“郑官房”,老一辈人都知道,随便说出一二个故事来。

如今,曾经风光新塍的“郑官房”,遗留下来的仅仅是书里和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眼前这幢已破旧了的屋子,据说那是“郑官房”的旧屋。
那天,钱家姑姑引我们沿市河去中北大街寻访的时候,住在那里的一位大妈,指给我们看一排旧房子,说就是这里了,但房子都塌得差不多了,但见一个暗黄的石门框依然坚固地嵌于旧墙里,一边的墙上书“贝贝托儿所”字样。那作为“郑官房”标志的清贻堂消失得无踪影。我们从侧面一个深深的小弄走进去,见一个瓦楞窗,望进去,是一个大天井,里面分明见得那门楣上的砖雕依稀,天井一侧很小的短墙上写着“好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字样。
作为托儿所的里屋,朝南的几间二层楼的厅屋,依然有整齐的门窗,但此刻门窗都关着,托儿所的孩子大概早已接回家了,园子里静静的。再走进去是第二进,也是二层楼,老枇杷树依然郁郁葱葱地发着亮光,热烈地长在断垣上,全然不顾物是人非的变幻。
我们很想找到郑氏后人来聊聊,可是当我们叩着一个虚掩着的侧门,却没人应答,轻轻推开,但见里面绿树红花开满小天井,主人不在,回应我们的是门上贴着的对联:“年年好运随春到,岁岁平安福自来”和“吉星高照”的横批,还有横批下大红的“文明家庭”的牌子……就只有这些了。寻访往往让人有太多的失落,回头只能从书里找到一些慰藉,为那些曾经的辉煌而空欢喜一场罢了。

先在新塍历史上留下光彩一笔的当是“郑官房”之清贻堂。
“郑官房”第一代郑熙(字敬安,号缉亭),早年游学,家贫课蒙学而自给,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乡试中举,后到直隶柏乡、宁晋、顺义等县任县令,皆有政声。特别是在任顺义县令时,着力堵塞县试之歪风,留下清名。
顺义县历来县试总将富家子弟置榜首,藉以索重礼而为学使供用,而府县首列之卷也为学使所必录。郑熙莅任,胥吏援惯例以请,郑听说后大怒曰:“此国家求贤之始,当凭文取士,且寒士苦况,我备尝之,夫岂可贪贿赂屈真才乎?吾子孙尚欲读书,焉肯造此罪孽?”胥吏不敢声。后又有郑信任之人进言,也不为动。从此县试关防加严,舞弊之风禁匿,所取者多为有真才实学之士,日后功名显达。
后来郑熙告老回到新塍,其门楣取名“清贻堂”,意为以清白贻后人。郑氏为官为人的高风亮节,真正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后郑熙之孙、曾孙辈,府县试名列榜首的也不乏其人。“郑官房”之清贻堂,以清白贻后人,至今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

为新塍写志记事,是“郑官房”郑氏的另一大突出贡献。新塍自清道光年间始有郑凤锵(1802~1863,郑敬安之孙)编著的《新塍镇志》14卷,仿照府志形式,详细记录了上下数百年新塍疆域沿革、风俗变迁、祠宇兴废、宦官政绩、儒林词章,已具规模。
这在新塍志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先锋。郑凤锵有乃祖之风,从小聪明好学,32岁中举人,42岁时值清廷大挑,授衢州开化县教谕。其教育倡导履行“先识器而后文艺”,为人清傲自立,不随流俗,世人皆肃然敬之。
郑凤锵久居新塍,少小时即留意于掌故之学,关心乡里历史人物、典章沿革。为使后来者考查不致湮没无稽,他便仿府志,分门别类,编纂成书。期间,凡乡镇胜迹、残碑或有关风俗教化,不辞辛苦,亲历郊野,手采笔录。
郑凤锵之后,到光绪年间,郑氏后辈有郑折三的《光绪新塍志》稿。这当中自然少不了郑氏家学之风的代代相传。正是在他们这些编志稿的基础上,才有后来民国五年朱仿枚辑成《新塍镇志》26卷,今天我们读到的1995年新编的《新塍镇志》,自然是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成书的。
单从记录历史的角度,郑氏在新塍的历史上很值得大大书上一笔。

诗书传家,为新塍“郑官房”奠定了扎实的人文基础。新塍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更多的是郑家出过许多读书人。
那天我们问起“郑官房”,七十多岁的钱奶奶还绘声绘色地讲起,老底子的时候,“郑官房”是新塍镇上的大户人家,他家大门上,常年挂着一把类似于能煽灭火焰山的大芭蕉扇呢,这是读书的大户人家才有挂的呀。事实也是如此,自郑敬安开始在新塍定居之后,郑家出了许多读书人,或为官,或从文,或从事教育事业,都有好名声,不辱“清贻堂”之门风。郑敬安自己不用说,其孙郑凤锵、郑宝锴(曾任闽南靖县刑法典史),还有后辈郑折三(《光绪新塍志》编者、新塍名宿)、郑兰华(1895-1971,著名化学科学家、教育家)等,讴歌新塍风情的诗作《新溪棹歌》百二十首和《新溪杂事诗》、《新溪棹歌》(稿本),作者郑镰、郑纶章、郑之章,都出自“郑官房”清贻堂。

最有意思的是,“郑官房”多巾帼女杰,可见郑氏家风之开明。
郑敬安之女郑以和,为当时知名女诗人,少时便工于吟咏,常与诸兄作诗唱和,适嘉兴府郡主簿沈潭生后,夫妻俩玉台联咏,乡人艳称之。郑以和性情豪爽,观察使朱九山称其为“天仙化人。”
郑敬安之曾孙女郑静兰,也本邑才媛,幼年承家教庭训工诗歌。适杭州范鸿书为妻,夫亡后归故里,以《焦桐集》名噪嘉湖,绍兴秋瑾、石门徐自华都曾奉诗求见,执弟子礼。后来还在乡里办起“新新”女塾,以振兴女学为己任,乡人皆尊其为范先生。 ……合上了书,翻过了历史。何时重见“清贻堂”?幸好这幢旧屋子里还有个“贝贝托儿所”,可是老师有没有给孩子们讲讲关于“郑官房”清贻堂呢?
--END
文/唐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