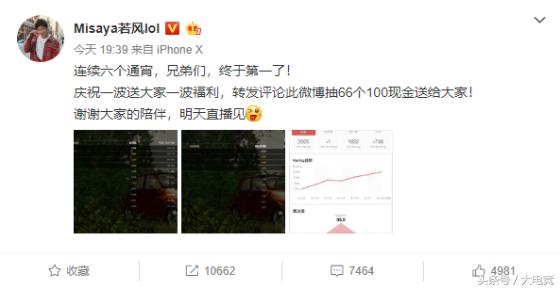乳腺癌已成为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2020年中国女性新发乳腺癌病例约42万,发病高峰集中在45-55岁由于乳腺癌的特殊性,患者面临的往往不止疾病带来的疼痛,还有心理恐惧、社会歧视带来的深层次隐忧,以及如何回归社会的期待,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80后乳腺癌患者分享抗癌经历?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80后乳腺癌患者分享抗癌经历
乳腺癌已成为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2020年中国女性新发乳腺癌病例约42万,发病高峰集中在45-55岁。由于乳腺癌的特殊性,患者面临的往往不止疾病带来的疼痛,还有心理恐惧、社会歧视带来的深层次隐忧,以及如何回归社会的期待。
在近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患者组织经验交流会(CEEPO)上,如何“以患者为中心”,关注患者生活质量,构筑中国医疗健康生态圈成为与会者热议的话题。
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分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副理事长殷咏梅教授指出,在患者为中心的时代,患者的认知和需求在不断地提升,医疗机构依赖原有固定的服务及诊疗模式比较难以满足患者与日俱增的健康管理需求。“以患者为中心”一定是要建立在对患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实现患者的真正参与,不断加强医患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做好医疗服务。
随着乳腺癌诊疗方案不断地升阶更迭,为乳腺癌患者“身心”治愈带来更强信心,让更多女性患者以高质量的生命状态回归社会。在大会期间,笔者走进三位乳腺癌患者,倾听她们的抗癌故事,以及对“治愈”的终极渴望。
“身”的治愈:自信回归社会
如果没有遇到癌症,39岁的史安利正意气风发地走在日内瓦湖畔,前往世界卫生组织一展抱负。
如今的她,大概是中国最知名的抗癌斗士之一:30余年间,先后确诊左侧乳腺癌、结直肠癌、右侧乳腺癌,走上了不止不休的抗癌之路。
命运难以预料的“跌宕起伏”,让史安利见证了肿瘤治疗的飞跃发展,也对每位患者的不甘与挣扎都感同身受。“那时候没有保乳的概念,大家关心的是有没有切干净、会不会复发。”手术后很多年,手臂水肿一直伴随着史安利。因为长时间的化疗,血管变硬打不进针更是家常便饭。“我特乖,每次一见着护士马上就说对不起我的血管不好,你打坏了没事的,放心。”史安利笑着回忆,这些经历打磨着她的身体和意志。
其实,即便有医学背景,最初确诊癌症时,史安利也曾经历人生低谷:“我那时候看电视,只要谈肿瘤马上就转台,不看,不和任何人说我自己的病,不想人家知道。”真正的转变,来自看见了真正的患者。“患者和患者之间,谈得特别亲热,精神上抱团取暖的作用,甚至大于治疗,我自己就有这个感受。”
正是这样的契机,让史安利的事业轨道,也转向患者组织。在她和伙伴们的努力下,中国抗癌协会康复分会规模扩大了一倍多,截至2022年,全国已经有123家肿瘤患者康复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患者有40多万,参加活动的患者有上百万。”
已经76岁的她,常常忘了自己是个“癌症患者”,活跃在抗癌的各项活动现场,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癌症不可怕。
“我们不能光承认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实际上我们对社会是有作用的。”史安利指出,中国患者组织经验交流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舞台,让患者组织对其自身的作用和价值有了理论上的提高。“未来患者组织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包括对新药的研发、药品的评估、医保的决策等等,患者组织通过调查拿出实际的数据,将有助于决策的进一步科学化。”
“心”的治愈:勇敢撕掉患者标签
从初闻癌症时“怕得要死”,到如今成为患者群里的知心大姐,王喆抗癌八年,最期待的,是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利落的短发,精干的黑框眼镜,初见王喆,很难联想到乳腺癌三个字。2015年1月16日,知名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去世,新闻报道铺天盖地,48岁的王喆想到自己胸部的结节,预约了乳腺体检。“医生一摸就说马上要做手术。”王喆被确诊为HER2阳性乳腺癌,已经出现了淋巴结转移。
彼时的王喆刚从国外回到温州,在当地开了一家私人定制的高端奢侈品店。“之前在国外因为一次严重车祸,我先后经历了6次大的手术,一直都是乐观面对。可是听到癌症的瞬间,我真是万念俱灰,觉得自己快死了,那种感觉特别强烈。”王喆告诉笔者,自己当时对癌症一无所知,感觉很迷茫。这也成为后来她创办患者组织的初心。
接受治疗半年后,王喆在病房里创办了温州市幸福丝带姊妹之家志愿者协会。刚开始只是一个微信病友群,慢慢地,微信群发展壮大,从2016年创立至今已经有1000多患者加入,其中包括200多名康复义工。在政府支持下,“幸福丝带”有了独立办公室,王喆和30多个骨干义务为患者们提供服务。
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缺乳、缺钱、缺爱是最常见的难题。癌症治疗经济负担不轻,乳房缺失则给患者带来情感创伤。王喆表示:“很多乳腺癌患者特别自卑,不敢面对大众,不敢去澡堂、去游泳,从患者转向志愿者走向社会,角色转换其实特别吃力。”
来自社会的不理解,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如雪上加霜。“他们就是觉得癌症病人不正常,跟他们不一样。”如今的王喆停掉了自己的生意,全身心投入“会长”这一职务。“还有很多癌症患者不敢面对社会,觉得丢脸,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是个病人。”王喆表示,中国乳腺癌的高发年龄在45-55岁,正好是子女即将结婚成家的时期,有不少病人担心会影响家人。“我们协会希望帮助更多患者从疾病阴影中走出来。”
“新”的治愈:要“活有所用”
乳腺癌带给身体和心灵的伤痛,可以被时间冲淡,不过,漫长的治疗过程,又常常会像闹钟一样提醒你是名“患者”。
2017年,53岁的李莉(化名)在单位钼靶体检时,发现了早期乳腺癌,开始了新辅助化疗。她至今记得,由于病床紧张,大部分的化疗都在门诊日间病房完成,有时候就只能坐在一张凳子上,一坐至少三个小时。“那时候输的叫‘红白药水’,好多患者一见到药水就开始作呕,护士知道后,每次化疗都把药瓶外面包裹好再拿进来。”
长期的化疗,癌症病人手臂或锁骨处就得装一个PICC管(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方便输注治疗。“生活非常不方便,洗澡和洗头要分开,每个星期还要去冲洗一次管避免堵塞。”李莉告诉笔者,对于癌症病人来说,化疗以后免疫力低下,去一次医院增加一次感染的风险,长时间输液一待就是小半天,更是增加了这种风险。
类似的经历王喆也经历过。化疗结束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王喆的手臂上都挂着PICC管以方便靶向药物注射用曲妥珠单抗的静脉输注,让王喆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癌症病人。为了隐藏起这个“标签”,王喆曾经特别买了个蕾丝手环将置留管“藏”起来。
保乳、减少化疗、精准用药……从单纯“求生”,到如今追求生活质量,乳腺癌创新药物的上市也在支撑患者走向更好的“治愈”。
“乳腺癌又是幸运的,越来越多的创新药物上市可供选择。例如靶向药物注射用曲妥珠单抗推出皮下制剂,对于病人来说,治疗时间从近2小时缩短到5分钟,不用再因为输液时间长‘受罪’、频繁请假耽误工作,心理感觉也会好很多。”史安利表示,治疗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可以让乳腺癌真正实现慢病化管理,回归生活、回归社会成为可能。
“皮下制剂也让未来居家治疗成为可能,每次治疗几乎可以节省近半天的时间。”对于王喆来说,这些时间有太多事情可以去做——学习插画,去喝下午茶,也可以跟朋友聚一下,为患者提供咨询,出谋划策……从确诊乳腺癌至今已经8年多,王喆的生活完全转了方向。“我觉得自己活有所用,不像患者一样坐在那里哀嚎,走上社会可以帮助别人,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作者】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 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