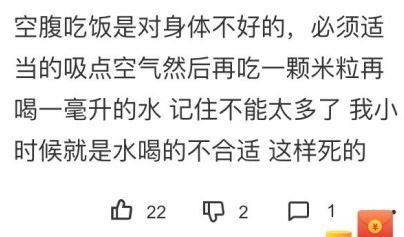作者题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雨历程,有我笔下共产党人的奋斗足迹。他们及后人历经磨难,受尽敌人的折磨和同志的误解,但,不改初心,担当大义,默默秉承着“红岩”精神。小说章章“设悬”,处处“埋雷”,请各位莫当走马观花的过客。究竟写的是什么?碎片拼接才知结果。
第二十章 谢先自杀,于伟忠继续追查
半夜时分,艾灵拉住陈得索在草屋里转。寻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割草的镰刀,这是她家唯一的家产和劳动工具。母子俩登上漫滩湖大坝,准备顺水闸出水口处,沿洪河向东逃......
艾灵母子登上二郎山漫滩湖大坝。突然,陈得索转身发疯似的往湖坡下跑。
艾灵惊恐而压低声,“得索,你干啥?”陈得索也不回答,一直跑到湖边。他脱下破衣服,扎进了碧波缓流的漫滩湖,不一会儿从水手里托出一个瓷罈子,其内还轰隆轰隆地响......陈得索迅速上岸,穿好衣服,从瓷罈子里掏出大小不一的几条鲶鱼。
艾灵惊奇地,“这是谁家的罈子?”
陈得索穿上破衣服,“是咱家的,也是公家的。”
艾灵不解,“咋这样说?”
陈得索让母亲抚摸罈子,“这还是咱的青花瓷罈子!”
艾灵不相信,“咱的,我给陈青岩炼铁做炉芯材料了。”
陈得索说,“您忘了?奶奶死时说,陈青岩没有把咱的青花瓷罈子砸碎。她曾看见陈魁掂着玩。前天,我看见陈魁抱一个罈子,学我用绳子套住罈子脖子往湖里扔,结果绳套脱了,罈子落到湖里。陈魁不会水,丢这儿不要了。我忽然想起奶奶的话,去下水打捞,真是咱的青花瓷罈子!”
艾灵喜出望外,“老天有眼,物归原主。这是咱的传家宝,要好好珍藏。”
陈得索把青花瓷罈子里的淤泥清理出去,灌进一些清水把鲶鱼重新装进罈子。艾灵用一个粗布破单子把青花瓷罈子包起来,让陈得索挎在肩上。母子快速离开漫滩湖......

陈得索家的青花瓷罈子
豫西县文教局长于伟忠,听说孔庙镇公社因大炼钢铁让学生停课,还听说孔庙镇吃食堂饿死人。他感到震惊和不安,共产党流血牺牲打天下,为的是让人民过好生活呀。于是他主动向县委宋名请求,前来孔庙镇实地调查。宋名早已经知道孔庙镇的问题,并清楚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他内心其实不愿于伟忠去孔庙镇调查,但又不敢也说不出拒绝的理由,只得表面同意,暗地指示谢先做好迎接准备。谢先心虚,听于伟忠来孔庙镇调查,感到惴惴不安,只得硬着头皮亲自到县城迎接和陪同这位他又敬、又畏、又疑的于老师。
吉普车沿漫滩湖公路向孔庙镇方向行驶,谢先穿着军装陪坐于伟中右边,试探问,“于老师来孔庙公社要调查什么工作?”
于伟中表情严肃,“督查学校开课了没有,再看看你的共产主义大食堂是不是天堂。”
谢先面色阴沉,说活再没有了过去的底气,“冬天,修大坝没有结束,就让学校师生复课了。”
于伟中脸不放,“听说艾灵老师下放回陈家庄体验共产主义生活去了?”
谢先辩解,“她儿子从学校水道眼子里偷学校一个馍,她不批评还袒护。”
于伟中质问,“伙房的水道眼子小孩能钻进去吗?”
“应该能钻进去。”
“你们让陈得索钻了吗?”
“没有,而让‘老赵’钻了。”
“怎么样?”
“结果 连‘老赵’的头都进不去。”
“那凭什么说陈得索偷馍呢?”
“他的同学陈魁、吴九清说陈得索会偷瓜。”
于伟中听罢,抑制不住怒火,“谢先呀谢先,打鬼子,你设伏击;追老蒋,你有胆量;到朝鲜,你不怕死。为什么你做基层工作这么官僚?”
谢先低头不语。于伟中神情凝重,目视前方。对司机说,“到陈家庄看看!”
车向陈家庄前进。于伟中扫视车外,黄土岗麦苗稀疏,杂草疯长......不时闪出有人躺在路边,不知是死是活......柏子山黑石凸露,古柏树横七竖八,枝枯根残,炼铁炉子东倒西歪,狼藉不堪......
车到陈家庄食堂,于伟中下车。炊事员陈石堆站在食堂门口转动着眼珠张望......于伟中看到食堂流着污水却没有开伙,急切地问,“怎么不开伙?”
陈石堆塌蒙着眼,不敢看大家,少气无力地说,“没有东西做。”
于伟中扫视四周,“村里社员呢?”

吃食堂饿死了人
陈石堆看看谢先,说实情,“死的死,逃的逃。”谢先不敢抬头,两鬓冒出汗珠。
于伟中转脸问谢先,“陈国清的家人呢?”谢先抹把汗,回答,“国清母亲死了。艾灵和儿子在家。”
“走,我们看看去!”谢先无奈,只得陪于伟中沿山路到艾灵家。陈得索和艾灵早无踪影。仅剩一所破草房孤零零地听溪流倾诉。......于伟中环顾左邻右舍,墙倒屋露,十室九空......
于伟中怒吼道,“你们浮夸蛮干,这是犯罪!”接着他哽咽起来,“谢先,你带兵打仗一辈子了。打老日,你死了多少人?打老蒋,你死了多少人?打老美,你死了多少人?现在,敌人没动一刀一枪,跟着你的老百姓就大批倒下。你、你怎么向组织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
谢先低头,泪水夺眶而出,“我也是一腔热血干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啊!”
于伟中也哭起来,“为共产主义奋斗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脱离实际,浮夸蛮干,瞎折腾!”
第二天于伟中走进宋名办公室,准备汇报孔庙镇存在的严重问题。宋名神情沮丧,没有等于伟中开口,便站起来发起火,“你在谢先那里都说了什么?”
于伟中坦坦荡荡说,“我狠狠地批评了他!大炼钢铁,修水库,他擅自让学校停课;孔庙小学因为丢两个馍,他随意开除教师艾灵;过共产主义吃食堂,他又让饿死很多公社社员。”
宋名摇头显得非常懊悔,“49年解放重庆,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于伟中瞪大眼睛,“为什么?”
宋名摆摆手,“老于呀,不懂政治,只能做学问!”
于伟中诧异,“我批评谢先错了?”
宋名把一页纸递给于伟中,“谢先想不开,昨天晚上,在孔庙小学后花园投井自尽了。这是他的遗书,你看看!”
于伟中手哆哆嗦嗦接谢先遗书看:“宋书记、于老师,我与妻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搞建设殚精竭虑。但孔庙公社饿死人事件,我罪责难逃。于老师批评得对,我对不起组织,更无脸面对孔庙父老乡亲。战乱中,我有子难保;解放后我赴朝抗美,有子又丢。我走了,请寻我根。拜托关照。”
于伟中看罢两眼落泪,“这个谢先,怎么走这条路?”
宋名也沉痛,“他丢子丧妻,加之你批评他工作失误,想不开呀。”
于伟中显得痛苦的样子,“早知这样,我不该批评他。”
“孔庙镇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呀。”宋名慢慢踱着步,“谢先是我的亲密战友,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我们要记住他的嘱托,想办法寻找他失踪的儿子。”
于伟中点头,“好。杨秀玉死时说,她的两个儿子头顶上都有两个旋,我们可顺着这个线索找。”
宋名站起来,招呼于伟忠,“走,我们先到孔庙小学,看看谢先殉职的地方。”

孔庙古井
谢先被埋在孔庙小学后花园古井旁。老师‘老赵’、侯气、村民赵末吃力地挥锹填土。宋名、于伟中、陈青岩伫立默哀,孔庙小学师生和孔庙镇附近社员围观叹息,个个精神萎靡,癀病刮瘦......
龙山跪在一旁悲痛欲绝,龙根跪在一旁搀扶。“表弟呀表弟,你不该走这条路呀。饿死人,不光是你的责任呀!”
宋名皱眉,低声问陈青岩,“这人是谁?”
陈青岩低声说,“叫龙山,是谢先妻子杨秀玉的姨表。”
宋名声音轻蔑,“就是把谢先的儿子交给日本人杀害的那个龙山吗?”陈青岩点头。宋名显得不屑一顾,“猫哭耗子——。让他滚开!”
于伟中上前扶龙山,“别哭了龙山,宋书记让你回去哩。”
龙山抬眼看看宋名,小眼睛放光,“他是县委书记?”
于伟中点头,“是的。”龙山突然转身拉着龙根跪在宋名面前哭诉,“宋书记,散食堂吧,不然,死人更多!”
宋名环顾左右,“散不散,上头说了算。你不当家,我也不当家!”
龙山抱头痛哭,“因为吃食堂,俺饿得浮肿,儿子给俺……”
龙根打断龙山话,“爹,这是儿应尽的孝!”
于伟中、陈青岩、‘老赵’听龙山父子话中有话,都愣着了。炊事员武大林却哆嗦起来,他不满意龙山说,“龙根,你爹疯了吧?”
龙根跪着低头喃喃道,“武师傅,我爹说的是实话。我爹饿得慌,上一周我真给俺送一个馍。”
武大林吃惊,“这是谁的馍?”
龙根不敢抬头,“我的。”
‘老赵’插话,“是不是偷的?”
龙根抬起头,“不是。这个馍,是我舍不得吃,节省的。”
陈青岩柔中带威,有强加之意,“龙根,你带回家的馍,应该是两个吧?”
龙根头冒虚汗,侧目视陈青岩,“就一个!”
于伟中沉痛道,“学校因为丢了两个杂草馍,艾灵失教,其子失学。一件小事,酿成惨案和悬案。”
宋名心生恻隐,“恢复艾灵的工作,让她母子回校!”
陈青岩面红耳赤,看看于伟中。于伟中禁不住落泪,“艾灵婆母饿死后,她带儿子逃荒,失踪了!”
龙山面色煞白,“都作孽呀。”龙根抱着龙山呜呜地大哭起来。宋名上前,低头打量龙根。突然他发现龙根乱蓬蓬的头上长两个旋。宋名心中嘀咕,“为什么这龙根孩子头上也有两个旋?”他不动声色,把龙根拉起,“你是个孝顺和诚实的孩子,跟我到县委做饭吧。”大家都惊愕。
人都散去。于伟中还在孔庙小学后中心路徘徊。路东是陈国清的小坆头,孤零零的,上面长满荒草;路西是谢先的新坟,以古井为伴。
于伟中意识流动,“孔庙小学,风景独特,山水相连,曾是孔子周游落脚讲学圣地。千年名校,多少学子走出去,为国献身,尽显风采。我于伟中也曾在这里传播真理,让学生抗日图强,兴国安邦。可是世道沧桑,他们前程有别。陈国清和谢先你们既是兄弟,又是同学,都是我的学生,走的都是革命道路,可是你们同途有岐,反目为仇,其结果又都魂归母校。作为老师我如父辈,你们寻短见,让我困惑、无奈、悲哀,甚至恨你们。你们走了,留下遗憾,更让我这个老师担忧你们的亲人。国清呀,你上吊干什么,你为什么忍心抛弃父母和妻儿?谢先呀,你投井干什么?饿死人是你一人所为吗?难道你还真干了其他见不得人的事?”于伟中眼含泪水,他环顾四周,看没有人了,匆匆走进‘老赵’住室。
‘老赵’刚埋了谢先,身上还一身土。他傻傻坐着,看见于伟中进来,表情漠然。
于伟忠进屋安抚‘老赵’,“谢先走了,您也不必伤心。”
‘老赵’神情黯然,给于伟忠让座,“于局长,请坐。”
于伟中开始问一些让‘老赵’不着边的问题,“谢先是你捞出来的吗?”
老赵漫不经心道,“以我为主,还有陈校长、武大林帮忙。”
“谢先从井里捞出来,穿什么衣服?”
“只穿一个裤头。”
“他右膝盖前有伤疤吗?”
“右膝盖伤疤?”他皱眉回忆,“没有。给他穿衣服时,只发现他右膝盖后腿窝里有伤疤。武大林、陈青岩在场也知道。”
于伟中沉思一会,突然按着老赵,喝道,“把你的右膝盖搂起来!”
‘老赵’困惑、不满,“于局长,你是唱的哪出戏?你在侮辱我,我不搂起!”
于伟中与其缓和,“好、好。我问你,你右膝盖负过伤吗?”
老赵充满敌意,“负伤不负伤与你无关!”
于伟中低声道,“我怀疑你在捣鬼!”
‘老赵’惊愕,“我捣什么鬼?”
于伟中怒视‘老赵’:“你对艾灵图有不轨。”
‘老赵’抓起自己坐的凳子摔下,“你出去!”
于伟中没有畏惧,反而逼近‘老赵’,威严道,“还有,谢先的儿子呢?”
老赵吓得直哆嗦,“于老师,您不能再冤枉人了。您冤枉陈国清,陈国清丢了命,您再冤枉我,我也会没有命的!”
于伟中往外瞧瞧,进一步压低声,“你的身份瞒得住别人,瞒不住我和艾灵。说,谢先的儿子是不是你偷走后又对艾灵侮辱?”
老赵不吃这于伟忠一套,“于局长,您别逼我了,你调查呀!”
于伟忠被‘老赵’当头棒喝,皱眉冷静沉思,“是的,我该调查。作为当事人,诸多悬案我弄不清楚,岂能对得起死去的陈国清、谢先、杨秀玉和活着艾灵母子?”责任、使命、亲情让于伟忠下定决心,继续调查。第二天他只身到郑州大学附中找到杨秀峰。杨秀峰青少年时期,在孔庙小学就读时,与谢先、陈国清、陈青岩、杨秀玉等是同班同学,都是于伟中的学生。1938杨秀峰被校选为精英少年随校南迁辗转武汉、重庆,后在重庆就读初高中,留校。杨秀峰是杨秀玉之弟,但起初兄妹俩各奔东西,况且都不知道杨钦典就是他们的父亲。现在杨秀峰夫妇在郑州大学附中教书,和于伟忠爱人是同一个学校。于伟忠知道杨秀峰家住教师家属院二层小楼,只是多种原因两家联系不多。于伟忠敲杨秀峰家门。杨秀峰开门,一看是于伟忠,非常惊讶,上下打量于,“啊?于老师!”他慌忙请进,让座,“咱们近10年就没有见面了。”
于伟中落座,“是呀,重庆解放前夕,你提前回郑州了,后来我随军又回豫西。”
杨秀峰说,“其实,您家师母和俺在一所学校,只是不在一个小区住,你的女儿秋叶也和俺的孩子一班。”
于伟中不动声色问,“哦。你有几个孩子?”
杨秀峰迟疑一下,“两个。”
于伟中笑笑,“学生比老师跃进。都多大了?”
杨秀峰回答,“大儿子叫抗利,女儿叫抗美,都十来岁了。”
于伟中歉意,“我也回来几次,没有多停。也知道你在这儿住,是我官僚,孩子这么大了还不知。”
杨秀峰摆手,“您当官忙,我是个教书匠,也不愿意和人接触。”他乜斜于伟中一眼 “还没有见师母吧?她身体好像不太好。”
于伟中伤感地说,“是的,生秋叶时,我不在她身边,又没有人照护,得了类风湿。”
“哦,这病缠人。”杨秀峰转移话题,试探问,“您怎么这时间回来?”
于伟中没正面回答,问,“你还记得重庆白公馆军警大逮捕我们一中老师的情景吧?”
杨秀峰皱眉回忆,“记得。文艺陶校长被撤职、周梅修老师和你、陈国清都被捕了,一中解散了。”
于伟中扯到正题,“你知道吧?抓我们的那个高个子军警班长就是你父亲杨钦典!”
杨秀峰警惕起来,似乎不愿承认,至少不愿提起杨钦典是自己父亲,“于老师,您今天来我家怎么说这事?他是我父亲吗?他不是死了吗?”
于伟中一愣怔,尔后又沉痛道,“是的,他死了。他的女儿、女婿也死了!”
杨秀峰哭起来,“我姐、姐夫哥死,我都知道,只是怕母亲知道,我没有回去。”
于伟中追问,“你母亲在哪里?”
杨秀峰说,“我回郑州教书后把母亲接到我这儿,一直跟着我,今天星期天和张艳到金水河坡挖野菜去了。”
于伟中说,“哦。你这样瞒着母亲也不是长法呀。”
杨秀峰显得淡定,“老实说,我姐、哥活着我也不愿沾他们的光,死了我也不愿哭他一阵子。”
于伟中紧盯杨秀峰,“可是,你外甥,你要管呀。”
杨秀峰反问于伟中,“我外甥叫什么,在哪里?”
于伟中盯着杨秀峰,“他叫谢弘,你姐姐死时托付艾灵了,结果没多久被人偷走了,从此没信儿,不知死活。谢先投井自尽,遗嘱宋书记和我帮他寻根。”
杨秀峰皱眉,低头沉默片刻,尔后抬头,“我儿女双全。他有儿无儿跟我无关系。”
于伟中将信将疑而又显得无奈,心想,“难道杨秀峰也不知道谢先儿子的下落?”
于伟中辞别杨秀峰,回家路过金水河岸。河岸上,柳树、榆树歪歪扭扭地长着。杨抗利在榆树上折着挂满榆钱的枝子,扔下。于秋叶、杨抗美在树下捋着榆钱大把大把地往嘴里捂着吃......
杨抗利是杨秀峰之子,在郑州大学附小、附中就读,与于伟忠的女儿于秋叶是同学。其妹叫杨抗美。三人的年龄都在10岁左右。于秋叶看到父亲于伟中走过来,欣喜、羞涩又感到陌生,瞪大眼睛捂在嘴里的榆钱忘记了咀嚼……于伟中弯腰拉着于秋叶,“叶儿,爸回来了,走,回家!”于秋叶点点头,嚼着榆钱,泪珠嘟噜嘟噜顺脸淌。
杨抗利在榆树上俯视,问,“您是谁?”
于秋叶把榆钱咽下,抢答,“是俺爸!”
杨抗美也在树下仰头喊,“哥下来吧,咱也回家!”杨抗利扔下榆钱枝子,像猴子一样跳下。于伟中忽然想起了什么,招呼杨抗利),“来,抗利,你们三个比比个头,让我看看谁高?”杨抗利上下打量于伟中,并没有上前,做个鬼脸,拾起榆钱枝子,拉着杨抗美跑了……
中午。杨秀峰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吃饭。杨抗利、杨抗美狼吞虎咽地吃黑窝窝头。而杨秀峰面色阴沉,愣住不吃,也不说话。
张艳32岁,郑州大学附中教师,杨秀峰之妻,她端汤嚷道,“你们这孩子,只顾吃也不叫您爸吃。”杨抗利、杨抗美停止嚼咽,怯怯地望着杨秀峰。秀峰母56岁,杨秀峰母亲,杨钦典之妻,却护着孙子孙女,“别吓着俩孩子。秀峰不吃是不饿。”
杨秀峰面无表情,他拿一个馍,盯着杨抗利,问,“抗利,最近学校有人问过你是哪里人吗?”
杨抗利摇头,怯生回答,“没有。”
杨秀峰虎着脸,“都记着,今后不管谁问,我们和谢先是什么关系?就说不认识谢先!”
秀峰母把饭碗放下,生气又伤心,道,“过去不认你爹,现在连你姐夫谢先你也不让认了,过你自己呀?”
杨秀峰不理睬母亲,“谢先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记住,我的儿子在家在学校都叫杨抗利。抗美,你也记住!”
妻子张艳小声责怪,“你怎么这样?不怕咱娘伤心?”
杨秀峰坚持己见,自有道理,“咱求的是平安和宁静。你不想安心教书,让两个孩子快乐学习?”
张艳白他一眼,吃饭,嘟囔道,“神经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