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柏琳
自从1970年代“白澳政策”被扔进历史垃圾堆后,有一大批澳洲原住民作家在世界文坛上迅速成长,他们的声音也愈发清晰有力,尤以亚力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金姆·斯科特(Kim Scott)、梅丽莎·卢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等人取得了耀眼成就。这表明,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在和殖民统治、种族歧视的斗争中,既传承了本民族的古老文化传统,又在现代社会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声位置。
这些原住民作家中,梅丽莎是特立独行的一位女作家,也堪称澳洲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1967年出生在布里斯班远郊,父亲是来自俄国难民的儿子,母亲是混血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后代,属于邦家仑(Bundjalung)民族。梅丽莎并非“纯粹”的原住民,她长着白人的皮肤,却坚定选择了母亲家族的身份认同。白人外表下,她的胸腔里跳动着一颗强力的“土著之心”。
14岁时得知自己原住民身份她有强烈的个性,生活经历丰富多彩。从小练习空手道,拥有空手道黑带,五次获得昆士兰州空手道大赛冠军,三次获得全国空手道荣誉称号。她正义感强烈,是一位勇敢的女权主义者,为原住民女性的权益发声,积极参与此类的社会公共活动。她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学院派写作训练,所有关于写作的事都靠自学。
因为意识到澳大利亚主流文学中对于原住民生活的描述很少,由原住民作家来写的就更罕见,梅丽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了小说创作。她多年来坚持书写普通原住民的不普通生活,发表了7部获奖小说和多篇散文。

她的第一部小说《蒸猪》(Steam pigs)就入围了新南威尔士州长文学奖和地区英联邦作家奖,后来的小说《穆伦宾比》(Mullumbimby)荣获昆士兰文学奖。新作《多嘴多舌》(Too Much Lip) 更是获得了2019 年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她因此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得此殊誉的原住民作家。
我和梅丽莎做访谈,最鲜明的感受就是她对于原住民身份意识和原住民文化传统的极度认同。在她看来,是不是原住民,并非只是由血统和肤色来决定,而是必须建立在对原住民文化充分融入的程度、对祖先家族记忆的深入了解,以及是否认可这种文化的基础上的。
梅丽莎家里有7个孩子,她是老幺妹妹,上头有六个哥哥。在这样的原住民家庭中,且不说是否成为一个作家,顺利成长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年,母亲被迫把她的大哥藏起来,担心会被政府强行带走,放到白人家庭寄养来达到同化的目的。因为家境困难,梅丽莎还是个孩子时,大哥就离家工作了,而她15岁也出门打工,接济家庭。19岁的她上了大学,主修公共政策和经济。在她上大学的年代,原住民上大学是十分困难的,梅丽莎本想着毕业后能做个小生意,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她从来没想过写作。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完全得益于她的好奇心和自学的毅力。
有一件大事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即得知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她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因为只从肤色上看不出来她是个原住民。直到14岁时,母亲才和她坦白家族历史。得知此事后,梅丽莎除了震惊,并无其他感受。原来,她从小就以为,每个人出生时都可能有不同的肤色,有的是白人,有的是黑人,有的是棕色皮肤的人,就像有的人是卷发而有的人是直发。1970年代后,澳洲政府停止了同化原住民的政策,当时的人们也就很少再谈论种族话题。当母亲告诉她是原住民时,梅丽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她在学校里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蓝眼睛金色头发的同学不一样。
知道自己的身份后,梅丽莎感觉开始自动接收到周围有一个原住民文化磁场的存在,吸引着她不断靠拢。从此,她有意识地和其他原住民学生共同学习和生活,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原住民文化传统,成为许多原住民家庭的一员,并把这种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
原住民社群内部互相伤害和丑陋的一面父亲来自遥远的俄罗斯,梅丽莎从未在那片土地生活过,她无法对父亲的家族产生强烈认同。又因为叛逆不羁的性格,她天生就对澳洲主流白人文化圈不以为然。她坦言,如果愿意,完全可以一辈子假装自己是个白人,不必忍受因为是澳洲土著的后代而在主流社会经历的精神折磨。但那么做是不诚实的,梅丽莎不能忍受自己不诚实。
最新完成的小说《多嘴多舌》,就是一部堪称诚实的作品。黑色幽默与犀利并存,一幅澳洲原住民在当代社会生活的画卷,以新鲜热辣的方式呈现在好奇的读者面前。澳洲的原住民绝非是整天躺在大树下睡懒觉的原始人,也不是成日沉溺在毒品和暴力中的野蛮人。面对传统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他们同样面临艰难挑战。
这个故事,讲述澳洲新南威尔士州郊外的下层阶级原住民的生活。同时背负着沉重的家族记忆和刺痛的当代经验的原住民,每一个人都如舔舐伤口的野兽一般,默默承受着伤痛,并且和当下的澳洲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彼此攻击,互相伤害,各自承担自己的伤心往事,却都有共同的使命要去面对:如何重新追回原住民祖先的古老土地?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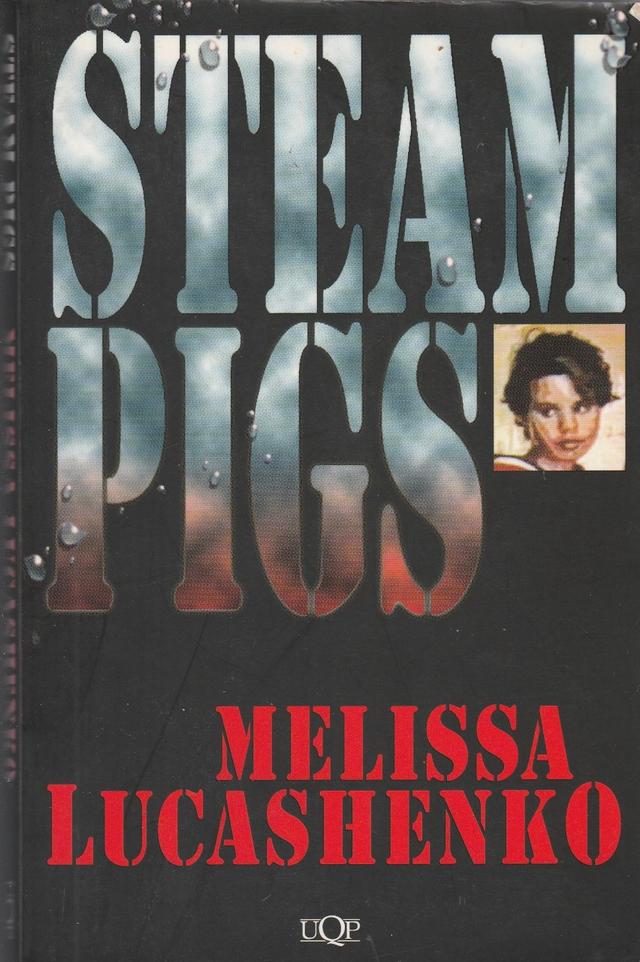
这部小说拥有一种反常的爆发力和诗性。和描写澳洲白人对原住民的伤害这种常规的写法不同,梅丽莎把笔端对准原住民社群内部的互相伤害和丑陋的一面,这种从描写“外部伤害内部”转变为“内部互相伤害”的写法,让人读来震撼,也让这部小说显现出诚实的动人特质。梅丽莎必须小心翼翼地展现这种诚实,现实情况是,来自外部的暴力——警察的暴力、当局的暴力、腐败、对原住民文化的蔑视等等,这是无处不在的。原住民生存环境的恶化,肯定不是全部由内部斗争导致。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被遮蔽的真相需要被揭露,这需要很大勇气。
写这部小说时,她一直都有恐惧感,害怕原住民社群讨厌她。因为她写了内部人群互相之间的伤害和邪恶,担心他们会抵制她。事实上,她未曾遭遇过类似的排斥。在《多嘴多舌》正式出版前的两三个月,一家著名的澳洲原住民媒体在一档系列节目中发布了新书讯息。这个节目的策划者是原住民导演瑞秋·博格斯,也就是已经去世的原住民著名领袖人物查尔斯·博格斯的女儿。她对梅丽莎说,她正在做的这档记录澳洲原住民生活的节目,关注点也在内部的嫌隙和斗争。梅丽莎听后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
但写作《多嘴多舌》的两年里,她确实是担惊受怕的。要知道,有些话说起来总是很容易——坏警察在屠杀原住民,白人教师是种族主义者,澳洲政府觊觎原住民的土地,但是抛弃了他们。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但还有更艰难的真相:你的某个叔叔猥亵了你的某个家庭成员,你的父亲长期对母亲实施家暴,这些真相让人更加难以承受。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梅丽莎更多关注族群里的女人和孩子长期遭受的内部暴力。她认为她有责任把这些写出来,并且相信,随着内部的真相逐渐被公之于众,族群内部的窃窃私语也会逐渐销声匿迹,更多黑暗的秘密会重见天日,这就迫使所有人包括原住民和白人诚实地讨论,勇敢地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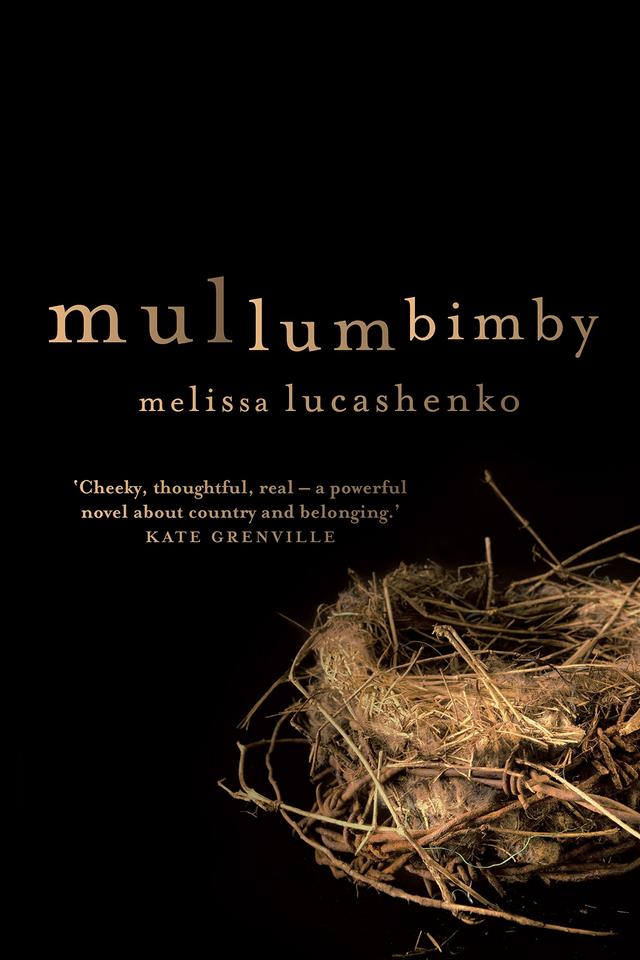
也许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梅丽莎选择从内部直面澳洲原住民的生存困境。但与此同时,《多嘴多舌》依然是一本疗愈之书。书中的索尔特家族里的成员,以及家庭所在的社区,都有互相帮助和互相救赎的方法。在梅丽莎看来,正是因为澳洲主流社会总是通过负面的镜头来描述原住民,让人产生原住民懒散、酗酒、暴力、原始等标签,使得他们无法进行自我疗愈。事实上,澳洲大陆拥有十万年以上的历史,而原住民很早很早就在这里安家了,远早于后来入侵的白人。
她告诉我:“我们早就弄明白了该如何生活、如何创造理想的生活环境。只是因为后来的种族主义者对原住民进行了各方面的‘净化’,原住民的生活理念被最大程度的忽略了。”
古老而梦幻的文化传统梅丽莎的原住民身份最初是被隐瞒的,但她从小就成长在原住民的价值世界中。得知自己的出身后,她更是努力从各方面靠近和学习那个古老而梦幻的文化传统。她坦言自己在多方面受到原住民价值观的影响。比如不把一棵树上的果实都摘光,比如对待老人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帮助,比如提醒自己绝对不能自私。
梅丽莎说,如果你有了很多资产,你必须和社群的其他成员分享。当然,一个人也不需要独自承受苦难,所有人都会和你共同分担,但你不能单枪匹马去做个人主义的事情。她告诉周刊:“在我的原住民社群中,如果一个人有了一座豪宅或一辆豪车(当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他/她如果不和族人共同分享,那么就会被鄙视,会被说成 ‘变得像个白人’。”
她从方方面面都警惕自己“变得像个白人”,而这既需要非常勇敢,也需要有足够的敏感。梅丽莎身上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偏执”,她坚持认为,非原住民作家无论多么优秀,都很难真正写好原住民的生活。
“白人作家所了解的原住民故事只限于200多年来在种族歧视生存环境下的原住民,而这一点甚至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观看的。对于非原住民作家,我的主张是,你尽可以把原住民写入故事里,但只能作为配角,而不能作为主角,因为你不可能做到准确把握。在不能正确地表现人物时,你就会有意无意造成对原住民生活真相的损害。”
有一件事情让她至今耿耿于怀。2000年,梅丽莎在伦敦遇见澳洲白人作家彼得·凯里(Peter Carey),她本人挺喜欢这位可能是当代最著名的澳洲作家。当时,凯里正在面向英国观众做一场主题演讲,其中一部分谈到“澳洲原住民文化作为一种文明怎样怎样”,梅丽莎就混在听众之中,听到凯里这么说,她很惊喜,这可是她第一次听见有人说澳洲原住民文化是一种“文明”!
可是接下去听他说的话,梅丽莎就不乐意了。他说:“可惜这种文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梅丽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质问:“有没有搞错啊?我,作为一个邦家仑族(Bundjalung)的后代,一个澳洲原住民女人,就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你没有看到,并不代表这种文明不存在。”后来,她和凯里在澳洲时也因为这个观点激烈辩论过。梅丽莎坚持自己的看法:澳洲原住民文化的确在现代世界中经历着巨大的改变,但传统的部分从未死去。
《多嘴多舌》聚焦原住民在现代社会的生活,目的之一在于反驳原住民文化行将消亡的论调。梅丽莎承认,有一部分原住民英语不好,甚至根本不会讲英语,但绝大多数原住民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现代科技,比如FaceTime这类新型社交手段。与此同时,原住民依然在践行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己族群的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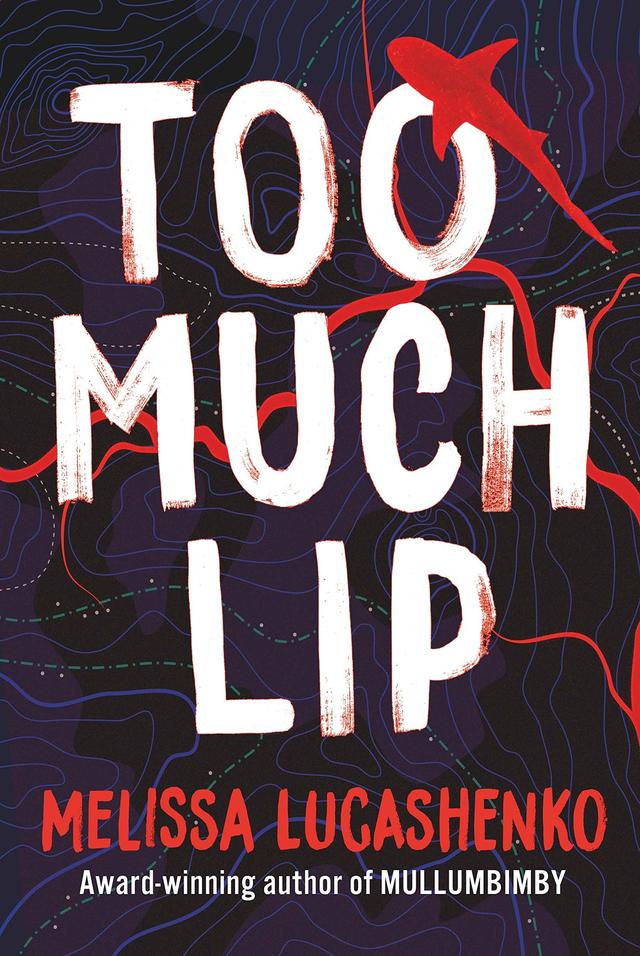
白人进入澳洲大陆前,原住民早就幸福生活在这里了,这是梅丽莎想要努力给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传达的信息。写上一部以原住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穆伦宾比》时,她的焦点在于表明原住民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民族也从未消亡。那部小说之后,她的眼界和“野心”扩展了。在《多嘴多舌》中,作家让她笔下的原住民人物能够拥有五样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第一有美,第二有权利,第三有幽默感,第四有土地,第五有爱。在白人进入这个大陆之前,梅丽莎的祖先的生活,正是因为有这五样东西,生活得富足而美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融合与交互,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到每一个地域的细部,就连澳洲原住民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社群也正在被现代社会切分和打散。梅丽莎生活的布里斯班的原住民社区,也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原住民社区了,那里现在变得多元化,有来自中国、印度、南非的移民,还有澳洲白人,这是一个混合的生态社群。
一个城市复合型社群中都有聚集的原住民住户,祖先分别来自不同的部落,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都“秘密”生活着,互相拥有一条“隐秘通道”,可以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在澳洲的许多中心城市的郊外,也都分布着若干超过50%的人口是原住民的更“纯粹”的社区。梅丽莎如今有两个住处,平时住在城市里那个多元化的社区,感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文化性格。周末来临,她就会回到郊外,回到祖先生活的土地上去找归属感。
对于当下的原住民来说,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精神层面的事情了。而且原住民的认同也总是与土地息息相关,他们的祖辈已经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了数十万年,每一天所走的路其实都踏在祖辈的足迹上。梅丽莎意识到,今后的澳洲社会中,身边的原住民会越来越少,但她毫不气馁:“因为我们依然在唱诵祖先的歌谣,依然在延续祖先所使用的关于树木、河流、动物的语言,所以尽管有时也会面临现代社会的焦虑和困境,但是我们原住民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用的是原住民的眼睛,世间万物都是有神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