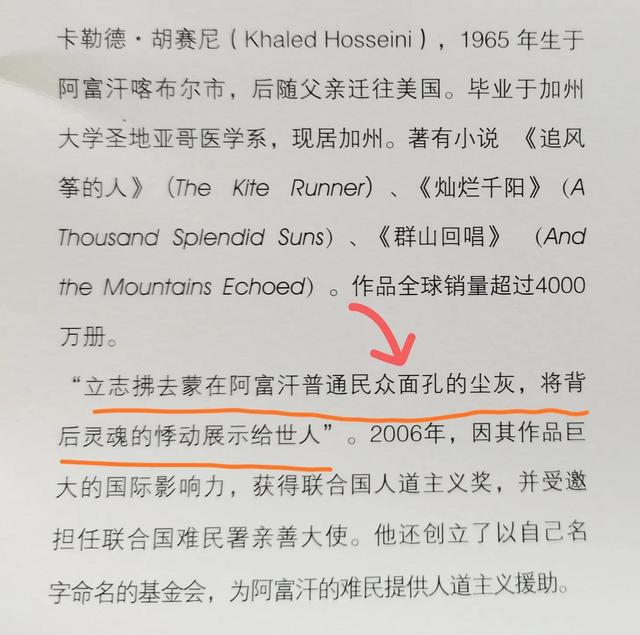《灿烂千阳》的作者胡赛尼出生于1965年,他生于阿富汗,长于阿富汗。11岁那年,父亲任职法国大使馆外交官,全家搬到法国。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胡赛尼的父亲请求政治避难,举家移民美国。胡赛尼作为一个在阿富汗长大的孩子,能够深深理解阿富汗的苦难,更深刻同情着这里的同胞。《灿烂千阳》是这位美籍阿富汗作家继《追风筝的人》后第二部力作,这本书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极强的叙事能力展现了阿富汗广阔的生活画面,读来颇为震撼。

近三十年来,战争、饥饿、专制使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背井离乡,在这些苦难的人们中,有一个群体,她们孤独而顽强地承受着生命的重担。2003年,卡勒德·胡塞尼带着联合国的使命回到祖国,访问难民营。当他走在阿富汗街头,那些身穿布卡、深低着头的女性使他意识到这个群体的悲惨命运。带着对同胞的同情,他拿起笔,为阿富汗的女性谱写了一曲壮美的赞歌——《灿烂千阳》。胡赛尼呼吁人们关注阿富汗,因为“每张落满灰尘的面孔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灵魂。”他在书中写到:“此书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妇女。”
《灿烂千阳》中有两位女主人公,她们二人的成长环境、年龄、性格都截然不同,她们原本像两条平行线,原本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中运行,却因为偶然的命运相交了。她们是玛利亚姆和莱拉。
玛利亚姆是一个哈拉米(私生子)。她的母亲娜娜原本是富商扎里勒家的女仆,因为有了玛利亚姆而被主人扎里勒始乱终弃。扎里勒迫于家中三位妻子的压力,只能将娜娜赶出家门,在遥远的山谷下建造一间简陋的泥屋,让娜娜在这里生下孩子。扎里勒每周派他的孩子送去日用品。娜娜生产的时候,独自一人在泥屋又冷又硬的地上躺了两天。悲剧性的出生方式奠定了玛利亚姆一生的悲剧色彩。玛利亚姆在泥屋长大,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她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四这天,父亲扎里勒会带着时有时无的礼物来看望她。“每到周二,她就开始心不在焉,周四终于来临,她什么都不做,背靠一面墙壁,静静地坐着,眼睛死死钉盯着山溪,等待着。如果扎里勒来迟了,一阵可怕的张皇会点点滴滴涌上她的心头。”缺乏父爱的她对外面的世界好奇而又向往,玛利亚姆十五岁生日这天,扎里勒失约,她不顾娜娜疯狂地反对,坚持要去外面找扎里勒。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她的心兴奋地砰砰跳。尽管她在扎里勒门前发现了他的汽车,扎里勒却迟迟不愿出来见她。可怜的玛利亚姆绝望地在门口等待了一夜以后,冲进了那扇大门,无意间看到了楼上躲在窗帘后面的父亲的眼睛。她终于明白,娜娜说的话都是对的,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存在对于父亲来说,更大程度上是耻辱。她在回家的路上哭个不停,她流下的是愤怒的眼泪,是梦想破灭的眼泪,但更是深深的屈辱的眼泪。回家后,她发现母亲吊死在一棵树上。
年仅十五岁的玛利亚姆没有父亲的关爱,又失去了母亲,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出嫁。扎里勒是一个极其自私与虚伪的上层阶级男性的代表,为了维护自己和家族的颜面,不惜将女儿远嫁比她大三十多岁的鞋匠拉希德,将女儿送到了更为绝望的人生境地。可怜的玛利亚姆从此过上了卑微、低贱、被虐待的日子。

丈夫拉希德有着强烈的男权意识,将玛利亚姆视为奴仆。她不仅要承担所有沉重的家务劳作,还经常受到丈夫的鞭打。拉希德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让她出门时一定要穿上黑色罩袍,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阿富汗女性所穿的黑色罩袍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布卡”,穿上布卡后的女性看不到周边的状况,只能通过网状的屏障看前面的世界。布卡象征着一种社会秩序,即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在玛利亚姆多次失去孩子后,他更是对她拳打脚踢,任意践踏。玛利亚姆默默忍受着丈夫的暴力,承受着由父亲和丈夫所赐的生命中全部的苦难。
玛利亚姆是胡赛尼笔下一个展现阿富汗女性苦难命运的代表。在这本书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生活在苦难中的人。
莱拉是玛利亚姆邻居家的女儿,比玛利亚姆小十四岁。她的父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西方自由思想的教师,因此,莱拉有机会受到学校教育。苏联入侵后,莱拉的两个哥哥参加圣战组织,双双牺牲。莱拉的母亲从此一蹶不振,悲痛欲绝。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后,街上处处是枪林弹雨,每天都有大量无辜的百姓死去。莱拉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塔里克逃到了巴基斯坦,莱拉顾及父母没有随塔里克逃走。莱拉的母亲为了替两个死去的儿子看到战争胜利,坚持留在喀布尔。在每天川流不息的子弹的威胁下,莱拉一家人终于决定离开,然而在收拾行李时被流弹击中。莱拉父母的躯体被炸裂,碎片四处都是。而莱拉却被拉希德救回家里。拉希德觊觎莱拉的年轻美貌,不惜请人来欺骗莱拉,告诉她的男友塔里克已经去世。走投无路的莱拉为了腹中塔里克的孩子,答应嫁给拉希德为妻。
两位出身和背景截然不同的女主人公同时落在了同一个丈夫手中,饱受丈夫的摧残与蹂躏。最初两人是仇视对方的,可是在长期的折磨中,两个人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她们像姐妹、像母女、像朋友,她们共同承担家务,为对方被打而心痛,共同抚养莱拉的孩子。两个人曾经试图逃跑,却被陌生人揭发遣返,回来又是一顿更为残暴的折磨。玛利亚姆的隐忍逐渐发生了变化,她在意莱拉的生命胜过了自己。终于,在莱拉被拉希德打得奄奄一息之时,玛利亚姆用尽了平生所有的力气用铁锨砸向拉希德。
玛利亚姆因为对莱拉的爱而反抗,虽然被处以死刑,但她心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一个从出生就被人耻笑的“哈拉米”,最终成为一个为爱而战的勇士,成为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之花。
这本小说意识流手法运用娴熟,在叙事方式与结构上别具一格。玛利亚姆和莱拉的苦难生活各成章节,穿插出现,相得益彰。拉希德的专制和暴力构成了对两个女性的直接灾难,然而在他背后,还有战争、贫穷、疾病对这个群体进行更大的迫害。塔利班掌权时期,他们极端的宗教政策对女性尤其苛刻,他们禁止女性工作、受教育。书中莱拉生产的时候,接生的医生都被要求穿着布卡工作,医生只能拉上帘子偷偷拿下布卡。
《灿烂千阳》是一部充满女性关怀的小说,表现了作者对阿富汗女性苦难命运的同情,对男权思想的批判。这本书尽管极力刻画女性生命中的苦难,但每一段悲痛的情节中都让人看见希望的光芒。两位主人公在苦难中挣扎、极力反抗,这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在为读者带来震撼的同时,也带来了慰藉和希望。

17世纪诗人赛博依描绘喀布尔说“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我想这一千个灿烂的太阳便是绽放在苦难中的花朵,她们坚强、美丽,她们越来越勇敢,越来越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