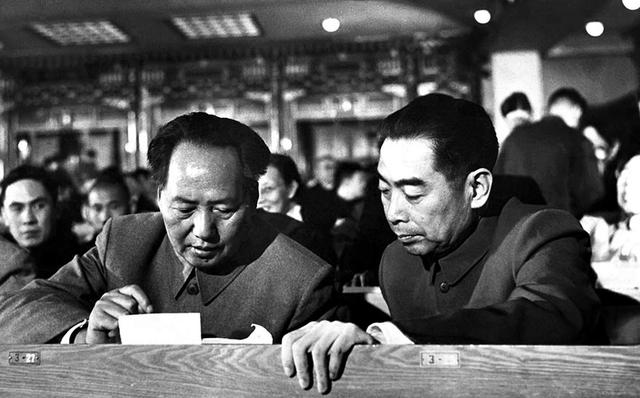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历史的第一页是从互相猜忌、搞阴谋和耍手腕开始的。(米·左琴科《一本浅蓝色的书》)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汉·许慎《说文解字》)
——————▼——————

背景图片《长城闪电》(摄影/杨振武)【如有侵权通知我们随时撤下】
▍崇祯王朝的人与事】
▎“荣华我已知庄梦”:袁崇焕冤狱】
▶阅读提要◀
皇上越是深信不疑恩宠有加,袁崇焕就越是如芒在背懊恼不迭。一场召对下来,冷汗竟至湿透了内衣……内致猜疑,外遭离间,袁崇焕好像有第三只眼睛,事先就看出了自己日后的遭遇,可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作为帝王的驭下之术,崇祯当然不是始作俑者,也不会是最后的终结者,他的无师自通挥洒自如出神入化只能让我们叹为观止自叹弗如。
只有一点疑虑:天子金口玉牙一言九鼎,却怎的前矛后盾出尔反尔以至于此?
——————☟——————

后金的队伍在游猎三天后在等待,等待科尔沁蒙古军队组成联军
——————☟——————
☜五☞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崇祯二年的六月初,同年十月初,后金皇太极就率近十万精兵,借道蒙古,开始了崇祯即位后对内地的第一次大规模袭击骚扰。
这个时间表一开始就让人有了想法:
怎么这么快?
怎么这么巧?
其实,继努尔哈赤之后登上后金汗位的皇太极一直磨刀霍霍,觊觎中原。
袁崇焕重返辽东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引起皇太极的极大关注,再后就变成了不安:
上任伊始,袁崇焕就合宁远、锦州为一镇,命祖大寿驻守锦州,以中军副将何可纲为都督佥事驻宁远,又调蓟镇总兵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以三层设防的部署表达了不让后金西进一步的决心。
当然,要仅止于此也不至于让人太过担心,问题在于,重返辽东的袁崇焕不再是昔日小小的宁远道,也不是只管辽东一地的巡抚,而是手握重权,辖区囊括蓟州、宁锦、天津、登莱还有东江诸岛,掌控水陆二十多万兵马的兵部尚书兼督师,他要真有什么动作,那可就是腹背夹击,大金可就岌岌可危了!
在皇太极看来,袁崇焕心狠手辣,当年只是个小小的宁远道,就凭着区区两万兵马,将宁远城变成了一架绞肉机,不仅挡住了先汗王努尔哈赤纵横辽东四十年所向披靡的马头,并最终使他身负重伤,“满恚而毙”。
也是在宁远城下,当时还是个贝勒的皇太极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亲身领教了袁崇焕战法和袁军红夷大炮的厉害。
总之一句话,在皇太极看来,袁崇焕一日不除,大金国就一无宁日!
作为应对之策,皇太极以联姻加盟誓加封赏的办法,加紧了对长城北边的漠南蒙古诸部的笼络,既是给大金国门再加一道保险,也是为日后跨过长城饮马黄河预留一道走廊的意思。
后来他就接到了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报告。
和远在北京的崇祯一样,接到报告的皇太极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很明显,袁崇焕这是要统一事权呢。
此举不是向大金大举进攻的预备动作又是什么呢?
用兵之道,原本就在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制敌要害。与其被动应敌,不如主动出击。还有,毛文龙新死,东江诸岛必定人心不稳,大小将领也都是泥菩萨过河,自顾不暇的他们还能有心思干别的吗?
像一头梭巡山林机敏万分的东北虎,皇太极几乎是凭本能就嗅出了其中的战机,再加上他麾下还有范文程那样熟悉汉地风情文化的原本就是汉人谋臣。
一番密谋之后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调兵遣将,兴奋难捺的皇太极甚至要御驾亲征。进军路线当然要好好谋划一番。
既然山海关外袁崇焕有三层防线,那就绕开好了。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和原因,明朝人叫长城为边墙,颇有些不太拿它当事的意思。因此“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也就在所难免。
长城那边是蒙古,而蒙古又是大金的盟友,别说借道了,就是借兵他们也没二话。
而最为关键的是,由长城乘虚而下,别说北京城里的崇祯皇上了,就是宁远前线的袁崇焕也想不到。
咱们这次就是要拿他说事儿,就是要让他哪怕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楚他自己!
依计而行,皇太极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沈阳,亲自率领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以及多尔衮、多铎等贝勒,还有谋士范文程,在六万八旗兵丁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出发了。
那一天是大明崇祯二年也是后金天聪三年十月初二。
皇太极领兵进入蒙古之后,一路顺风顺水,被借道的蒙古奈曼、熬汉还有喀喇沁部都派出兵力加盟随征,大军很快就增至近十万之众。
十月二十四,大军到达长城龙井关外。
在龙井关和与它毗邻的大安口,满蒙联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很快就破关而入,于十月三十会师长城以南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
遵化城距蓟州一百五十余里,纵骑一日可达;距京城也不过两三百里,要不了两天即可兵临北京城下。
铁蹄杂沓,狼烟滚滚,接到警报的北京城于十一月初一宣布戒严。
——————☟——————

现在给袁崇焕的造型——他震惊皇太极联军越过长城之余心里怎么盘算的呢?
——————☟——————
☜六☞
不论崇祯还是袁崇焕,这一惊都非同小可!
震惊之余,崇祯敕令刚从乡下老家奉召而来、征尘未洗的老将孙承宗以兵部尚书身份率领京营二万兵马驻守通州,阻止八旗兵丁进犯京师;敕令大同总兵官满桂、宣府总兵官侯世禄率兵勤王,并急令蓟辽督师袁崇焕挥师入关,保卫京畿。
获悉敌军来势汹汹,深感震惊的袁崇焕也是章法大乱,他甚至没想这仗是否还有别的打法,就先派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为先锋,率军前往救援。
早在上任之初,为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三人的调防,袁崇焕就在崇祯面前表过态:
“此三人当与臣始而终之,若届期无效,臣手戮三人,而以身请死皇上。”
赵率教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接令后火速驰援,于十一月初三在遵化城外与敌激战,中箭阵亡,全军覆灭。
袁崇焕自己于十一月初五率部进关,进行增援。
攻下遵化的皇太极马不停蹄,又于十一月十三攻克蓟州,然后继续挥兵西指,连克京师东部屏障三河、香河、顺义、通州等县。
袁崇焕率部于十一月十五赶到通州附近的河西务,与诸将计议前往北京。
在此之前,袁崇焕已经连出昏着,本应在蓟州一带阻击敌军,争取在京师外围展开决战,他却率部跟蹑?
现在又要退保京师,怎么看怎么像是纵敌深入,意欲将战火引到京师门外。
现在我们可以站在袁崇焕的角度想一想了。
最初的震惊过后,对皇太极的突然犯境,袁崇焕心里有没有一点儿窃喜,有没有一点儿借敌军大兵压境之际和皇上讨价还价的意思呢?
袁崇焕早已成了民族英雄,葬着他头颅的地处北京东花市的坟茔遗址也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的这种推测很可能会犯了众怒,但联系此前此后袁崇焕的所作所为,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这么说。
我们无意佛头着粪,我们只是明白,袁大督师的处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啊!
“五年平辽”是袁崇焕在皇上和满朝文武面前夸下的海口,但他几乎是立刻就后悔了。可覆水难收,他又必须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如今敌军轻而易举就兵临城下,不正说明五年平辽的不可能和不现实吗?
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打了多年交道的袁崇焕不会不知道,凶悍的八旗兵丁擅长野战,攻城破隘却非其所长;
况且京师城坚墙厚,又有勤王兵马四处云集,京师之战恰好就是以我之长攻其所短,最终只能是有惊无险。
只是袁崇焕没有料到,皇太极此番出动,几乎全是冲着他来的。一个又一个连环套般的陷阱已经都替他挖好,就等着他自己往里边跳了。
更何况他已经有那么多把柄攥在崇祯皇上手里。
他为什么要那么急切地将整个辽东地区的军政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光巡抚建制就撤了两个?
他为什么要大搞顺昌逆亡的把戏,不容分说就杀了毛文龙?
以前诸多的蛛丝马迹现在都盘缠一处,纠结成一张让人狐疑不已的大网,终日萦绕在忧心忡忡的皇上心里,且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更何况还有流传在京城皇亲国戚朝中权贵富商巨贾之间的各种小道消息。
就是在京师人心骚乱一夕数惊的情况下,屯兵京师北边德胜门的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与来犯之敌展开了血战。
也是那一天,袁崇焕领着祖大寿率两万宁锦铁骑在京师南边广渠门外也与皇太极殊死相搏。
同样都是打仗,满桂与袁崇焕的待遇却并不一样:
满桂苦战城下,城上守军发炮相助,被误伤的满桂和他的兵丁得以避入德胜门瓮城稍事喘息;
苦战于广渠门外的袁崇焕、祖大寿却得不到城中守军的任何帮助,他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袁崇焕几次负伤,却始终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来自己方阵营的猜疑和敌意至此已表露无疑,而皇上这时也要召见作战有功的人员。
为了那次召见,袁崇焕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他甚至没有穿自己二品大员的朝服,而是一身老百姓青衣小帽的打扮就进了宫——与其让皇上下令锦衣卫扒了自己的朝服,还不如自己先脱了的好。
但皇上那次并没有责怪于他。皇上甚至还解下自己的裘皮大氅给袁崇焕披上了。
当然,对他极力渲染的局势如何如何危急,敌军又是如何如何不可抵挡的耸人听闻的言辞,皇上也没有表态,尽管他还别有用心,散布说皇太极此来是要做皇帝的话让朝臣惊疑不已,但皇上就是不肯就局势表态。
慑于皇上的威严,袁崇焕到底没敢提出已在舌尖滚了几滚的和议之事,只是向皇上提出:
连日奔波征战,士卒马匹均疲惫不堪,可否援引满桂进德胜门瓮城先例,也进城休整一番?
皇上却一口回绝了。
披着御赐的裘皮大氅,袁崇焕心绪复杂,浑身也忽冷忽热像打摆子一样。
这不能怪袁崇焕多心,春寒、秋暖、君宠、老健原本就是人尽皆知的最没谱的事情,可他又一点办法也没有,真的没有。
✎待续ღ
——————▼——————
【每周二、四、六发布 敬请关注】
更多阅读 点击链接
作者:蔡磊 郑泉宝
编辑:@云山
配图: 杯子
校对: 绿篱
——————▼——————
【免责声明】
本文选自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明日落——崇祯王朝的人与事》,经过作者蔡磊、郑泉宝授权网络发布。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信息,否则视为侵权,作者保留追责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