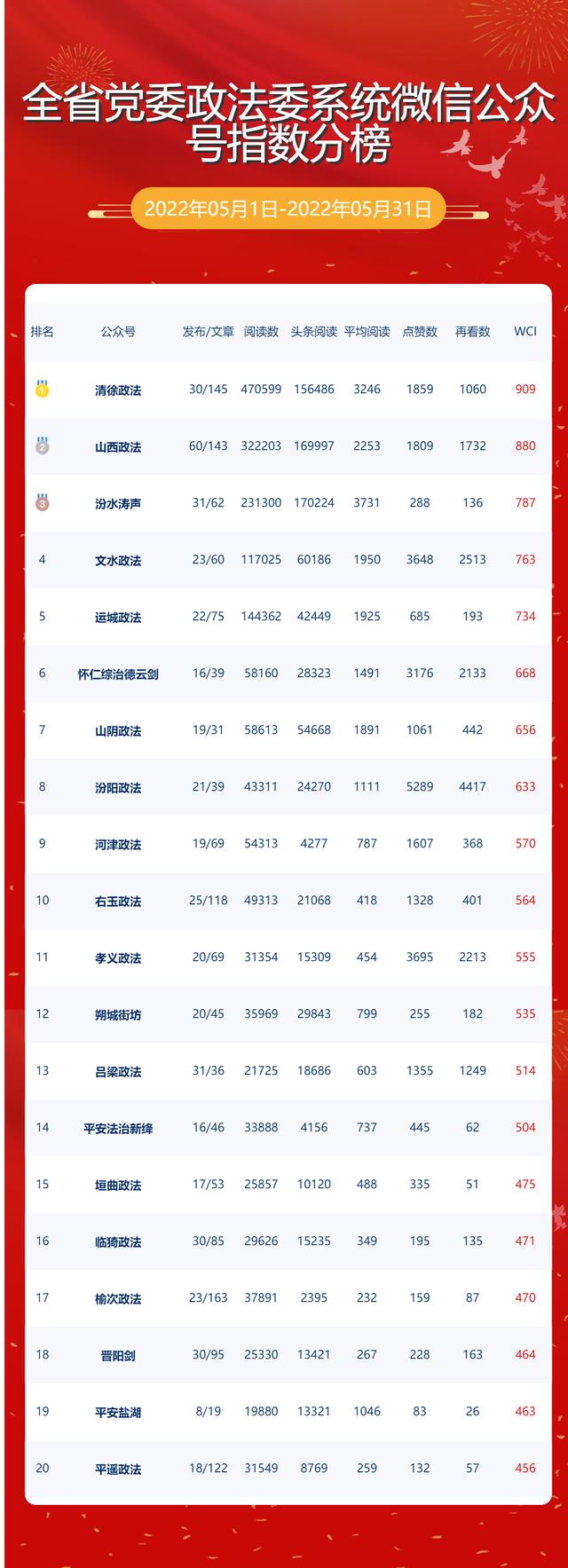导语:戏剧场景的结构与呈现是编剧和以导演为主的演出者沟通与交流最主要的桥梁,是戏剧创作中作为虚构的故事空间和物质的叙事空间发生关系的重要环节。编剧建构场景、编织场景结构,演出者赋予场景物质的表象。场景结构是由场景与场景间的关系形成的。
李宗熹戏剧叙事空间的构成受到其戏剧中场景结构的复合化、开放化和内心化的制约。复合化与开放化源于需要呈现的场景数量的多,内心化是因为作为戏剧行动的场景不是单纯的外在环境空间,而是经过剧中人物的主观过滤后生成的具有环境空间状貌的内心空间。
李宗熹戏剧中的故事空间,其建构方式绝大部分属于第一种,由此其戏剧作品便传递出了一种生活化的意味。这种故事空间的写实意味并不会因为叙事空间的变形或场景结构的繁复而有太多的消减,顶多是被遮蔽和悬置。
一、戏剧空间构成层面1、故事空间
戏剧是一门叙述故事的艺术,所叙述的故事不仅具有故事时间的层面,也具有故事空间的层面。故事时间是故事事件持续的长度,故事空间则是故事事件发生的环境,其主要的构成单位是一个个场景。
在戏剧艺术中,故事空间一般来说是由剧作家建构的,剧作家使用的媒介与小说家一样是文字符号,因此,故事空间在本质上也是需要想象的。
戏剧舞台叙事时,其媒介的物质性要求戏剧叙事不仅需要剧作家创造的故事空间,还需要由以导演为首的戏剧演出者建构的舞台叙事空间。

话剧《四世同堂》空间环境展示剧照
故事空间中只有那些在舞台叙事空间里被呈现出的场景,才能被观众直接感受,进而引发想象。这样的场景是剧中人物活动的场所,是戏剧事件发生的场所,也是戏剧场面的主要构成部分。本质上说它是不出场的,可因为被舞台叙事空间进行了呈现,于是又具有一定的直观性,因此被呈现的场景是故事空间中特殊的构成部分,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价值。

话剧《大酒店套房》舞台空间设计
对于戏剧场景的结构和呈现沟通着戏剧叙事的故事空间和叙事空间,场景本身可分为主体场景、相连场景和关联场景,作为剧中人物主要活动场所的场景是戏剧的主体场景,一般来说,这一场景必须在叙事空间中呈现,否则戏剧行动无法发生,围绕在主体场景前后、左右、上下3个维度延伸的场景是戏剧的相连场景。
相连场景与主体场景间形成某种关系,有利于调度剧中人物的上下场,使主体场景中的人物关系产生相应的变化,增强戏剧性。
它可以被直接呈现,也可以不被呈现,通过暗示供观众想象,至于关联场景其与主体场景的距离相对来说更加遥远,它打开的是事件发生的更加广阔的世界,剧作家会使用剧中人物的远距离位移、台词等方式将其暗示出来,它一般不被舞台呈现。
2、叙事空间
作为戏剧叙事物质基础的叙事空间,直观性是它的本质属性,在高度写实的戏剧中,叙事空间的直观性等同于视觉效果的生活逼真性,这时被呈现出的场景的想象性与叙事空间的直观性和视觉的逼真性高度融合在一起,令人难以分清。
在这样的戏剧作品中,主体场景往往不可过多,这是因为在视觉逼真性的限制下,在一定的叙事时间中进行高频率的场景切换是不切实际的。

话剧《大过年》叙事空间设计
戏剧不如电影灵活,也不如小说自由,但是当戏剧场景舞台呈现的视觉逼真性的限制被突破时,灵活的场景切换便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有利于戏剧的叙事结构走向多元,也向叙事空间的呈现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以导演为首的戏剧演出者有了其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舞台分区、舞美变形、灯光布景、虚拟表演等舞台语汇成为戏剧舞台上最为常见的风景。
这些叙事空间的组织方式既可以为呈现场景服务,也可以遮蔽场景,表达演出者自己对戏剧故事的理解和评判。
二、戏剧作品里的叙事1、叙事空间的展现
李宗熹作为一个在大陆接受戏剧导演教育的台湾导演,他在叙事空间的视觉造型和调度都有所涉及,如在他耳朵《守岁》和《又见老爸》中都有比较写实的还原故事空间。
这种写实风格的叙事空间使戏中的演员在大多数的故事叙事时间里,可以保持与日常生活中的人类行动保持着相当的视觉一致。
在话剧《师父》中,逼真的模拟性造型仍占据着视觉风格的主流,但是在灯光的切割与变换下,叙事空间便显现出了其功能性的特征。

话剧《师父》剧照
《师父》故事讲述了3个被困银行的抢劫犯,在进行回忆和内心挣扎时,舞台上搭建的3个房间变成了他们剖白内心世界的平台,同时,灯光使原本不透明的墙壁变成透明的纱幕,纱幕后是已经重换了的天地,演员在其中进行虚拟化的表演。此时叙事空间的逼真性被遮蔽,功能性破壳而出。
这种转换在话剧《频率》中同样如此,在灯光的变换下,叙事空间原本建立了一个模拟的电台直播间,这个空间变成了供演员表演的功能性场所。

话剧《频率》剧照
在话剧《求偶》中,舞台两侧的长椅与舞台中心两道半圆形的由低到高的楼梯转台以虚拟的方式模拟上海人民广场的空间环境。当转台转动、灯光变换、音乐响起时,舞台便时而成为演员表达情绪的功能性场所,时而成为火车车厢的模拟性暗示。
当转台合闭,台顶一道道尖角的防护栏和转台垂直面上的矩形方框又点染出"家"的意象,"家"门封闭。
此时叙事空间在模拟"家宅"的同时,对"求爱之路艰难"的意蕴和主人公庆庆悲伤的心境进行了出色的阐释。
在话剧《邮差》中,叙事空间营造了大面积的虚空,这种虚空会随着事件的变化并通过道具的填入,较为真切地模拟出家宅、医院、部队、广场等环境。如果说叙事空间是大实小虚的话,那么《邮差》则是大虚小实,虽然如此,实体仍是空间的主体部分,是演员表演的主要场所。

话剧《邮差》剧照
在话剧《移动的幸福》中,舞台左侧逼真的"山腰上"邮局与右侧呈"之"字形重叠而上的几何形山坡就一左一右并不突兀地交融在一起, 演员的表演便也在左侧的写实与右侧的虚拟间来回跳跃,呈现出一派虚实相融的景象。
2、李宗熹作品里的叙事空间
除了以模拟性造型为基础兼容其他两种造型的叙事空间的构成方式外,李宗熹在他少数戏剧中尽力剔除了模拟性的叙事空间,朝着功能性与阐释性的相融方式。
这在话剧《我的祖宗十八代》中显现得最为明显,戏一开场,舞台后方的一棵由《朝代歌》歌词中的汉字拼成的大树作为主要场景,舞台上3个插着刀的木桩,前二后一,呈三角形对称摆放。其实在话剧第一幕的时候是看不出这里是演奏会的后台,也看不出这里将会是武馆、大街、皇宫、妓院、渔船等,只有天幕下的大树些许有点桃树的意思。

话剧《我的祖宗十八代》剧照
因此这出戏的叙事空间是极具功能性的,在这个功能性的舞台上,演员的表演也极尽虚拟夸张之能事,动作的视觉逼真性成为有限的组成部分,戏剧将近尾声时,那棵矗立的大树显现出了它存在的意义。
这棵树更接近阐释性造型,它除了在外形上模拟一番桃树的形象外,真正起到的作用是象征世事沧桑、朝代更迭里情义的永恒不灭。
可是这样的叙事空间并未完全遮蔽故事空间,或者说这样的造型设计是为了让演员通过虚拟的表演更明确地将舞美造型无法逐一逼真还原的场景暗示出来,它的虚终究为着的还是实。
三、场景结构的复合化、开放化与内心化1、复合化场景的体现
李宗熹戏剧复合化的场景结构是从同时性角度进行组织的,复合化的场景结构源自不同场景的同时出现,可分为家宅式和群落式两种。
所谓家宅式就是这种场景结构是关于家宅的,在这里家宅是表现戏剧事件主要甚至唯一的环境空间,复合化家宅式场景结构不同于曹禺《雷雨》、《北京人》等剧中的单一家宅场景结构。
在曹禺的《雷雨》中,描绘的家宅场景仅是家宅中一个单独的房间,如周家客厅,至于与其相连的其他场景如周繁漪的卧房、周朴园的书房、餐厅、花园等只被暗示,不被细致描绘,不作为人物展开具体行动的场所。

话剧《雷雨》剧照
李宗熹戏剧中的家宅场景则突破单一场景的限制,走向复合结构,表现为一栋完整的家宅。这个家宅由几个房间组成,每一个房间都能作为人物展开行动的场所,这样的表现形式在他的作品《守岁》和《又见老爸》体现的格外明显。
《守岁》的场景由左厢房、客厅、右厢房三间屋子以及一间厨房结构而成,《又见老爸》里的场景则是由楼上两间卧室,楼下客厅、车库和厨房结构而成。

话剧《守岁》剧照
这些小环境之间既可彼此沟通又能相互独立,这样的场景结构不再单一,而是复合的。这种场景结构的设置是有目的的,它有利于展示家人间的误解、隔阂,比如房间的彼此独立可使得隔阂具象化,又有利于误会的解除,同处于一个屋檐下,相互误解的人有机会听到他人间的谈话,化解矛盾,同时这样的场景结构对戏剧氛围的渲染有极大的帮助。

话剧《又见老爸》场景
群落式复合化场景结构不同于家宅式,群落式复合化场景结构的覆盖面积远远大于家宅,其需要呈现的场景集合不再限于几个房间。
如在李宗熹的《移动的幸福》一剧中,戏剧呈现的场景集合是一个山村,不仅有山腰上的邮局,还有山峰,以及山中的房屋,这远远超出了舞台叙事空间所能逼真还原的范围。因此在面对这样一种场景的开放化结构时,李宗熹使用了模拟性造型中虚实结合的叙事空间,实的是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的邮局,虚的是山坡和山坡中的房屋。
2、场景结构开放化
复合化的场景结构作为同时性的场景集合,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历史性的开放化场景结构却不是如此,其描绘的场景随着戏剧叙事者视点的转变、剧中人物的行动或讲述不断地发生变化,使戏剧行动的进行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环境。
《求偶》这出话剧就是如此,女孩庆庆从安徽老家前往上海追寻爱情,涉及的场景有家乡的火车站、上海人民广场、公墓、西藏等,这样的场景结构使舞台叙事不可能逼真地做到逐个还原。

话剧《求偶》场景
因此只能在舞台上营造虚空或搭建功能性的造型,继而配合道具以及人物虚拟性的表演将不断变化的场景展现出来。
复合化和开放化的场景结构并非不能兼容,特别是在开放化场景结构中,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环节的场景本身也可以呈现出复合化的倾向。
不过在复合化场景结构中也可结构出新的复合化场景,只是结构中的场景不再是本身作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的主体场景和相邻场景,而是有相当距离的关联场景。
这在《频率》这出话剧中有所展示,其进行转换的支点是打电话通过电话将远方的场景暂时性地融入原本的环境空间中。在叙事空间里,这一被融入的关联场景多通过灯光分区呈现。
3、场景结构的内心化
"20世纪世界戏剧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走向人物深层心理的直接表现。"如果说复合化、开放化的场景结构是由多个场景在同一空间维度中结构的话,那么内心化的场景结构就是一种在不同空间维度里的结构组织。

话剧《邮差》场景
这种内心化的结构依附于戏剧故事中的外在环境,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使内心的场景出现在外层场景之中,作为戏剧舞台叙事需要呈现的主要场所。
李宗熹建构内心化的场景使用最多的方式是人物回忆,而使用得最优秀的一种却是具有些许超自然倾向的穿越与轮回。
如《邮差》中的林和平诉说自己的一生,最外层的场景是他讲述动作发生的场所就是他的家,占据叙事主体的则是他回忆中的过去的场景,这种回忆中的场景以开放化的结构展开,成为戏剧叙事空间需要呈现的主要部分。
四、话剧的单一化现象1、故事空间的单一化
李宗熹说过这样的话"有很多创作者常常会借创作来填补心里的缺憾,或者作为对于自己的一种治疗。我的家庭是非常不健全的,所以我对家的温暖的渴求是很高的。我借由创作来弥平心里的缺憾,因此会有很多题材想到家,想到亲情,这是我最缺的一块。"

李宗熹
或许是要弥补自己心灵的缺憾,而这缺憾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经意间错过的,于是他的戏总会给人一种温柔的抚慰。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憾。缺憾在于太过执着,这执着造成的就是李宗熹的"单一性"。
执着于琐碎,执着于回顾,执着于弥补,执着于亲情、爱情、友情等人世间细小的温情,使得李宗熹的故事空间的范围和性质往往只能局限在小小一隅。

话剧《邮差》场景
如在话剧《邮差》中,李宗熹就把世界通过压缩的方式与主角林和平的人生场景结合在一起叙述,因此该戏不仅有林和平的个人线索,也有社会历史的背景线索。如此林和平的人生际遇便套上了一层社会时代的色彩,将戏剧的主题意蕴引向更广阔的天地。
如果说李宗熹戏剧故事空间的单一化只是因为关联场景的缺失的话,这未必就能算得上他戏剧创作中真正的缺憾,因为温情的戏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2、人物设置单一化
事实上故事空间的单一化不仅仅源自其范围的狭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来自李宗熹对于场景中人物设置的单一。
乍一看,人物设置似乎与故事本身的关联不大,但是人物的设置及在场景中的人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故事空间的性质。

话剧《胭脂盒》剧照
李宗熹大多数的戏剧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经济状态、文化涵养的区别有多大,都有一个相似的属性,就是他们都认为人世间的感情大于一切,即便有些人物并不完全认同,最终还是臣服于此,这就使得他设置出的故事空间的性质时常停留在单纯的"情"上。
因此解决戏剧矛盾的前提条件,往往建立在世界本就为情而生的基础上,换言之就是建立在对手本质上是好人的基础上。故事空间性质的封闭,造成了戏剧主题的单一,因此戏剧矛盾的形成多数时候是通过不知情与误会等技法造成的,与人物的性格、信仰、社会身份等的联系不够紧密。
结束语:李宗熹戏剧叙事空间实中融虚的多元化更多是其戏剧作品的外部表象,其场景结构的复合化、开放化与内心化既影响了戏剧叙事空间的构成表象,也为戏剧行动变得生动活泼贡献了力量。
影响叙事空间构成表象和场景结构的核心在于故事空间的设置,生活化的设置使李宗熹的戏剧贴近了温情,而单一化的设置则使他的温情不够深刻。
李宗熹的戏剧作品的缺憾不只是其个人的缺憾,也折射出当代话剧的缺憾,人物设置单一导致的故事空间的扁平,制约着话剧的发展,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使话剧发展的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汤逸佩《空间的变形中国当代话剧舞台叙事空间的变革》
李文君《重拾生活中被遗忘的情感台湾戏剧表演家剧团创始人李宗熹》
孙正国《论媒介建构故事的空间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