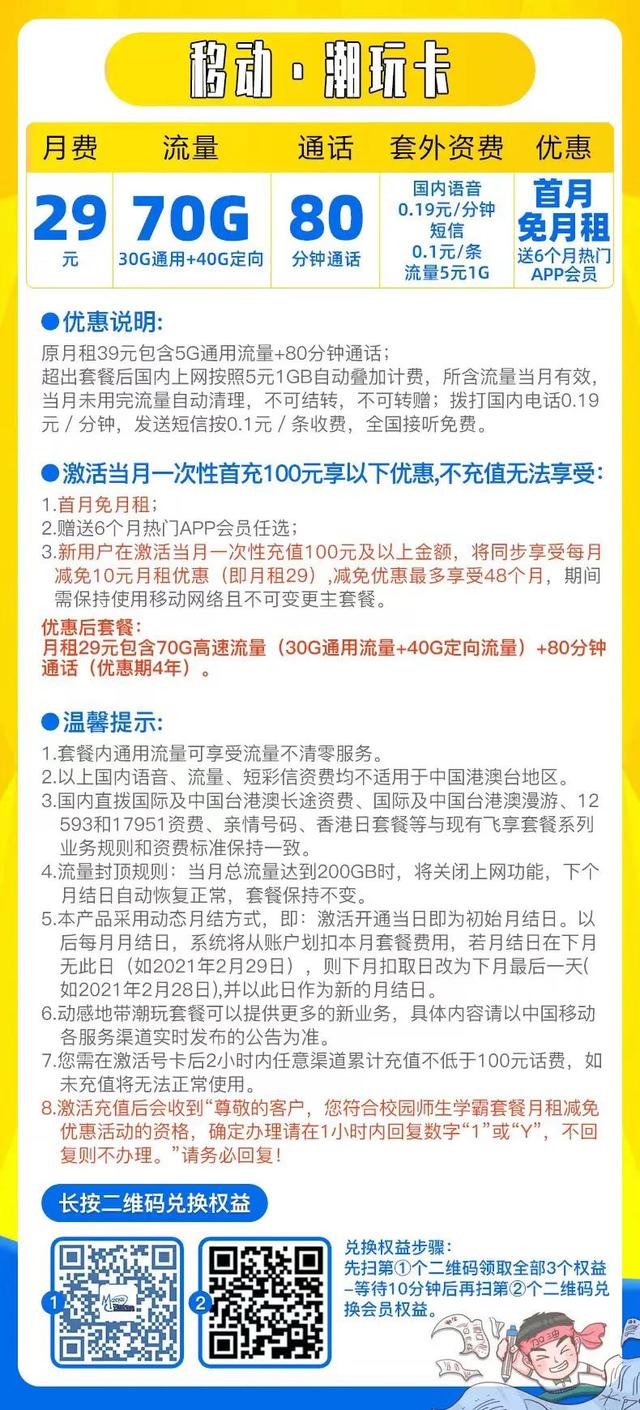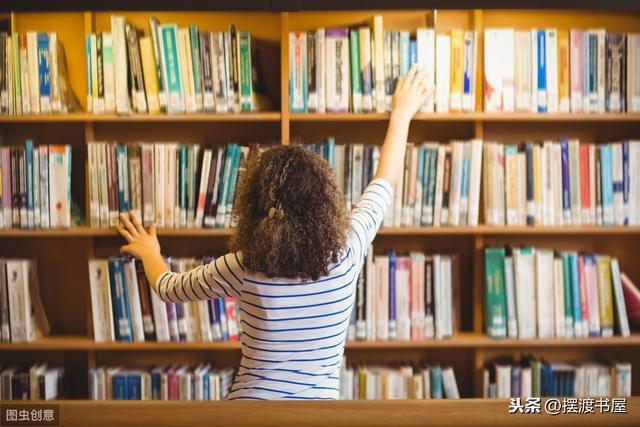自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建立以来,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专业能力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商业组织,一直在扩张自己的行为领地。
随着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日益集中,商业组织正极大可能地吞噬着一切以个人形式存在的经济行为及其经济领域。
即便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也大多数被纳入各类自治或半自治的经济合作组织中,家庭农户演变为农场组织,个体农户或个体工商户联合而成经济合作社或集体工商企业,以便籍此取得现代经济行为所不可或缺的法律主体地位。
这种趋势与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对经济行为自由实施保护的法律特许有关。
因为“国王的专权”在被自由主义者的“法律专权”取代后,没有法律专权许可的经济行为,会由于失去来自于法律的“特许权”和“自由权”而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

一、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特别法律地位
在近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各国《公司法》均将这些特权赋予商业组织,并使商业组织取得了相对于自然人的经济行为优势。
如美国标准(示范)公司法第三章(目的和权利)对公司设立的目的、公司拥有的一般权力、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超级权限等进行了规定和约定,意在给予公司经营者足够法律授权的同时,使其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管辖。
德国《商法典》(HGB,1897年颁布,2003年最新修订)及《有限责任公司法》(GmbHG,1892年颁布,2002年最新修订)、《股份法》(AktG,1965年颁布,2003年最新修订)、《自由职业人员合伙公司法》(PartGG,1994年)、《工商业合作社法》(GenG,1994年)等,对公司设立条件、股东(投资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组织结构及权力规范、章程及修改章程要约、解散及清算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和法律授权。
在近代以来的商业法律中,或许最重要的是英国人在19世纪确立的公司享有独立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原则。
该原则确认,股东作为公司设立或公司资本(及债权)变更的出资人(投资人),一旦其出资以公司股份做了对价认定,该出资所形成的公司财产(资产或资本)的所有权便只属于公司,而与出资人脱离财产所有者关系;
即:股东虽然是公司的所有权人,但对公司的财产没有所有权,它只能按其股份比例以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取得公司经营利润的分享权、参加股东会议及议事投票权、公司清算之财产分配及剩余价值索取权、公司经营管理及资产负债表的内部知情权、非限定优先认股权等。
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这一特别法律地位,使它获得了远超其商业组织属性的诸多特权。
其中有三项特权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使股东或公司的经营者可以在这一法律地位遮掩下,获取相对于普通人的特别利益:
一是股东通过所设立的公司获得自然人所不具有的对雇员进行组织管理、监督其工作行为的法律保护,这种保护为公司一致行动人滥用内部规则对雇员进行经济强制或薪资胁迫提供了前提;
二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可通过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或使公司独立人格空洞化,作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或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的工具;
三是以公司之名招募新股东、新资本,以形成更大的资本行动能力,通过在公众市场或公开市场上操纵经济物品的交易量、交易价格或交易时效,来获取不正当利益。
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银行资本家、大商人及其财团往往通过主导立法,获得巨额工程项目或社会事业的专营权。

二、公司法律特权与科斯定理假说
正如哈耶克所说,现代经济的发展使个人在增加财富或获得职业机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以财富向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高度集中、非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财富占比相对减少且经济行为能力相对孱弱为代价的。
可以说,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所具有的一切优势,正建立在自然人的经济行为能力因法律强制和来自公司的经济胁迫而被弱化的基础上。
公司越多越大,资本越集中,受雇于公司的自然人(雇员)的行为自由就越小。
现代社会在自由问题上的悖论,如同哈耶克错觉那样,来源于个人财富的增加等于社会普遍进步的假说。
正如科斯认为的那样,为实现社会的普遍进步,需要减少或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且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可通过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并允许他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并赋予他管理和组织生产要素的权力,以便通过“内部”协调而不是通过市场,以契约方式获得这种可能性来实现。
科斯认为,这种赋予“权威”(企业家)以特定权力——如某一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不必与企业内部同他协作的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而是用一个契约(按:劳动契约)来替代①——的做法,对社会而言是必须且必要的。
在这样的假设下,“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它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浮动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②,同样也是在为社会普遍繁荣而做贡献,因此让渡个人的行为自由、服从企业家的指挥,也是合理而必须的。况且,科斯相信,这样的雇佣契约,“本质仅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力范围!”③
如果说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法律特权有助于社会普遍进步的话,当社会交易成本趋于零时,这种进步会由于交易成本事实上不可能为零而遭遇自身的极限。
这时,股东的法律特权必然会由于极限的存在而到达它的最大限度:在由价格机制“组织”资源分配的专业化交换经济中,资源流向将完全依赖于买方(企业家)④,并由买方所主导。
这种情形衍生的一个社会后果是,因交易税课征而导致政府管制与法律特权的混同——因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交易税(营业税、增值税、关税、契税、消费税等)。
对股东法律特权的质疑,既来源于专业化经济交换中存在的上述事实,也来源于对科斯有关企业组织与交易成本之间关系所做的辨析。

在我们看来,企业家代替价格机制必要性的科斯说辞,不仅仅涉及交易成本问题,也涉及现代法律体系为什么会赋予企业家去支配他人工作权力的法律特权问题。
科斯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家不得不在较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这是鉴于如下的事实:他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总可以再回到公开市场。⑤
在科斯的理论中,企业家这个“权威”具有支配资源(诸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并通过组织内部协调以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的能力,并且他还具备一项特殊的能力,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因而,在专业化经济交换中,这样的“权威”自然而然地由于能低成本协调生产要素而获得指挥或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只要他通过雇佣契约为那些听从他指挥的人(作为生产要素)支付工作报酬即可。
科斯的这个推断,将企业家支配他人工作权力的特权归结为一种基于自由选择权的法律关系:企业家与作为生产要素的雇员所签订的雇佣契约,以及他可以在以低成本方式获得生产要素(雇员)和在公开市场上获得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基于自利的选择。
三、科斯假说与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理论》
科斯是从对比他更早注意到企业性质问题的奈特的质疑中坚信自己意见的。
奈特在1921年完成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认为,现实的经济过程由预见未来的行动所构成,而未来总是存在不确定因素;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决定做什么与怎样做比实际去做本身更重要;如果不能消除不确定性,经济过程或生产过程就会发生混乱。
避免混乱的方法是,需要由具有预测和控制能力、良好判断力和自信的人来负责生产和经营活动。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愿意承担风险,绝大部分人因为惧怕风险和不愿承担风险,而愿意交出自己对不确定性的控制权,前提是,将自己置于他人指挥下能获得稳定的工资安排。企业便是经济行为中存在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
奈特的分析过程如下:
第一,物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其基础是完全非个人的需求预测,而不是为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生产者承担了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第二,预测工作和与此同时的对生产的技术指导和控制的大部分会进一步集中在一小部分生产者那里,由此出现了新的经济工作人员——企业家……当存在不确定时,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任务相对于其实施处于支配地位,生产团体的内部组织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和机械性的细节。决策和控制功能的集中化是亟需的,一个“头领化”的过程不可避免。
在这种体制下,自信者和冒险家承担风险或保证动摇者和胆小鬼获得一定的收入,以此作为对实际结果进行分配的交换……出于人类的天性,我们知道,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的特定结果而没有赋予其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是不现实的和非常罕见的。另一方面,没有这样的保证,后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前者的指挥之下……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以及产业的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⑥

四、公司法律特权是“股东追求利润 资本扩张 政府税收强制”的产物
不管是像科斯那样将企业和企业家理解为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产物,还是像奈特那样将它们理解为不确定性和风险规避者自愿进行权利交换的结果,都事实上将企业和企业家的性质定性为生产团体追求利润(成本为负利润)的结果:
当不具备抵御经济行为决策的胆小鬼、或自愿以契约方式出卖自己并获得生产要素身份的人甘于将自己的权利出卖给那些承诺发给自己工资的一小部分人时,企业这个商业组织便诞生了,并且,由于这个商业组织具有减少全社会交易成本的伟大功能(普遍进步),而被法律授予企业家指挥雇员和以经济胁迫为手段管理雇员行为的特别权力。
这个特别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将雇员的经济行为自由交于企业或企业家去代行,并使雇员处于经济胁迫的威压之下而臣服于企业的内部制度。
奈特和科斯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精心构造的企业理论,与亚里士多德有关因为缺少理智而必须作为财产依附于有健全理智的主人的奴隶的理论如出一辙;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使企业和企业家获得法律特权的力量并不是专业化经济交换过程中所存在的经济胁迫事实,而是资本的力量和来自政府的因交易税征收而采取的保障股东(商业组织合伙人)利润增长的政治强制(或法律强制)。
企业这个商业组织并不是人们主观上为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或为了规避不可预见的风险而产生的,它是“股东追求利润 资本扩张 政府税收强制”的产物,在它的早期历史中,还包含着英国王权和议会以法律之名胁迫农民放弃土地的诸多故事。
如1235年的默顿法令、1285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15世纪中叶起,庄园佃农中的公簿持有农在土地被侵占后,可依据公簿持有地权益保护规则,向大法官法庭请求司法救济;为因应羊毛制品利润增长带来的圈地需求,1766英国议会通过私法圈地程序法案;1801年又颁布《一般圈地法》,规定圈地应以议会通过法令的形式进行;在18、19世纪中,英国议会共通过了4736件与圈地有关的法案。
或许,并不需要什么理论去解释企业的性质和产生缘由,企业这类商业组织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事实,不管有没有科斯定理,它都存在着;也不需要什么理论去解释股东或企业家法律特权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个问题,只要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立法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自由主义者构建的观念体系,企业及其股东(或其委任的经营者)的法律特权就会一直存在。

五、被商业组织法律特权裹挟的生产要素们
现在,我们来讨论企业中那些由动摇者和胆小鬼构成的生产要素们。
他们之所以会被认为是生产要素,大概与亚当·斯密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价格构成学说有关。
当然,比起科斯和奈特,亚当·斯密对劳动者有更多的怜悯,他至少在物品的价格中将劳动者的工资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明确提了出来。
这与英国和西欧庄园主们役使农奴们耕种、占有其全部劳动成果、提供其住宿和膳食的惯例相比,是一个明显“进步”。
当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纺织厂或煤矿的工人时,随着劳动场景的变化,他的劳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不再是土地和锄头,而是机器和以智力为基础的操作技能。
这种变化使他从锄头的主动操纵者变身为跟随机器运行节凑的技能输出者。
他原先至少还拥有在劳作的地块上操纵锄头的自由,现在却不得不与机器捆绑在一起,因为只要他离开机器,便会失去获得工资的可能。
他们就是这样与机器一起成为生产要素的。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2亿多农民工比较幸运些,离开机器和建筑工地后,他们还可以选择回家种地。
当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与资本、土地、机器(生产资料)、原材料、技术一起被视作企业运营必不可少的要素时,他就不再是具有感情、拥有法律权利的自然人。
除非他受到法律明确禁止的伤害,否则,他的自然人身份会隐匿于生产要素这个属性中,而需要接受来自于企业和企业家基于法律特权所给与的安排。
这时,他只是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或经济物品,他的价值(价格),等于其将劳动权利在协议的时长内让渡于企业和企业家时的应得工资。
这种出让一定时长劳动权利(及其劳动技能)从而获得报酬(工资)的社会存在,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谋生方式,也是强大的商业力量挤压非商业活动的必然结果。
在非商业化生活方式的时代,家庭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主要场所。
但随着近代以来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经济革命、技术革命等各类革命的兴起,家庭功能呈现萎缩状态,家庭的经济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只剩下养育子女、婚姻关系维系以及睡觉、休息这样的功能,对不要子女、不要婚姻的独身主义者来说,家庭概念已无关紧要,甚至厌弃家庭正是独身主义者乐于独身的主要原因。
与家庭功能萎缩同步的是社会组织的功能扩张,无所不在的商业组织、技术组织、政府组织、社会机构及其团体吸引了城市社区绝大多数人员,他们要在这些组织之外获得谋生的便利和行为自由,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六、家庭的经济功能让位于商业组织,使大多数人处于商业组织的经济胁迫之中
这或许便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在城市社区中,家庭的经济功能让位于商业组织,使大多数人处于商业组织的经济胁迫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中,个人生活活动的主要场景被分割为白天和晚上两个部分:
白天,在家庭之外选择加入某一商业组织或社会组织,为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而不得不臣服于组织的经济胁迫;
晚上,回到家中吃饭、休息和睡觉,并与婚姻关系中的伙伴和子女以家庭方式共处一室。
这种分裂型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有任何社会进步意义的话,那便是企业主和企业家们可籍此从合法的经济胁迫中获得超额利益的巨大进步了。
此外,他们从获得的利益中拿出一部分,以交易税和利得税的方式贡献于政府,使政府得以不断扩大规模、不断编制法律文件,以便促进日益分裂的社会(城市和乡村)和城市生活(白天的经济行为和黑夜中的家庭)走向更加彻底地分裂。
而企图连接白天和黑夜的城市中那数不清的霓虹灯,藉由金钱为放纵的物欲和情欲增添着华丽的光彩,就像经济学家们的语言那样,为现代社会走向分裂提供着理论和制造着思想。

七、商业组织对个人领地的肆意扩张迫使人类正进入经济专制社会
科斯有关生产要素权利行使的意见,建立在生产要素所有权和行为权利相一致的假说上。
科斯认为,商人得到和使用的实物,作为生产素,必然包含着对实物实施行为的权利。
在他看来,企业雇员作为生产要素,在他出让一定时长劳动权利的同时,他的劳动权利不仅归属于企业主,同时如何使用这个劳动权利也将成为企业主的权利行为,甚至包括做产生有害效应的事的权利也是生产要素(雇员)的权利属性。
他说: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应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正如我们可以将一块土地用做防止他人穿越、停汽车、造房子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它用做破坏他人的视野、安逸、或新鲜空气。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所蒙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逸或呼吸新鲜空气。⑦
当我们将一切有用的事物(包括具有劳动技能的任何人)均看作是经济物品时,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所有社会权利均可成为企业或企业家们交易的对象。
在科斯看来,拥有一种经济物品,就自动获得了该经济物品的权利行使权利,即使利用这个权利做产生有害效应的事,也会从法律那里得到许可并受到保护。
因为科斯们认为,只要承认私人财产的终极权利,便必须承认基于自利的权利行使行为的合法性,便必须承认企业主(股东)和企业家们对他用工资交易得到的雇员拥有使用和管理的权利;甚至当企业和企业家们为得到自身的利益,通过权利行使使别人蒙受损失或做产生有害效应的事情时,法律也必须保护其权益。
这种被概括为产权理论的权利原则,当然不仅仅是科斯们的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行为法律关系的核心原则。
在这种原则下,那些宣称自己对自然资源或国民共有资源拥有所有权的组织或政治团体,也自然获得了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权和管理权,且会通过法律制定使这一权利获得合法性。
但是,科斯有关所有者对生产要素行使行为权利的意见,不过是欧美人士基于自利假说的一种法律推断。
它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商业组织对利益和权利的诉求,却忽视了将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去认知的恶劣后果。
这不仅伤害了劳动者作为人的尊严,也同时损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或许更为恶劣的是,这种局限于权利观念的理论,助长了生产要素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正使人类社会走向商业组织的权利行使行为高于劳动者个人行为权利的经济至上状态。
可以预见,在这种理论影响下,现在和未来,人类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政治专制,必将为经济专制所取代。

八、摆脱人类文明危机的方法需要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共同承担企业经营法律责任
要解除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一危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将商业组织的法律特权置于有关国家宪法确认的“民主管理权”的约束之下,即:企业所有者必须与管理者一起承担企业经营的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商业组织对生产要素的权利行使行为,其法律责任不仅由管理者承担,同时应该由所有者(出资人)共同承担。
出资人作为企业经营利润的享有者,他不能独立于企业经营的法律责任之外,企业财产(资产或资本)的所有权不能与出资人脱离所有者关系,因为出资人不仅事实上按其股份比例享有着企业经营的净利润,也在事实上对企业的财产(生产要素)和经营行为拥有通常只有所有者才享有的最终支配权利。
不仅如此,企业所有者(出资人)还应对企业雇用的劳动者承担共同享有经营利润的责任,因为任何企业的经营利润中均包含着劳动者所拥有的对自身劳动技能的所有权的权利行使行为。
任何劳动者的劳动技能都没有、也不可能在一次劳动契约中全部地出让给雇用者,即使雇用者通过劳动契约承诺并得到劳动者确认的工资方式支付了对一定时长的劳动权利的对等购买,也不可能如此。

因为劳动者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他不仅贡献了其劳动技能和劳动权利,也同时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权利行使行为中,包含着属于他的那份对构成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的行为权利。
因为如果承认自然资源的全民共有权的话,不管这份自然资源在转化为生产要素过程中被如何公平地交易,都始终包含着所有者对这份资源作为经济物品所拥有的权利行使权益。
这份权益与任何政府的行政权的行使相关,并因为行政权的行使而使其具有的权利行使权益受到主权的终极保护,不管这份自然资源作为经济物品被交易了多少次,每次交易都没有灭失自然资源所有者所拥有的行为权利和权益。
【本文完】
注释
①[美]科斯著,盛洪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4年,第32-33页。
②[美]科斯著,盛洪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4年,第32页。
③[美]科斯著,盛洪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4年,第32页。
④[ [美]科斯著,盛洪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4年,第33-34页。
⑤[美]科斯著,盛洪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4年,第33页。
⑥转引自:[美]科斯著,盛洪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4年,第38-39页。
⑦[美]科斯著,盛洪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14年,第118页。
版权说明:本文的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或者引用本文内容请注明来源。本文图片或视频资料来源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