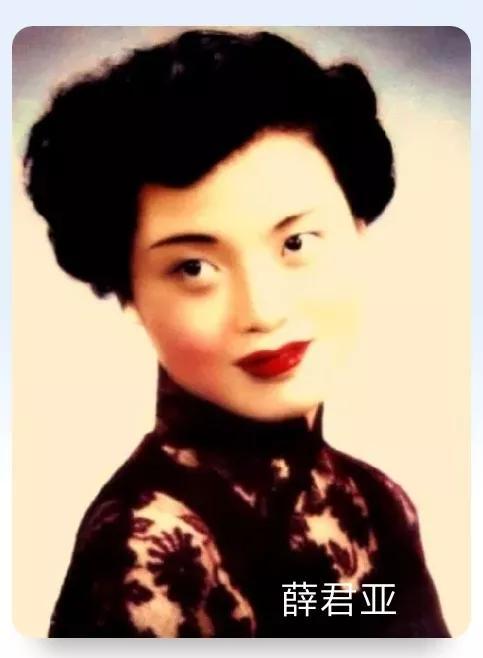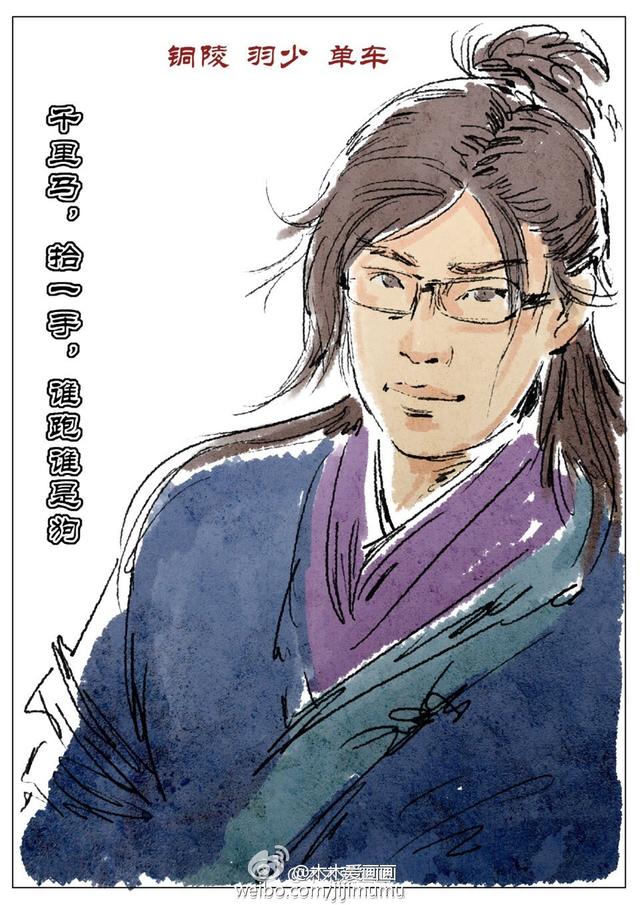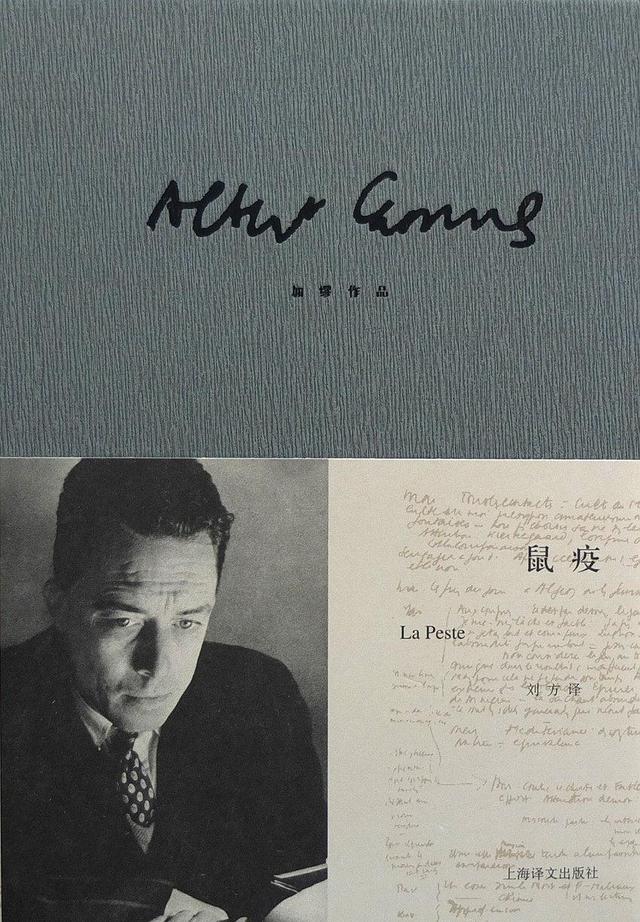我精心保存着一只精致的柳编工艺品——“圜子”。每当我看到它就想起我的奶奶来。就是这只圜子,它一直高高的悬挂在我的脑海中。

奶奶生于1912年民国元年,享年87岁。虽然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几年了,但她那和蔼的面庞、慈祥的微笑,慢条斯理的言谈举止,缠着一对小脚走路的样子,还经常活灵活现地进入我的梦中。
小时候,我们姐妹四人同爸妈一块挤在老院的一间小北屋里。由于屋子小,人口多,实在是转悠不开,所以打记事起,我就和爷爷、奶奶在大北屋的里间睡对面炕。因此,也就经常听奶奶说起她的一些故事:
“我从八岁的时候就进了你们孙家的大门,在你家里弹养着,给你爷爷做童养媳。想想那时候的生活,连做梦也没想到会过上现代的好日子。”奶奶很知足地给我说起过这样的话不止一次。(大姑夫给奶奶是一个村的。大姑夫曾经给我说起过,你那个老姥爷就是个典型的浪荡公子,从仲宫到营里,说不知道张三爷,出门在外时连上衣口袋里小手巾从来都是带三块不同样式的。‘什么擦鼻子的、擦汗的,提溜耷拉好看的。’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沾化惹柳的人,最后死到哪里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奶奶只给她妈上坟,根本不知道她爹埋在什么地方。)
奶奶回忆道:“市里经七纬一路的东安街北头,你七老爷爷家里开了个洋车行,那时,你爷爷就跟人家拉洋车(黄包车)每天交上租金剩下不了多少钱,你爷爷拉着个黄包车到处跑。我们拉扯着你爸爸,你小爸爸,还有你二姑,一家好几口人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有一次同我们的小叔,就是你黑子爷爷(孙丙坤老爷爷)他们两人一块拉着车到城外的一个解放区去送人,正赶上济南战役前期,就被当地的政府人员扣住了,待了好几天了。开始时被共产党当成了国民党的间谍,等到核实好了,弄清楚了你爷爷他们的身份,才被放了回来。我们一家人可担心死了。可你七老爷爷还是说三道四的不高兴,认为是你爷爷他爷儿俩私自挣钱去了。直到解放军攻打济南的前夕,由于害怕几个孩子受到伤害才回到了老家居住。”
……
儿子未上幼儿园之前,我、妻子、爸爸、妈妈,我们上班的上班,做生意的做生意。只有奶奶经常用小儿车推着我儿子满大街的逗着他玩。
有一次,我听到了奶奶在哄着儿子唱童谣,那是我小时候奶奶唱给我听的。她只是把童谣里面的名字改了一下。那童谣是这样唱的:“打箩箩,蒸馍馍,蒸了给谁吃?给俺小楠楠吃。”她一遍遍重复唱着。直到儿子不闹了睡着了才停下来。我想,爸爸小时候可能也听到同一首歌谣吧。我小时候奶奶给我唱过许多童谣,直到现在我还会背。像《月亮奶奶,好吃韭菜》、《小巴狗,带铃铛》、《小老鼠,上灯台》、《狼来了,虎来了》……一首首童谣,奶奶唱了一辈子,滋润了我们三代人。
奶奶去世之后我留下了奶奶的两件遗物算是做个纪念吧。一把可手的菜刀,那是我刚参加工作后不久给奶奶买的。奶奶生前能自己能做饭的时候,一直都在用着。菜刀用钝了,用磨刀石磨一磨继续用;菜刀生锈了,用磨刀石磨一磨再继续用。好像她孙子给她买的不是一把菜刀,而是一件宝贝似的。直到现在这把菜刀我依然使用着。我也学着奶奶的样子,用钝了,生锈了,在磨刀石上磨一下再用。好像这不是一把菜刀,而是丢不了奶奶这件宝贝似的。
另外一件就是这只柳编工艺品——圜子。直到现在我依然也在使用着。就是这只圜子留给我多少童年的回忆啊!

奶奶的这只圜子,静静地悬挂在炕上面。我们睡觉的炕顶上是一个用高粱杆子铺底做成的架棚,是用来放置秋后生产队里分到的“老棒槌子”、“地瓜干”等一类的粮食。扎棚的横杆上顺下一个榉夹绳子来,麻绳上挂着这只圆圆的小篮子,我有时呆呆傻傻的盯着它看老半天,这里面曾经带给我多少诱惑呀!
每年到了年底的腊月二十七、八晚上,大姑夫就担着一副“半宅筐”来给爷爷奶奶送年下来了。一头是劈的整整齐齐的木头块,一头是蒸好的大白馒头。从此后一直到二月二龙抬头,奶奶圜子里馒头可就断不了。
那时春节,我们这里走亲访友风俗都是带上几斤面条。从亲戚家吃过饭带去的礼物是不能全留下的。亲戚要回礼的,或几个馒头,或一、两把面条。知己的亲戚回礼六个馒头或两把面条,远一点的亲戚回礼四个馒头或一把面条。 有时馋了想吃块馒头,可馒头高高地挂在奶奶的圜子里。我的年龄小、力气小,尝试了好多次也没办法够下来。有时想趁奶奶不在家里时,把小杌子放到炕上,想把那只圜子摘下来,可是连托都托不动。最后,还是只得央求奶奶。奶奶总是给我掰上一小块递到我的手上,用手指头轻轻点一下我的额头“小馋猫。”她自己舍不得吃又把那半块馒头放回到圜子里。在那物质生活困乏时期,连馒头都成了人们的奢侈品。
奶奶的圜子,不仅有香喷喷的馒头,而且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一次,我好像是生病了发高烧,躺在爸爸妈妈的炕上,当爸爸妈妈走进房间时,我看到他们不是从门口进来的。好像是打着嘴仗从屋门上面的窗户上走了进来。我头昏昏沉沉的,眼皮怎么使劲也睁不开。但模模糊糊记得奶奶着急地给妈妈爸爸说:“孩子可能是发高烧了,把他抱到我屋里来,我和你婶子给他咕噜咕噜就好了。”我被一只大手抱到了爷爷奶奶的土炕上。我躺在炕上浑身难受,抬头两眼直直地盯着上方的顶棚,感觉眼前,就像有人在缠一团麻线蛋,那个线蛋才开始线圈很小,一点一点的,一圈一圈的,那个线球越缠越大,越缠越大,最后不知道有多大了。 只是头顶上的那只圜子还好好挂在在那里。朦朦胧胧中看到奶奶从那只圜子里,拿了几张火纸出来,然后二奶奶找来了一个盆子,里面舀上许多水,又不知找了一个什么东西。只看那火纸点着之后,二奶奶在一个瓶子里面摇晃了一下,然后扣在那个盆子里面。于是盆子里就有咕噜、咕噜、咕噜噜的声音。我听到奶奶和二奶奶不停的叫:“快回来吧孩子!快回来吧!”一会儿,我可能是动了动,听奶奶说:“这一回,这孩子的魂可能回来了。”我睁开眼,看到奶奶喜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这回好了,这回好啦,孩子的魂回来了。”
老院老屋的屋后,有我家的一个小小的后园子,园子不大,但有一棵“葫芦把子梨”,现代人们叫它“茄梨”。在那个年代茄梨可是个稀罕物。
在我的印象当中,只有第三生产小队的南山根儿的娄家院子后有这样的一棵梨树。每当那儿的茄梨快熟了的时候,我们几个馋嘴的小猫咪只是眼巴巴的望着那棵梨树,想让胆大的小伙伴偷一个出来尝尝一人吃上一口,可是生产队里总有人看管着,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性。于是,我也就只能惦记着奶奶圜子里的“葫芦把子梨”了。到了秋天的时候,那篮子里装得满满的了。我算计着日子等着,一直等到茄梨软糯了,奶奶才给我拿出一个出来。咬一口,那甜蜜的汁水一下子流到了心里。
奶奶的圜子,留给多少我童年的回忆啊!每当看到它,就好像看到我奶奶又出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