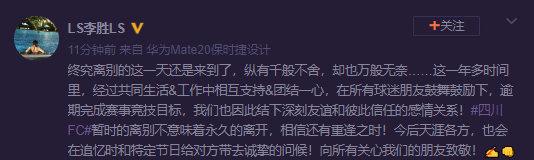《破窑赋》是一篇伪作和破烂赋
无论任何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没有消停过。
可是,理想的日子不是一蹴而就,站在焦虑的此岸,望着幸福的彼岸,一时到达不了,更多的是一辈子都到达不了。
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世人的心灵需要抚慰,需要鸡汤,需要在起伏的命运中获得一个安静的心态。
岁月不静好,但心态要静好。
于是,就有了“破窑赋”。又名“寒窑赋”,“劝世章”。、
传闻是大宋名相吕蒙正的作品。
在网上流行若干年了,被冠以“千古奇文”。
其实,这不是“千古奇文”,而它能够流行,则是“千古奇闻”。
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是一篇伪作,也是一篇破作。
“破窑赋”的火爆,是民族审美的悲剧。

首先,这不是北宋的语言风格,倒像是明清时期鸡汤文的风格,诸如“增广贤文”、“弟子规”,更像是街头巷尾算命先生编的顺口溜。
北宋的赋是啥样的,请看王安石的“思归赋”: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兮亲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马兮山阿。”
用词之典雅,意境之高远,一比“破窑赋”,就有金玉破布之别。
吕蒙正虽然不是文学家,文字上比不上王荆公,但再不济也是个宰相,正规途径考上的进士,也不至于跌落到这种街头说唱的水平。
再举个例子,范仲淹的“蒙以养正赋”,看开头:
“蒙者处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群。守晦蒙而靡失,养中正而可分。处下韬光,允谓含章之士;居上弃智,斯为抱一之君。”
比一比“破窑赋”的开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学者之气和粗鄙之气之对比,昭然若揭。
弗曜、弗群、靡失、允谓、含章之士、抱一之君。
这些都是明显的文言文用语,尤其是“允谓”、“含章”,都是古里古气的,在现代基本不用了。而“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都是俚里俚气的,很像顺口溜。

举一篇大家最熟悉的宋朝的赋(文体赋),欧阳修的“秋声赋”:
“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对比“破窑赋”这一段:
“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
“烟霏云敛”、“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跟“不肖之儿”、“大孝之子”比一下,就知道语言功夫不在一个档次。
吕蒙正文学成就固然比不上欧阳修,但也不至于用语停留在街头说唱水平。
其实,说唱作品的水平也比“破窑赋”高。
说唱讲究用韵,辞赋也讲究押韵。
什么是押韵?
说得浅一点,就是韵母相同,至于古人的韵,这里不细说了,拿现代的韵母来说吧。
宋代的歌谣: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烧”、“焦”和“摇”都用的同一个韵母,哪怕从现代拼音来读。
宋代王安石的诗: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即使从现代拼音角度来看,“升”、“层”是同一个韵母。
哪怕是当代的歌曲,不押韵都不好意思,例如毛不易的“消愁”: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
“场”、“想”、“妆”、“样”,都同一个韵母。
试着唱一唱“偏偏喜欢你”: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 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
“去”、“虚”、“除”、“句”,是不是韵母是同一回事?

还是说赋吧,同时北宋人苏轼写的“前赤壁赋”: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鹿”、“属”、“粟”也都是跟着同一个韵母走。
反观“破窑赋”,一开篇就不用韵: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蛇”和“鸦”按照平水韵算是押韵了,但“往”、“通”,都是各用各的韵,各跑各的路,一篇赋在韵律上就这么跑散了。
“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
“刎”、“山”、“封”、“遇”,都是该押韵的地方,却也是各唱各的调,一片混乱。
宋朝出现了散文赋,不一定都要押韵,例如“秋声赋”,但如果你用的是整齐对仗的句子,那还是得用韵。
吕蒙正也是朝廷重臣,进士出身,状元身份,写个赋都不好好押韵,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在路上遇到那些饱读诗书的同僚,估计都不好意打招呼了。
难道他的语文是呼延赞教的?
就算是吕相国只会应试,不会文学,文章粗鄙,但还有一点不对。
那就是:
格局!
格调!
范仲淹的格局是这样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天下为己任的画风。
王安石的格局是这样的:
“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
为革新不畏人言的气度。
这是一位相国写过另一位相国的,气度自然大,且不论,看看王安石钻个山洞,其感悟也能做到非凡: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欧阳修的格调是这样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虽然有些颓废,但审美气质这一块,那是拿捏得死死的。
至于苏轼的“前赤壁赋”: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则与古希腊的能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已经在开启王阳明的路子。

至于“破窑赋”,满篇都是个人际遇,一己荣辱,关心的是升斗之间的待遇,毫无宰相心怀天下的胸襟。
你仔细去玩味,就如同一个人生不得意的loser,前来街头算命,街头那位带着墨镜的先生,嘴里絮絮叨叨:“时遭不遇,只宜安贫守份;心若不欺,必然扬眉吐气”,心心念念都是凤凰男的壮志,把大宋江山交给这样的人去打理,我都替皇帝出一身冷汗。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视文学审美的名族,在民间流行不衰的是什么?
是“滕王阁序”里的“秋水共长天一色,孤鹜与落霞齐飞”,神哉!
是“岳阳楼记”里的“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妙哉!
是“醉翁亭记”里的“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美哉!
我们民族的审美格调,无论是辞藻,还是境界,从来没有低过。
到如今,反而全网盛行“牛叉”、“蓝瘦香菇”,在这种文化审美基调上,一篇伪造的粗陋的所谓赋,能被人成为千古奇文,悲哉,真是千古奇闻。
如果你在网络上遇到那种特别好懂,特别能触动你的所谓古文,你就要多长个心眼,那极有可能是假冒的。
古文总是有点门槛的,不可能那么容易懂。
如果这点门槛都不给你,那就是一次网络策划。
“忽有故人上心头,回首山河已是秋”,这句诗特别温暖,其实是假的,前半句是龚自珍,稍微懂格律的就知道,这两句格律完全不对。
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两句诗个人的温暖感,和“破窑赋”比起来,其价值稍高。
流行的一定是有人群基础的,“破窑赋”通俗易懂,语句朗朗上口,尤其是切中人心:命运不可测,心态要调整好,忍受一时的艰难,也要看淡滔天的繁华。
当成段子乐一乐,说一说,未尝不可,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网络不是学问之地,假冒而不害人也就罢了。
但你如果真要当成文学上品,让孩子毕恭毕敬去朗读背诵,那就是在耽误你的孩子了,人的脑子一旦灌进了这种油滑低俗的文字,以后的格局和品味,就真的起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