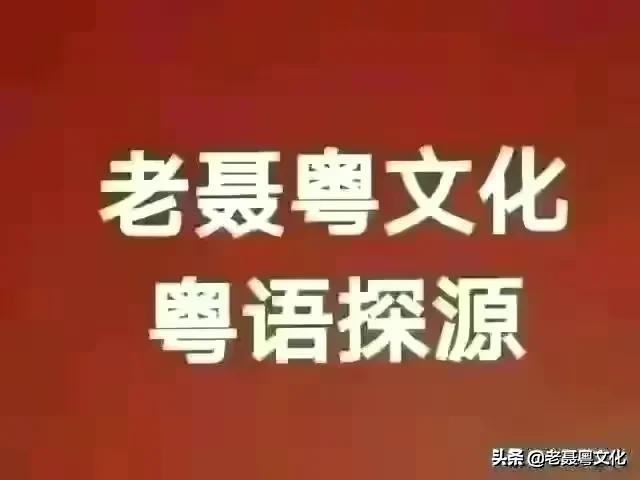在《有关〈云中记〉的一些闲话》中,阿来回忆了十一年前亲历汶川地震的过程。那时,他正在成都的家中写《格萨尔王》,“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嗄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判断之后,才知这并非源自《格萨尔王》中的想象。地震发生了。之后他前往汶川,看到了大地给人类带来的是何种灾难。多年后,关于这场灾难的书不断涌现。阿来没有写,怕自己有灾民心态。
十年过去,2018年5月12日,阿来和十年前一样,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新小说,“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那个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遂成书《云中记》。

阿来,作家,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著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
一个人,名叫阿巴,一个偏僻的藏地小村庄,名叫云中村,对于要写的庞大灾难,视角小得不能再小,但通过阿巴的眼睛望出去,视界却恢弘如整片大地,庄重而神秘。阿巴不是通常所谓的普通人,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一名经培训而获得“祭师”称谓的人。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也是祭师,但没经过培训,他们是通过云中村文化的传承成为祭师的。阿巴被培训为祭师,是为了发展文化旅游,需要这样一个具有传统身份的人。因此阿巴对祭师身份不以为然,直到地震发生,世界猛然崩塌。人的大片死亡,让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发生转折,阿巴从一个不相信鬼神的人,逐渐开始转变,进而思辨: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魂?
在移民村待了三年多,阿巴以祭师的身份回到云中村祭祀亡魂。“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一趟寻回过往、寻找自我的旅程就这样开启。终于回到村子,他看到的是一幅苍凉景象:人烟销迹,屋子坍塌。死去的人在他的记忆中活转。还有那场地震,作为背景,克制地闪现。不煽情,不悲惨,而带有人性的尊严与庄重。这是阿来面对生命与死亡的姿态,他说,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
阿来没有在《云中记》中着重写“灾后惨状”,而是写出灾后人们的重建之艰难。央金姑娘失去一条腿,还在梦想着跳舞,无论她多么努力,公司的营销策略定位于她的灾难背景;中祥巴靠直播灾后的云中村挣钱,以养育儿女。精神和物质的重建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
灾后的世界是灰暗的,阿来并不想让灰暗长久笼罩。阿巴精神的回归,中祥巴的自我修正,都实现了自我确认与救赎,正如写完这部关于地震灾难的《云中记》后,阿来说:“这只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书中的世界也是如此。
死亡会给我们带来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
新京报:新书为什么会选择汶川地震这一题材?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你表示有些反对写这一题材。
阿来:不是反对写这个题材,而是反对非常着急、都没有想清楚就来涉及这一题材。文学和新闻不同,不会那么快反映纪实的情形,需要一段时间情感的沉淀、认知的升华,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对题材保持慎重。我并不反对,因为文学总要处理各种题材,灾难也是题材。
新京报:与之前的写作相比,《云中记》的写作过程有没有因题材的特殊而有所不同?
阿来:小说从本质上讲都是在特定空间中创造人物、创造人物关系,这个人物关系,当然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尤其是这样的题材。所以,从本质上说,任何小说都在处理这些关系。每部小说可能都要进入到一个不同的领域当中。有可能我们会永远写同一种模式的东西,但商业化的写作才会走这种路子。所以(《云中记》的写作过程)没有特别的不同。
新京报:书中的主要人物阿巴不是通常所说的普通人,而是一个祭师,且他家世世代代都是祭师,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主要叙述对象,有哪些考虑?
阿来:书写灾难会面临一个重大的哲学和文学命题,就是死亡。死亡会给我们带来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也会强化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情感推到一种极致状态。普通人面对死亡,可能会有一阵痛苦,随着时间的消逝会慢慢减缓,然后遗忘。但是如果想要更哲理地思考生命意义,不能采用这种方式。我们可能通常要假定有灵魂的存在。
新京报:所以阿巴在书中一直在思辨,到底有没有鬼魂。
阿来:对。他更特殊的是……你刚才说“世世代代都是祭师”,也是也不是。因为到他这一代,(祭师的传统)正在消失,尤其经过“文革”。所以他过去并没有自称祭师,甚至他父亲在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些东西传给他。是后来,新的形势,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起来)。其实那时候他也只是扮演旅游从业者的角色。最初让他(以这种身份)出来,更多的是出于恢复旅游的考虑。我们经常说“文化旅游”,就是要挖掘这样一些传统文化。只是到了地震,有那么多死亡,那么多伤残,这时候大家获得了对生命的理解,现代科学并不提供这种知识,所以往往是宗教性的、神灵的系统会给人带来情感上巨大的抚慰,尽管它并不科学。这时候他才觉得,这个职业确实对他有了意义,甚至后来他愿意为了这种心理,和这个村子待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有鬼魂的话,他得和这些鬼魂待在一起。这是他的职业带给他的。为什么选这个人物,因为他有这种方便,具有人神沟通的职能,别的职业不具备这种职能。而在这部书中,有大量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或叙述。只有这样一个人物,才能担负起这一使命。
新京报:书中的云中村有自己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书里非常重要的展现之一,就是云中村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如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寺庙的拆除等。在你看来,像云中村这样的村庄和它们的文化,在当下应何去何从?
阿来:这些在历史中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书写,不想用碰撞、矛盾这些词。它只是历史在自然地演进。新的东西慢慢出现,旧的东西慢慢消失,这种过程在整个人类进程中一直在出现,只不过是现在因为技术进步,节奏变得更快了。在我的书写中,也没有悲情,都是把它当成对现实的记录。
面临灾难,意识到自己的职业和使命
新京报:阿巴在震后回到云中村,是为了祭奠死去的人的亡魂,也像是在寻找自我。
阿来:对,是这样的。原来他的自我确认是不明确的。他是上过中学的,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村落,他上中学的时间应该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是云中村最早的负责发电的人,后来稀里糊涂就让他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仅仅是因为他父亲和爷爷曾经是祭师,他的技能都是专门培训得来的。政府要做这件事,除了保存文化以外,更多还是出于旅游的考虑。这里面有一个乡村旅游的规划,刚好这个村子有这些特征。那时候他对这个身份没有那么高的认同,他知道这是表演性质的。当死亡大面积发生的时候,他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他才真正认同了祭师这个身份,要做祭师该做的事。
新京报:阿巴的外甥仁钦也是书中比较重要的人物,身上有矛盾性。他是从云中村走出的大学生,紧跟时代发展,很多传统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着舅舅的精神世界。政策不允许有人回到危险的云中村,但他没有强行把舅舅驱赶出去。
阿来:至少他在理解这件事情,理解他舅舅遵循的价值,所以他不惜因此丢掉乡长的职位。他也是我在地震灾区中接触到的大量基层干部(的形象),写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地震第一天,汶川很多县交通断绝,通信断绝,外面的援助晚了很多天才到达,那最开始谁在做救援?第一是老百姓自己,第二就是当地干部。我知道,由于余震不断,很多人就在发生地震当晚死在路上。地震灾难对人的觉醒,自己责任感的意识(都有重要作用)。仁钦上大学选的是文秘专业,想的是给领导当秘书,得到提拔,但是地震灾难面前,这些干部连夜就分散到全县的各个地方。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意识到自己的职业和使命。和阿巴一样,仁钦也有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
新京报:所以说在仁钦身上的矛盾性中……
阿来:我们现实中每个人身上在新和旧之间,在私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之间,肯定总是有摇摆和冲突的,只不过最后有人做了这样的处理,有人做了那样的处理。
新京报:在当时发生地震时,你也及时参与了救援。
阿来:这是非常普遍的。但我绝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带着一种意图。我想新闻媒体有时会有争论,当记者到达战争或其他现场时,你首先是选择记录呢,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参与。这是关于新闻伦理的讨论。我们也一样。有些人可能一去就意识到是找素材的,但是要我选择,我会作为一个普通人,帮助大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我相信这个过程,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点什么,但至少当时要忘掉作家的身份。
新京报:整部书中,你对地震的描写其实没有展现出过多的情感。
阿来:对。我更多的是把它当作背景,因为阿巴出现已经是地震三年以后了,三年后他要去抚慰亡灵。但他也是半信半疑。书中有一个情节,是他特别希望能碰见一个真正的鬼魂,但是没有。不过这是一个信念,更重要的是要把移民村里的消息带给那些亡灵。

《云中记》,作者:阿来,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灾后重建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一直没有完成
新京报:这部书更重要的是对灾后生活的反思。
阿来:是。当时地震刚发生,全国、甚至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但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节奏这么快,媒体上出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那么多,大家很快就遗忘了。对很多人来说,这件事和明星出绯闻、某个地方出现暴力事件意味差不多,它只是一些文字,一些图像。对经历灾难的人来说,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基层干部,他们的重建过程是很难的。我们说疗伤,遗忘死亡的悲伤,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而且他们要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重建自己的生活,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尤其书中写到的“地震后遗症”,就是地质结构破坏后那些次生灾害,还在不断发生,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对他们来说,重建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物质层面的,一直还没有完成。像灾后失去那么多土地,他们不得不转型,转向服务业。对祖祖辈辈种地的农民来讲,要学会这个事情,也是非常困难的。
新京报:书中对旅游业的描写具有很强的反思,尤其是书中的人物中祥巴,他是被灾难异化的人,通过直播发灾难财。
阿来:现在我们消费灾难的人多的是,有社会的例子,他受到启发。但他后来不断受到别人的抵制,自己内心也有尊严,开始了转变。还有一个央金姑娘,想学舞蹈,打算包装她的公司更多的不是看到她的才华,而是她的灾难背景。
新京报:你认为在这种地方开展旅游业,是不是利弊参半?
阿来:如果是纯文化,也没有什么,提供一个观赏。对待灾难就不一样,确实存在一种伦理在里面。
新京报:书中也明显涉及了你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就是自然的问题,书中也有自然神性的展现。
阿来:我的每本书都会涉及。我不想把我们的叙事文学限定在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们必须意识到人和自然关系,也就是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现在的人越来越厉害,技术手段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人口越来越多,这样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通过消费需要从自然界获得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很少考虑自然能承载多少。现在中国已经要负担这种负面影响了。在任何地方,我们要放心地找到一口干净的水,在最发达的地方要呼吸到纯净的空气,都已经是一个奢望。
新京报: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阿来:过去很多工业国家都走过这条道路。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他们迅速克服了。应该说在治理方面,比我们好很多。这个错误已经有人犯过,我们为什么没有从中学习。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在人可以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和自然是可以和谐相处的。
阿来:对,大部分是。当然,地震、火山这些例外。比如说某个地方爆发泥石流,你把山上的树砍光了,它怎么不发生泥石流呢。某个地方发生大洪水了,如果森林多一点,洪水就会少。
新京报:在书的前言中,你特意致敬了莫扎特的《安魂曲》。依照写作经验,音乐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阿来:肯定是很好的影响。因为音乐能把世界抽象得更纯粹,变成一串声音,这些声音、不同的乐器相互呼应,共同推进。当然,我说的不是流行音乐,而是说西方古典音乐。而且它们有非常精美的结构,这些都可以带来启发。我之所以致敬莫扎特,是贯彻一种精神。《安魂曲》是直接考虑生命和死亡关系的音乐。我们对待死亡大部分就是悲痛,但好像在欧洲的传统文化中,对死亡有更深刻的领悟。不光是在写作过程中,当时在灾区开车,我就经常听《安魂曲》。我们平常习惯的音乐,在那个地方肯定是不合适的,但为什么《安魂曲》就合适呢?这当然就会给我们思考。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进
编辑
:李永博;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