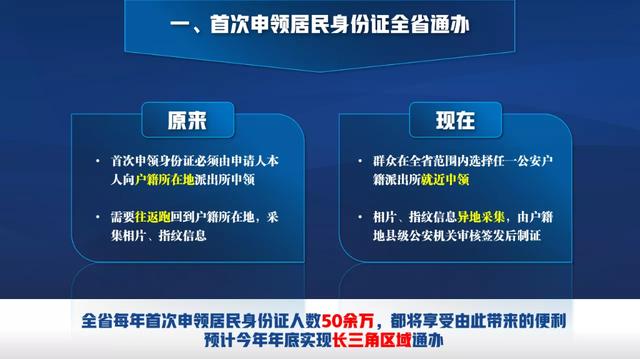割草的记忆
卢运锋

割草
我的童年总和割草相连。
小时候农村的日子每家都过得紧张,养一头猪、几只鸡补贴家用,是家家户户最普遍的创收方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家的“标配”。父亲工作在外,哥哥姐姐在外上学,家里只有奶奶、妈妈、我。没有劳力的家庭,更是指靠猪和鸡们维持日常的开销,还有那间断养过的一些兔子。
猪一直是养能下猪仔的母猪,为的是卖猪仔贴补家用,每年还要靠它给生产队还一部分欠的工分钱。我不记得吃过自家的猪肉,猪老了不能生猪仔后,会卖给收购的人,每次猪要被带走的时候,奶奶都借口出去串门了,母亲和我含着泪水,心里是依依不舍。时到今日,我仍旧记得它们不同的模样,记得它们吃食、睡觉、生猪仔时的幸福与苦痛,想起它们,心里满是暖暖的亲情。
筐子
割草需要的装备就是一把镰刀一个箩筐,家家都有。家乡方言里把镰刀叫镰,省却了刀字。筐子叫搓(cuo),这种叫法有一种粗狂的亲切,是与那时乡村人文环境融为一体的。镰刀没有太多的计较,式样都大同小异,木的把手也都是自己找一根顺手的木棍套上去,不锋利了就找个类似于磨石的石头磨一磨,不记得伙伴们议论羡慕过谁的镰刀好,也不记得自己出门前苦恼过自己镰刀比起小伙伴的如何。筐子就有计较了,主要是计较新旧,式样上倒没有多少变化,筐子那个时候是个多功能的劳动工具,担肥担土倒垃圾,运红薯运玉米棒子摘棉花桃,装猪崽装鸡鸭打猪草都要用,所以用的多烂的快。
经济紧张的时代,买一个新筐子是一项投资,所以都是和穿衣一样,烂了修修补补,哥哥用了弟弟用,夸张一点说就是新两年旧两年,补补修修再一年,最后拆了当柴烧。提着一个破筐子去割草,难免会有自卑的情绪。虽然那时村风淳朴,伙伴单纯,也不免有开玩笑的,伙伴们又都自尊,所以割草时提的筐子是不是很破是有计较的,能拥有一个新筐子,是每个伙伴的一个小梦想。
记忆里,每当家里买了新筐子,总是哥哥先用,说实话,心里会有一点不长时间的郁闷,但更多的是羡慕,因为那时候这样的事再正常不过,户户家家,件件事事都是这样,自然而平常。每次哥哥不放假的时候,我就提着他的筐子去割草,好像还时常有点理亏的感觉,所以总希望妈妈又买了新筐子,这样我就可以提到哥哥那个了。这也是我对规则秩序最初的理解。记得一种用竹子编织很密实的筐子,大小人都喜欢,新筐子外面绿绿的,里面浅浅的淡黄,白白的木提手,怎么看怎么漂亮,也最耐用。今年清明节回家,路过常青乡集市,看到路边大爷在卖这样的筐子,满怀亲切,毫不犹豫买了一个,双手情不自禁的满筐子摩挲,媳妇还有些诧异,但很快就笑笑的跨到胳膊上,欢喜得自拍起来,我心里还喜喜的说,这媳妇确实没有选错。一向爱埋怨我乱买东西的老妈,见了这个散发着竹子味的筐子,也翻来覆去地看,不停的评论着这筐子哪儿好为什么好,和看自己的孙子眼神一个样!

小伙伴
割草季节,最难忘的是在暑天的假期里。吃完饭,小伙伴们不约而同集合到一起,一起去地里。路上大家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一路上少不了干一些坏坏的事。那时候常在一起割草的小伙伴有小勇、锋娃、强强、红家、永泽几个。小勇最壮实,长得高饭量大,老是吃不饱的样子,到了地里最关注哪里有地鼠,老是提着筐子四处找地老鼠洞,发现了就大声吆喝我们过去,一起围到洞口琢磨里面有没有,七嘴八舌的。时间长了,他真成了专家,一眼就能辨别出里面有没有,找水一灌一个准,地鼠出洞的瞬间,他用右手虎口很麻利的一掐就抓到了。现在想来那感觉一定是钓到大鱼起竿一瞬间的兴奋,可惜我那时一直不敢抓,害怕时机掌握不好被咬了,现在想起来还十分的遗憾。前一段网上有个视频,就是灌地老鼠的情形,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亲切极了,勾起了许多回忆。
那时,小勇抓到地老鼠后,晚上回家扒皮煮了,第二天一定会给我们讲,地鼠肉是多么多么香,讲着讲着他口水就流下来了,我们也跟着咽口水,空气中好像就弥散着地鼠肉的香。不记得在哪个堂哥家吃过几口,确是人间难得的美味,现在也不定还能寻得到。小勇的心思在地鼠身上,割草他基本是应付,老是马马虎虎,就好像吃肉的动物,对草根本不上心。锋娃是我堂弟,只相差一个月,真真正正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他特别顽劣,上房揭瓦、下水淘泥,上树掏鸟下地摘瓜,偷粮食换桃,做弹弓打鸟,样样是能手,就是上不进去学。割草一有他,从开始往地里走,就要防着被他带偏了。记得顺着他走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老走不到他说的地方,一路上,先是爬到村边人家的后墙上,偷几个枣分给大家,然后吃了人家嘴软的我们,唆着不忍吐掉的枣核,又被他忽悠的钻到棉花地里,偷吃几个嫩棉桃,再信誓旦旦带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到了又是树上有个鸟窝,他嗖嗖地爬上去掏,也常常有一些鸟蛋和雏鸟的惊喜。要不就是有个马蜂窝,他领头去骚扰,马蜂炸开,我们四散奔逃,锋娃总是跑的最快,躲的最好,时常蜇的是强强、红家几个不麻利的,抱着头哇哇大哭,我们扒开头发,在肿起的疙瘩上挤蜂毒,他爬上柿子树摘几个青柿子,用柿子在蜂蜇的地方蹭蹭消毒。记得有效果,慢慢就不哭了,要是哭着回去就麻烦了,大人会嚷我们,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和功臣似的,好像马蜂窝是我们捅的一样。再就是带大家去的地方,往往是我们人比草多,还没有来得及埋怨,他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活动,鼓动小伙伴们先打一会土仗,都是贪玩的年龄,经不起诱惑,说打就打,简单的分两派,隔着一条水渠,几座坟茔,一间废弃的瓜房,学着电影里的场景,你攻我守,我逃你追,满地都是的土块是天然的子弹,满天的飞,头上被砸个包,鼻涕、泪水、热汗一马虎脸是经常的,常常是仗打的不亦乐乎,一塌糊涂。猛然看到天边大大的红红的落日时,才突然意识到天要黑了,筐子还是空的,小伙伴们就慌了神,顾不上埋怨,匆忙按各自的法子应付起来,折些榆树枝子蓬到筐子里,上面铺一层杂草伪装一下是最常用的方法,偶然也会偷割些红薯秧子和苜蓿,这是要冒着被没收筐子风险的,但这两样却是猪和小兔子的最爱。回家路上,伙伴们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各自想着各自可能的后果与应对。记忆中有过几次因为这样的贪玩,回家只有半筐子草,妈妈不曾责备,自己却觉得很愧疚,所以等大了一点点,锋娃就不再能诱惑了我,更多的是我主导他们去那儿割草。
许多年过去了,儿时的小伙伴们有时聚到一起,说起那时割草的种种情况,最快乐生动的记忆,恰恰是锋娃带给我们的,他带领我们在野地里打土仗,偷西瓜、花生、豌豆角,摘软柿子,套知了,卷棉花叶子当烟抽,都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时候。回忆起来笑声不断,快乐无比,不曾感觉到有错有苦的地方,有的只是单纯的友情与无忧无虑的快乐。
初中后,我离开了村庄,疏远了老家的绿草地,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但对于草的情感却已深深地融在了我的生命里,停留在了那看似辛苦却又简单快乐的日子。每次回到老家,我都情不自禁地要带着媳妇孩子,去地里转转看看,每一块土地我都很亲切,都仿佛还能看到我镰刀划过的痕迹,听见镰刀与地摩擦的声音,儿子老是纳闷没什么看的,我却那么动情。上班之余,我喜欢去野外,去爬山,去看它们,去触摸它们,和它们聊我们之间的故事。在我的语言里,从不曾有野草一词,它们和小麦、玉米、豆子一样,在我的心里都是五谷的一种,都是我最亲近的物种。我爱它们,感激它们,是它们给了我对责任的最早启蒙,给了我对成就感的最早体验,给了我对幸福生活最直接、最温暖的记忆。
经历了人生的许多起起落落,我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一棵朴素而坚强的小草,荣辱不惊,坚韧不拔,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坚强的成长,快乐的享受着阳光雨露!享受着内心那份淡然的强大!
晒酱
卢运锋
母亲晒的面酱,好吃的不得了!
母亲八十多岁了,每年到了六七月份,依旧的开始晒制我们家的面酱。先是一定让带她去市场,亲手买晒酱需要的面,常用的是豌豆、黄豆、玉米面,再加上家里常有的小麦面。妈妈总是挑的很细心,用食指尖微微的挑一点豆面,在食指与拇指前端轻轻的捻搓,感知它们的细度,抬手送到眼前,推起老花镜,仔细地观察面的色泽,然后放到鼻子下面,闻一闻是不是那熟悉的香味。满意了,像小孩子一样的高兴,没有满意的,妈妈会有失望的情绪,这时候我们会夸奖地说:“我们家的酱好吃,主要是你晒得好,面不是问题。”妈妈就又高兴起来。说是夸奖,其实就是真真正正的实话,是心里话。
面买回来了,首先是把它们炒熟,锅一定是铁锅,火是小火,炒是不停地连底翻动。一会锅里的豆面就慢慢变得蓬松了,颜色也深起来,豆面的香味,热热地弥散开来,引得左邻右舍禁不住过来问候:“奶奶,又开始晒酱了!”真是想低调也低调不了。这时候,妈妈总是遗憾,城里不便生柴火,要不炒出来的会更香。等面的颜色全部变过来就熟了,赶紧的倒出来,都炒好了,均匀地混合到一起,摊开放凉。凉透了,用细细的筛子筛一遍,把结块的过滤出来,用擀面杖擀开了再炒一遍,不小心有不熟的面混了进去,酱放时间长了,会有生虫子的可能。每次这个时候,我觉得麻烦,想把那一点点结块的倒掉,妈妈总是舍不得,不愿意有一点的浪费。
炒面这道工序,我们帮不上多大的忙,妈妈总是嫌火大了,翻炒慢了,欠了过了的,所以,只好有劳她老人家了,妈妈却干得津津有味。
过去在村子里,晒酱的面都是人工磨制。龙口夺粮的季节里,抽时间约好几户人家,商议了豆子的种类和各家的量,约好了时间,靠实石磨的使用,一切就在收工后的疲惫里,紧促有序的进行。称好小麦、大麦、玉米与各样的豆子,配比除小麦多一点,其它的相对自由,没有的可以相互赊借,来年地里收了再还。用柴火铁锅炒熟了,混合到一起,一同在石磨上磨制。先是把石磨冲洗一下,把磨盘间残留的生面洗出来,防止混了进去。夕阳西下,在夹杂着几丝凉爽的热浪里,推磨的推磨,放料的放料,筛面的筛面,一起说着,笑着,累着。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们,光着屁股,一边嘎嘣地嚼着豆子,一边热闹的嬉戏着,月上头顶时,把剩下的豆渣当报酬,给了石磨的主家,叫醒地上睡了的孩子,背上分好的面,满是疲惫与憧憬的快快往家回。
母亲总感慨,过去先把豆子与小麦炒熟,再用石磨磨好的面,比现在买了机器磨的,在煤气炉上炒熟的要香得多。虽然苦点累点,但收获的快乐和酱香却是现在所不及的。
面准备好了,选一个炎热的天,用冷的淡盐水,把面拌成酥状,然后用力在手心里,一点一点地添加挤压,做成铅球一样的面蛋子,俗称酱太子。母亲年龄大了,手上劲不足,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当主角了,妈妈总是不放心的在一旁监工,就像教练一样。唠叨的核心是,一定要从里到外的用力捏瓷实,表面一定尽量的光滑,不能有缝隙。捏好了,放到太阳下,一会一翻滚,均匀地暴晒,等晒到外面结了干层,马上用新鲜的柿子叶包严实,一层酱太子一层柿叶,叠放到瓷盆里,捂严实,放到阴凉处发酵。柿子叶尽量是选择大而厚实的,每次我会高兴地带上媳妇孩子,去郊外柿子树上摘,这项工作,小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发酵酱太子,需要一个潮湿闷热的环境。快速的暴晒,使酱太子内部既存储了足够的热量,又不被晒得太干,保持有适宜的水分。内瓷外光,使热量的存储与释放得到平衡。新鲜柿子叶的包裹,起到了很好的养护作用,防止了开裂,同时又持续挥发一定的水分,把它们捂到一起,就有了发酵所需要的环境。这些道理,母亲她们并不一定懂得,但人们在辛勤的劳动中,用心的去做事,不断地摸索改进,依靠经验的积累,一步步完善,一代代传承,做到了自然的完美无缺。
三七二十一天后,酱太子就发酵好了,掀开来,一屋子酶香的味道。为什么是二十一天,妈妈只说是老人传下来的,实践中也确实灵验,有点像数学公式一样准确。去掉表面霉烂的柿子叶,用刀把酱太子剁开,分成大大小小的块,放到太阳下晒干,然后用杵臼捣碎,一边捣一边用细筛子筛,直到又全部恢复成面粉状。这是个粗细结合的力气活,妈妈一个人做,需要一两天时间。在家的时候,我会主动地承揽下来,还总结了一个小技巧,捣的时候,在杵的上面套两张餐巾纸,用力捣下去的时候,纸巾正好盖住臼口,面块就蹦不出来,粉的面也扬不起来,这样就可以多装点,用力的捣,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妈妈夸奖了我以后,这道工序就成了我的专职,我一叫媳妇来做,她就借口妈妈不放心,坏坏地在一旁幸灾乐祸的。能这样让妈妈放心的叫我们帮到她,实在是很快乐的事。
面准备好了,下一步就是最关键的环节----晒。先要选一个连续三四天艳阳高照的日子,过去,妈妈是靠经验,现在科技了,就在手机上帮妈妈查一下,选择一个持续晴天的日子。选好了,用凉开水制些淡盐水,把发酵好的面和成糊状,盛在盆里,放太阳下晒。盆子上面用纱网做一个盖子,既透气又能阻隔苍蝇的侵扰,也曾用玻璃罩在上面,只是不透气,倒是气得苍蝇没有了脾气。酱盆常用的是传统的粗瓷盆,不只是保温好,那古朴凝重的气质,与面酱幽远的酵香,酱紫的色泽相得益彰。
开始连续几天的暴晒,一会就要深深搅拌一下,让酱糊充分与太阳接触。透透的暴晒,使酱糊先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要不很容易腐烂。之后就是每天的按部就班,在太阳可以照进小院的有限时间里,在促狭的空间中,移动着酱盆,追逐着太阳,一边晒,一边间歇地搅拌,适时地补充淡盐水。这个阶段,妈妈就不再午睡,累了就坐在沙发沙发上眯一下,陪着酱一起的熬晒,看着妈妈每天拖着跟不上身子的腿脚,费力地一点一点挪动着酱盆,我都要劝说明年一定不要晒了,母亲总说没事,当是锻炼身体了,不曾松过口。妈妈养的猫咪小黑,跟着挪了几天,也嫌不好玩,懒懒地躺在花荫里睡觉。儿子小时候,天天见奶奶摆弄酱盆,也模仿起来,一天妈妈在厨房里忙,儿子摇摇晃晃的也去挪动,一下子推翻了酱盆,碎了一地,摊了一片。那次,妈妈是一点脾气也没有,只是担心她的孙子是不是受到了惊吓,现在每年晒酱的时候,看着健康成长的孙子,常会幸福的回忆起来,这时才心疼起她的瓷盆和那年的酱。如今,花市有那种万向轮的地盘,买回来固定到板凳下面,推起来很轻松,蹒跚中倔强的母亲,开始了半自动化的晒酱。
晒酱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天气,一边埋怨着太阳的毒辣,一边期待着它更猛烈地照射着酱糊,期盼着更多的能量与美味溶进酱里。在汗流浃背的日子里,这是我们对红彤彤的太阳,少有的一份亲切与期待。雨水多的时候,就很令人焦虑了,应急的办法,是在房子里用灯泡烤,罩个反光好的灯罩,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烤。缺了阳光的能量,烤出来的酱,少了些鲜活与油亮,但吃起来,心里是一样的温度。现在讲节能,普通的灯泡很少有卖了,我和妈妈开玩笑说,家里还要储藏一些灯泡的,母亲回应的轻松又认真:“总有办法的!”
在妈妈精心的呵护下,面酱由咖啡色向黝黑一步步加深,越来越黑,油亮油亮的,酱体粘稠了起来,搅拌时形成的小漩涡,也不慌不忙地缓缓复平,咸香的味道在小院里弥漫,让人禁不住口舌生津。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好像也得到了滋润,在炽热的太阳下也抖擞起来。大约晒二十几天后,用辛烈的花椒水再拌和一遍,深深提了味,透透的晒一天,就大功告成了。自此,劳累后回到家、艰难的远行里、外出求学中,在热热凉凉的馒头里、在没有卤的白面条里、在缺少油花的汤汁里,幽香的酱,使一切都不再孤独,不再失落。
晒酱的方法有多种,有单用一种面的,有在蒸笼里蒸熟发酵的,有用馒头发酵的,妈妈的这种晒制方法,相对的复杂些,做工也要求的精致,但这样晒出来的酱,香味幽远,色泽光亮,稠而不粘,表面一直会沁着亮亮的一层油,保存多年也不会变质。妈妈回忆年轻时,家里曾经有一个存酱的瓷罐,搬家时找不见了,几年后偶然的又翻了出来,惊喜的是里面的酱依然完好,清清一炒,还是那样的清香四溢,让人记忆深刻。普普通通的五谷,经过炒、磨、发、捣、晒等多样的磨难之后,华丽地转身,成了人们生活里的宝贝,成为有温度有情感的美食。不屈服于生活的磨难,用心认真地去做事,事就不会辜负我们,妈妈常用晒酱给我们说理。
过去蔬菜少,经济紧张,自制的面酱和辣椒,是那些粗粮馒头最好的伴侣。因此,每年这个时候,村子里晒酱的场面很壮观,一块空地上就会有几十盆,大大小小,瓷盆铁盆的,很有气势,把旁边高大的几棵榆树,比得都懒洋洋的。盆在原地不动,一晒就是一整天,好几小时才过去搅拌一下,十几天就晒好了。乡亲们相互照看着,一个人过去,就顺手的全搅拌一遍,风了雨了的,有人帮着盖、帮着收,收错了,太阳出来了,就又在哪里了,不曾有担心。每讲起这些,母亲总是很怀念。
酱晒好了,妈妈先是习惯地给左邻右舍,一家送一些,隔壁常换的年轻租户,时常的半天反应不过来。远在上海的外孙女,早早的就与奶奶视频里要了,对她来说,那是舌尖上家的味道。她埋怨地告诉奶奶,同事们最爱去她家里吃这大上海稀罕的美食,是又心疼又骄傲,尤其是奶奶寄去的西瓜酱,是让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最苦思冥想的,“西瓜还能晒酱,”“怎们就这么香,”“真的是西瓜晒的吗?”是一边吃一边纳闷个不停,妈妈很骄傲她的作品,让这些大上海高知的孩子们,幸福地纳闷、疑惑。有时在大街上,碰到了以前的邻里,都还情不自禁的馋起妈妈的酱,怀念那香甜的邻里关系。如今,在这繁华而纷杂的社会里,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挖一勺质朴宁静的酱,拌上葱花蒜片,在薄薄的热油里轻轻的一拨拉,沁人心脾的酱香,一下子就润到了心田,一切的烦恼,瞬时的烟消云散,记得的只是,多吃了好几个馒头,想得便是,人间有味,最是酱香!
“总有办法的!”妈妈的这句话和那幽远的酱香一样,常在我心底萦绕
卢运锋,山西运城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今年五月开始学习散文的写作
来源:微安塞-文苑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