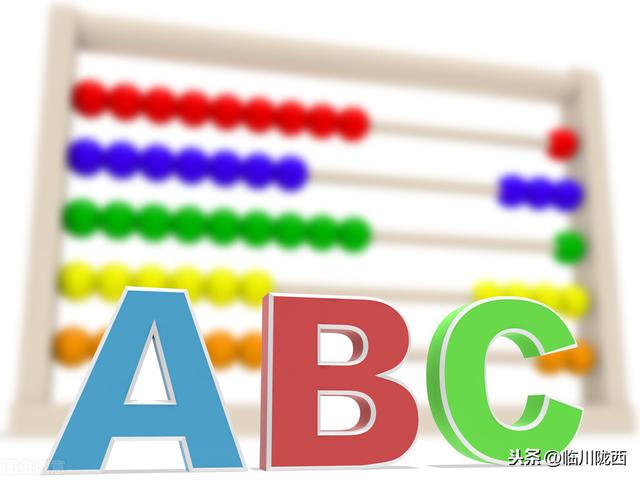大眼贼(散文) 李直,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散文双向线索?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散文双向线索
大眼贼(散文)
李直
按理说,这只在半个世纪前与我曾有一面之缘、而后不知所终的黄鼠,应该理当被岁月的尘埃掩埋,被时光的脚步遗忘,加之几十年来半是辛酸半是坷坎生活的左右夹击,记忆的仓库五味杂陈,早就不应有它的一席之地了。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五十个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它竟一直如影相随。快乐时、悲伤时、灰心丧气时、得意忘形时,它都会冷不防的闪跳出来,隔了半个世纪的烟云,在时光深处凄苦的向我投来一瞥。
见到它那天,是何年,已模糊,自己几岁,不分明,只记得是在一个春天里,午后,一场狂风刚刚离去。
黄鼠是它的学名,它有个很不雅的俗名:大眼贼。它本和老鼠是同类,因其嘴巴不像老鼠那样尖削,眼睛也比老鼠稍大了一点儿,所以显得受看些。这种动物据说只生活在野外,从不靠近人类,也许正因如此,人类对它的印象比老鼠要好得多。比如说,我曾亲眼目睹有人烤大眼贼大快朵頣,却不曾见到有人吞食老鼠。那人边啃一条黄鼠后腿边说:吃耗子肉,保准得鼠疫,吃大眼贼就没事。我当时信以为真,后来年岁渐长,又识了几个字,从百科全书中得知,黄鼠也是鼠疫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其危害绝不小于老鼠,顿时惊出一一身冷汗:幸亏当时吃得少(烤大眼贼者只分给我一条肉极少的前腿),否则,一定得上鼠疫了。后来又读过一本名为《鼠疫》的小说(作者为加缪),更惊出一身冷汗:鼠疫的传播不全依赖消化系统,介质广泛。不消说吃一条前腿,仅是被它看上一眼,就能染上鼠疫。
那天是个大风天,从早晨开始,大风一直肆虐到太阳即将沉没。刮风的日子,我那个年龄的孩子,是不允许出门的,说是怕风刮了去,或被狼叼了去。在屋子里憋差不多一整天,早已抓狂,风一住,赶紧跑出去了。
那天,我还偶遇一个伙伴,是个比我大四五岁的少年。其实我们之间有那么大的年差距,是无法玩到一块儿的,可当时大街上似乎只有我们二人,于是我们便一路同行。这个少年,现在我还记得,他姓穆。我俩在相伴穿一过条胡同时,在墙眼下,几乎同时发现了这只在我记忆里安家落户的小黄鼠。
它尚在童年,约摸两寸长,半眯着眼睛,瑟缩着身子,好象正在徬徨不定中。记得看见它时,它正试图往竖直的墙上爬。也许因脚力不健,力量不足,或许因沙土墙过于松散,无法抓牢,它要么刚从高处溜下来,要么正要努力地向上攀登。反正显出一副软弱无力又急于逃走的可怜模样。
也许我生来胆小,也许尚不掌握捕捉这种动物的技能,或许根本就因身手过慢,几乎就在发现它的同时,我的偶遇伙伴,那个穆少年,已经捏紧了它的脑门,将它举到眼前。
我没留下它哀鸣的记忆,只记得它死命挣扎的状貌:它张大嘴巴,显出白亮锋利的牙齿,看样子欲咬人,但却无法咬到;它努力地弯曲着身体,把后肢伸向头部,意欲用脚爪去抓挠捏它脑门的手,却够不到,因为这手隐在脑壳后面。它完全袒露了腹部,一小块柔软的洁白,像在黄褐皮毛上缝了一块白色的补丁。偶尔吹过的残风,吹拂了它的皮毛,我发现,黄鼠外覆全身的毛,竟有三种颜色:尖梢处,白或黄褐,而其内部,紧贴皮张的毛根,则青黑。如同染发者月余后新长出来的发根。
黄鼠和家鼠仓鼠不同,它不选择临近人居处打洞,一年四季住在田野里。那么,这只刚断奶的小黄鼠,是如何流落到村子中央的呢?根据我的记忆,那时我居住的村庄,也就是我出生的村子,很大,黄鼠无论从四面八方哪个方向入村,行至被捉拿处,按它当时的速度和体能,都得半小时以上。弄不好,中间还得歇上几歇。事后,我分析,它定是遭了狂风,被风吹着,连滚带爬地误入了村庄,当我们见到它时,尚不知身处何处,正在迷惘中。
我的那个偶遇伙伴,看样子因了这个意外收获而兴奋异常。他似乎没有再理我,而是举着这只惊恐万状、死命挣扎的小黄鼠扬长而去。后来,我应该多次见过此人,但都忘了询问这只小黄鼠的下落,大概觉得应该还会有机会打听吧。
又过了几年,我随家人迁居到另一个村庄居住,对于童年生活留下的记忆,渐渐含混模糊,以至于母亲叙述某件我目睹或经历的事件时,我都会觉得异常陌生。但是,我却唯独记下了这只小黄鼠:大张着嘴巴、卷曲着身子、在一只手中挣扎着,似乎还哀求着……这样的情景,出现过无数次,竟不曾洇灭……
许多年后,离春节已很近了,我借一个机会重返故乡。这时,我已长大成人,正在异地求学。恰巧,在磨道里,我遇上了当年的那个穆姓少年,他已全然不是抓黄鼠时的模样,不仅高高壮壮,而且已娶妻生子,一个像模像样的庄稼汉。
我向他打听那只小黄鼠的下落,他一边往石磨上填加泡胀的黄豆,一边木然地看我,一声未响。他不记得那只黄鼠了。他不记得我了。他不记得那个大风停止的午后了。
我真想知道,那只小黄鼠最后怎么样了,是自由了,还是————可是,没人告诉我。
,